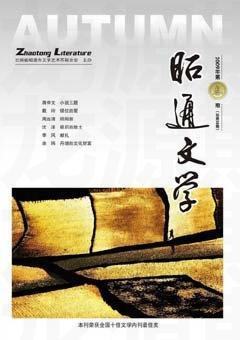大地上的行走
余冬云
一
在峰回路转的颠簸间,大湾突然出现。我这才明白,那秀丽如戴花少女的山峰,那雄峻如天外飞来的白岩,兀立路边,是为了迎客。
大湾其实没有刻意地要隐藏自己,对于东来西去的过客,大湾是厚道的。街道旁的老茶馆,老瓦房里的小旅馆,空气中悬浮着的深邃与宁静,百年的时光里开放的古镇仿佛一直在从容等待。于是,那些上云南下四川,行脚赶路的商贩选择从这里经过。简朴的八仙桌,粗陋的长板凳,不分贫富贵贱,只要你来了,尽可以大大方方坐下,卸下行囊,端起宽口的土陶碗,嘬一口茶馆老板刚冲好的热茶,眯着眼长长地“哎”一声,暖烘烘的感觉舒坦了全身的每一个毛孔,一路的疲乏顿时消除大半。相识的、陌生的,闲适地齐聚一堂,侃些山南海北的“壳子”,一时兴起,还可以接过谁的烟杆,美美地抽上一口,然后,起身各奔东西。
许多年过去了,那些匆忙的脚步越走越远,消失在岁月的烟尘里;那些兴衰成败的商路传奇,在历史的风雨里褪了颜色。被奔忙的汗渍味浸染过的小旅馆如今还躺在街道边,安静地守候,黑褐的瓦檐下,挂着“旅店”字样的招牌,红艳艳的油漆字依然那么新鲜那么惹眼。
一个声音洪亮的老乡站在高高的德陞桥上告诉我们,从前出镇雄入四川去贵州的马道,便是从这里经过。河上拱桥如虹,岸边垂柳如烟,尽数倒映在桥下凝碧如玉的深水中;田地里庄稼郁郁葱葱,农家乐的树上果实盈盈,遍布河谷的翠绿昭示着生机与活力。也许是担心赶路的人旅途寂寞,造物主才把这景色旖旎的“罗甸风光”摆放在路边,让远行的人一回头,就能看见家乡的美丽。
继续向前,便是传说中的“犀牛水”,每日三起三落,喷发退落,常常暗示着路过的生意人运程好坏,于是到了这里,他们会根据水起水落来决定自己的行程。传说无从考证,水已不再三起三落,我只在其中隐约感受这山这水对于路人的关照。
二
爬上罗甸东山,放眼远眺,一条峡谷南北贯通,罗甸河此时只是一条银白色的细带,温婉地躺在峡谷间。绵延不绝的山峦,层层叠叠地排列在面前,像是些时刻整装待发的卫士。沉沉的雾霭弥漫山尖,视野有些模糊。尽管如此,高天厚土的宏阔与苍茫,还是气势汹汹地逼入眼帘,山下“小桥流水人家”的精巧景致与此相比,就显得小气了。
把这样的大景纳入自家庭院的,绝非市井凡俗之人。陇维邦,这个芒部土司的后裔,凭着怎样的骁勇与智谋,从大湾出发,在清末民国初期这个风雨飘摇的乱世,走上了三品参将、镇彝边防游击统带、滇东边防司令等权贵之位?美丽的大湾在他戎马倥偬的岁月里,究竟发出过多少次呼唤,让他谢绝了龙云在民国18年时委以的中将参军之职,告老还乡?山水无言,一切只有逝去的时光知道。
抬脚走进被改作学校的陇家大院,昔日的繁华早已成烟,只有院子后面的那棵大树还绿荫如盖。曾经负责维护云贵川三省十多个县域治安的陇维邦,当年就是在这里打理他的一切剿匪事务的。
据史料记载,民国前期,川滇黔军阀为了扩张各自的势力,多次发动战争,沿街巷战,纵火焚房。败兵时窜扰镇雄,盘踞县城,骚扰四乡,索款筹粮。镇雄民间因战乱所受的损失,大到无法统计。手握政权和武装的陇维邦,一方面竭力维持着地方治安,另一方面却也在维持着他的封建地主式统治,对于他的是非功过,也就不好评说了。
他把一生的荣贵,都构筑在了这高山之上。这座占地数十亩的宅院,单是建筑工期就耗时多年。厚重的大门两旁,两个防卫的枪眼警觉而又空洞。一幢虽已破败却仍旧保持昔日华贵身姿的两层木楼,高高在上。从大门到楼前庭院,要经过长长的石阶。踏过这些承载过贫富不等、善恶各异的脚步的石阶,一步步向前,感觉空气中有一种凝重的威严在注视着来者。石阶旁工艺精良的石雕,廊檐下栩栩如生的木刻人物,以及那些神秘的彝族图腾,庭院里的巨大花台,线条柔美的石墙垣……每一个角落,都可以隐约看见宅院旧主人一时荣耀富贵的生活缩影。
除了在院落里追逐嬉戏的孩子们还能为这里带来一些生气,此时这里的一切是那样的残破不堪。在讲述往事的老人嘴里,这里曾经还有镌刻着陇维邦卓著功名的精美石门坊,还有七座守卫森严的碉楼,还有几重芳草鲜美的院落……这座民国时期封建地主的奢华建筑,对于后世的意义,也许只在于为县城人民公园增加一小个景点,为修中学、建粮管所木仓贡献些木材与砖石。于是,一段历史被拆散,一些艺术被遗弃,这座宅院只能满目疮痍。在楼上空空如也的房间里,我看见几缕明晃晃的阳光从瓦砾间漏了下来,照亮一地的尘埃,乱世的硝烟、血腥的富贵、诡秘的阴谋,机关算尽,到头来也只是尘埃一粒,注定要湮没在无情岁月里。
八面威风的陇维邦也许是含恨九泉的。“文革”时期“破四旧”,本该入土为安的他老也没能幸免于难,彻头彻尾的“革命者”把他的遗体从坟墓里拉出来,批斗一番,然后付之一炬,最终到底没让他的遗骨残骸再回到墓中。陇维邦原本是热爱大湾的,他也曾经是大湾历史的一个亮点,但历史对他却似乎有失厚道了。
三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这是一首几千年前的古老歌谣,描述了渔猎时代的先民们砍断竹子,再把它绑起来做成弓箭,然后将土块用弓箭射出,成功地捕获猎物的劳动场面。短促的歌号中洋溢着劳动者制造工具、获得成功的喜悦之情。也许衣不蔽体,也许饥肠辘辘,但在原始山林间,他们发出了源自心底的快乐歌唱。像这样,在生产劳动间孕育出了一个诗歌的国度,在山野村氓的代代传唱中,一些古老厚重的民间文艺得以传承下来。毋庸置疑,在田野的泥土间,在乡村的大树下,往往会出乎意料地掩藏着一些传统文化瑰宝。对于这些为现代文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养料,却又从未上得大雅之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人站出来,及时地加以整理保护,应该算是一件幸事。
比如此刻,在禾苗青青的罗甸河畔,杨老师在寻找一种叫做“打鼓草”的锄禾民歌。
那是一种在镇雄解放前后极为盛行的一种田间劳作歌谣。每到春末夏初,人们在地里薅秧锄草,便有一个挎鼓之人在人群中击鼓扬歌,一唱众合,满山遍野,歌声、鼓声、笑声荡漾,于是劳动的人们乐而忘返,在歌唱中提高了劳动效率,这便是“打鼓草”。
要找会唱“打鼓草”的人并不容易。土地承包到户,集体化劳动解散,人们的生活节奏变得自主与从容,苦中作乐的“打鼓草”的歌调也就慢慢消失在山野间。
但作为中原文化传入演变而来的文化现象,它的存在价值是时代无法磨灭的。
在罗甸小学操场边的柳荫下,一名姓熊的老人敲打着冒充木鼓的不锈钢盆子,为我们唱起了“打鼓草”。鼓点响起,老人的笑容迭现,那些用歌唱覆盖艰辛的往事又涌上心头。乡邻们围过来,课间休息的孩子们围过来,当呼啸向前的现代文明向这快要消失的民间质朴歌谣围过来时,我们生动地感受到了一种在乡野间生生不息的浪漫与坚韧,我再一次情不自禁地向哺育万物的劳动致敬。
杨老师记完谱子后兴奋地说,今天要数他的收获最大。正是有了像他这样以整理挽救濒临消亡的本土民间文化为己任的人,后来的人们才有更多的机会从传统文艺这片沃土中再次收获。
如此看来,大雄古邦是幸运的。
四
黄昏的细雨在青灰的屋瓦上笼起一层轻雾,黄褐色的廊柱再次陷入沉默,赶集的人群散去,循环上演的乡间片段徐徐落下帷幕,被岁月磨旧了的街道上,洒落一地安宁。
古镇,我来了。
整齐划一的老瓦房站立在街道两旁,衰老的身躯矜持而又不由自主地微微倾斜,几乎每一间的墙壁上,都挂着挡雨的塑料布,像外婆围裙上的补丁,破旧得让人心酸。一眼望不到街的尽头,灰暗的光线里漂浮着苍老的深邃。缓步前行,一百年的风雨沧桑在脚底细软无声。
在行人寥落的街道上,我不敢高声语,怕弄碎了空气中上悬挂着的百年时光。
被时光淘旧的黑白调子的老街,成了游人眼中意蕴深远的风景。于是,在光线开始暗淡下去的黄昏时分,那称作“新街”的老街上,闪起了一串镁光灯。
瞬间的光亮,让站出门来探望的居民们叹息失望,他们希望来者能够带来维护修缮古镇的消息。老屋老了,已经不能够更好地为他们遮风挡雨,出于对老屋的眷恋,他们又不忍将它贸然拆掉,于是只好在拆、留两难的矛盾中等待希望。
从抿嘴微笑的美丽少妇的脸上,从张大嗓门的粗犷汉子的话语里,从坐在黑洞洞的大门里默不作声的老人眼中,我们都在清晰地感受到他们对于改善已经有些破败的居住状况的强烈愿望。经过他们的面前,爱莫能助的讪讪情绪让我们无心看风景。
在街道上来回,我始终没见到在屋檐下做鞋的那个老人抬起过头。黄褐色木屋前的朱漆长板凳上,左边摆着老人装布壳的笸箩,右边是一只装浆糊的翠绿色旧碗,她身后的临街窗户上,贴着一张挡风用的泛黄塑料纸,如同一张晦色的过期广告,折射出暗淡的光线。穿得破旧的衣服,经过她的打理粘贴,变成了做新鞋的布壳,废旧的在她剪子下消亡,崭新的在她手底下完工,窄窄的长板凳此刻就是她的舞台,上演着她独自的精彩。
老人的瓦房和别家的没有两样。暴雨侵袭之时,硬砸砸的雨点也会从破旧的屋顶上穿瓦而入,准确地掉进锅碗瓢盆,肆意叮当作响;屋子里也会同样溅起无数幽凉潮湿的烦恼。不同的是,当人们都在等待希望的时候,她默然低头继续自己的生活,多少年惯听惊雷骤雨,沉淀了一份安详与淡定。
古镇,我走了。
我记住了古镇百年不渝的坚持和老人质朴超然的淡定,在名来利往的喧嚣中穿行,如果我的灵魂开始躁动不安,我就时时打开记忆,翻阅曾经在大湾在古镇的街道上,那个飘着雨的宁静黄昏。
【责任编辑 赵清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