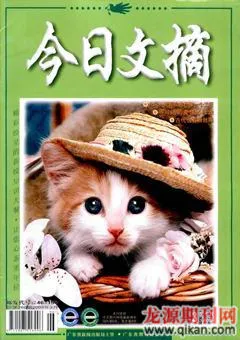若是尘土将你忘记
坚持艺术的纯粹性,坚持美、真理以及正义的寻找,已越发艰难。因为现实总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和理解的荒谬:人总因算计而变得卑琐与无耻,丑陋与邪恶无形中成为奉行的准则。但也不必沮丧,因为有信者还在,他们相信大地的事物总有它亘古不变的内在尺度。
周末处理旧杂志,将许多的印刷垃圾都清掉了。但我仍然不忍将那本刊有王家新悼念苇岸文章的杂志扔掉。因为他记述的是一个有信的人,对大地的事物进行守望的人。静寂的深夜,我又翻开来读。某些时候人还是会有些迷信和禁忌的,比如夜晚临睡偶尔打开电视,看到葬礼或死亡的画面就会马上关掉。因为深夜的阴阳交媾,总让人有怪戾的联想。但现在,我读这篇悼文,内心却有感动、安详与温暖的东西在,有一种被净化和过滤掉多天的淤塞和累赘的感觉。甚至,我仿佛也找到了内心完整而健康的原则。
苇岸是大地的守望者,是金黄色麦田,是湍急河流,是桃花满树的春天,是皑皑白雪覆盖下的北方平原的守望者,也是艺术的纯粹之守望者。他,以及之前的海子、骆一禾,都以殉身的终极虔诚而捍卫着一些我们久已隔膜的东西。
是的,我们现在已习惯听到的是喧嚣。一些投机文人是太懂语言的原创、艺术的纯粹坚守是一个无底的黑洞,它吞噬掉多少以之为天命的写作者。于是,聪明的炒作与闹腾、忙于口号与运动,居然也弄出了不小的声响;一场恶作剧,兴许也能被载入文学史。人因无知会无惧,会有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
又想起了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缪,站在聚焦灯闪烁的领奖台上,他感到对他是绝大的讽刺,他神情呆滞、自嘲惶悚,不停地念叨:该马尔罗拿奖,该马尔罗拿奖。因为只有他自己明白创作枯竭已无情地降临到他身上。清醒的恐惧也许可以使他再获新生,但车祸却将他的艺术可能性最终剥夺。
是的,谁还敢再坚持这艺术的纯粹性?总有勇者,那是尼采、卡夫卡、普鲁斯特,还有以上所记述的人。但他们则以残破的肉身作了精神的传送地。但是,必须有这样的人而不是那样的人,才能杜绝人类存在中将流畅变为松垂,将细节变成数据,将珍宝变成膺品,将丑恶变成流行。
不要太相信自己的一点聒噪,最后我还想引用里尔克的诗作结:
若是尘土将你忘记,
就对静止的地说:我流。
向流动的水说:我在。■
(李宣开荐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