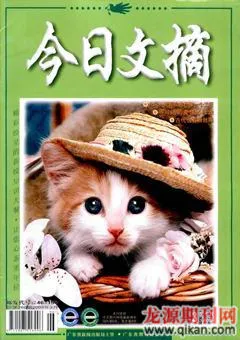藏在树洞里的秘密
饭后散步,朵而说:“爸爸,洞里有蝴蝶。”朵而指着路边的桉树。
这棵桉树我拥抱过,双手满抱尚不能合围。它怕有50岁了吧。澳大利亚年龄超过半百的树遍地都是,这缘于澳洲法令,鼓励栽树,严惩伐树——砍伐树木,须申请,再由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操刀。树木多,悉尼由此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森林里的城市。
桉树的树干底部有个窟窿,我早知道。我家信箱就在桉树旁,每天开信箱取信报,偶尔会见到无法无天的风将不知来自何方的碎纸或小树枝卷起,硬塞在树洞里。这个树洞,我将它定性为藏污纳垢之地,不喜欢它。
朵而歪着脑袋,朝树洞里看。我也弯腰,看。花蝴蝶当然走了,但我惊讶地发现,里面居然有株绿莹莹的鲜嫩小树苗。我想我不会猜错(在深圳生活时,这树我见过太多),这棵藏在桉树的树洞里的植物,是荔枝树苗。
朵而把小脑袋往树洞里凑。她还在用劲寻找蝴蝶,花了不少工夫,仍不甘心,重申:“爸爸,我昨天真的看见蝴蝶在里面。有只花蝴蝶,躲在洞洞里睡觉。”
蝴蝶喜欢四海为家,我安慰朵而,它去别处旅游了。我嘴里说着蝴蝶,心里却惦记着荔枝树苗。
风该无力托起一颗荔枝核到至少离地60厘米的树洞安家,定是某个人边慢悠悠散步,边享受着美味荔枝,忽然童心骤起(或许这食客本来就是儿童),将一枚荔枝核扔进树洞。风没播种,但功不可没——长年累月的风将尘土一点一点往树洞搬运,终在树洞里累积了足以让荔枝核安家的厚实土壤。巧的是,往年干旱少雨的悉尼,今年雨水也欣欣然赶来凑热闹。隔三岔五的阴雨天气,终于促成了一棵细小的荔枝树苗在阴暗角落里静悄悄地安家落户。
我无法断定这颗荔枝是来自遥远的中国南方,还是澳大利亚昆士兰的“水果外来户”。据说,有中国广东客商投资数千万在昆士兰种植荔枝,获初步成功。值得欢呼啊,此后,澳洲人民有幸能吃到无需远渡重洋的新鲜荔枝了。可我敢断定,这棵扎根于树洞里的荔枝,没法在悉尼这块火热的土地上开花结果。这不是悉尼的错,是老天爷不愿配合。老天爷给了悉尼美丽的风景,洁净的水和空气,却不肯给荔枝、龙眼等美味的亚热带水果颁发“居民证”。
我告诉朵而,树洞里这棵树苗是荔枝树。朵而高兴坏了,马上拍着自己的胸脯憧憬美好前景:“长大后,它结荔枝给宝宝吃。”
我很不情愿说出真相,让朵而瞬间失望,就问她:“你喜欢这棵小树苗吗?”
“喜欢。”朵而点头。
我建议道:“那往后我们散步时,常来看望它吧。”
再接再厉,转移注意力该能让朵而了解真实的未来后不至于过分伤心,我再问:“朵而,你昨天怎么发现树洞里的蝴蝶的?”
朵而来劲了,模拟昨天的故事。树侧,从东往西,朵而走一趟,说:“我从幼儿园回来,妈妈牵着我走,我就这样看,这样看,就看到了一只花蝴蝶,趴在洞洞里的小树上。我喊妈妈快看,妈妈说,花蝴蝶在洞洞里面睡觉。我和妈妈偷偷地走了,没有吵醒花蝴蝶。”
朵而昨天刚满两周岁,身高近90厘米。90厘米高的朵而能看到60厘米高的一个树洞里的蝴蝶,我想她一定是低着头才看到的。同样的时刻,昨天,若我从桉树旁边经过,定然错过这只躲进阴凉处稍作休憩的蝴蝶。我习惯了抬头朝前看,远望——不独是我,大人们,还有大人们中的正拥有大人物身份,或者期待将来拥有大人物身份的人,都习惯于抬头挺胸朝前看,习惯于远望。相对于远方和高处的风景,我们都不在乎近在眼前和低处的景致。
鼓几下掌,喝彩几声,我把这些表扬毫不吝啬地送给朵而,夸她有一双敏锐而美丽的眼睛,比爸爸妈妈更善于捕捉身边的精彩。继而,搬出一大堆气候知识,告诉她,树洞里的荔枝树很有可能将来不会开花结果。看着朵而脸上似懂非懂,呈现稍许失落的神色,我蹲下,指着树洞,说:“可是,你是第一个发现树洞里的秘密的小朋友。你知道有只漂亮的蝴蝶悄悄跑来旅游,还知道有棵荔枝树偷偷地在这里安家。如果你不说这个秘密,杰西卡、嘎那卡、萨米尔他们都不知道。”想到自己的几个要好的小玩伴还不知树洞里的秘密,朵而兴奋得手舞足蹈。也许明天,我猜她会和小伙伴们分享这秘密。
继续散步,走远,回头看。这个我曾定性为藏污纳垢之地的窟窿,在我眼里,忽然美丽起来了。因为,我也知道藏在这个残破的树洞里的秘密。它正养育一棵树的生机勃勃的希望(尽管渺茫),还曾停驻过一只花蝴蝶美丽的身影。■
(兰语荐自《城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