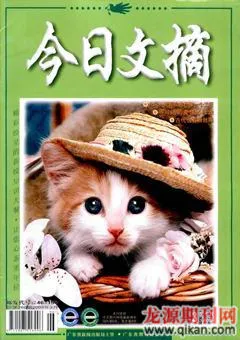最昂贵的蝴蝶夹
好久没有聪慧的消息了,她就像一滴水从人群中突然消失了^
她是班上最富有的女子,有一头公主般的秀发,谈过一个又一个差参不齐的男友。但最不济的,也会按照她的生活标准,送她300元以上的发夹。
她有许多发夹,配她动人的秀发。她也收集发夹,就像收集失去的情史。
到她终于决心嫁给一个买不起昂贵发夹的穷男生时,她的家庭全体出面阻拦了下来。
她注意到他,只因她许久以来第一次收到—枚自制的发夹。
那天,他有些发窘地递给她一个精致的木匣:原木的,被打磨得光滑无比,摸上去像摸着婴儿滑滑的皮肤。打开来,里面是一枚发夹,同样是木制的,蝴蝶状,只是背部加了一颗心形图案,是精心镶嵌在中间的,并且染上了淡淡的水红色,外围的红色沿着木纹的纹理渗透进去,居然自然而然斑驳成深浅不一的晕染感,在光线的照耀下更呈现层次。
她是发夹发烧友,于是更加好奇他是怎么把木质蝴蝶的翅膀折弯的,又怎么把基座板加进木头里的。一问,原来翅膀是用烛火逐渐烘烤,然后拇指借力慢慢烘弯,烛火可避免熏黑……而基座则是一点点凿出来的,他显然怕用烫的方式会留下印记,而且比量得精准,才能让弹性中片与上夹片都刚好合适。
后来从他室友口中得知,为了自制这个发夹,他在一木匠那里观摩了三天,要回来一捆碎木块,然后在天桥上买来了一打5元一枚的廉价发夹,好借助里面的弹性中片。前面弄坏了不知多少个,因为里面的基座很难取下来,另外木头吃色,水彩的颜色得反复调兑……
从此她将其它发夹都打入冷宫,每天都美滋滋地戴起这枚发夹。也不多话,只轻轻甩—甩头发,提醒坐在后排的他看到她头上可以以假乱真的蝴蝶夹。
后来,出外郊游,她穿的新鞋磨破了脚,咬牙坚持着走路,他很不忍,在旅游区的大庭广众之下脱下了自己的运动鞋给她穿上,自己拎着她的高跟鞋赤脚走在大太阳下走了有五里路,才遇见一辆出租车……
第二天,她把他的鞋子还他,然后撂下一句话:我从今往后都要戴你做的发夹,一辈子。
他满口欢喜地答—声“嗳”,这是他第一次对她开口讲话。
他开始更加努力地学习,一有时间便做起发夹,藏不住的笑容挂在脸上。
毕业临近,她想让他们的恋爱也领上毕业证,于是像打开那枚与众不同的发夹一样向家人隆重介绍了他。
可高官的父亲不能接受这样一桩寒碜的婚事,官太太的母亲亦不能接受男孩家的一贫如洗,以及游手好闲将来只会成为拖累的弟弟。她的恋爱嘎然而止。他的毕业分配,她也不能帮到他,她进了舒服不过的好单位,他只找了个郊区的工作,每晚对着满天星斗遥望她。
她还是会陆续收到发夹,但是不再保存,有朋友上门,就会大方相赠。
我是她的密友,拒绝了她两次相赠,接受了她一张喜帖。
豪门盛宴,—对门当户对的玉人,双方的家长都满意地颔首招待每一位来宾。她俨然木偶,任人摆布,嘴角还带着丝对新郎的嘲意,蝴碟夹突兀地立在头上。
一个月后,当她找到我时,讲出了天大的变故,却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我家出了丑闻,哈哈!”原来她新婚的丈夫在结婚半个月上就借故出差,睡在了旧情人的床上。
“这下我老妈终于知道他的狼子野心了!”她压根儿就瞧不上那个男人,知道他斯文的小眼镜下觊觎的不过是她显赫的家势罢了。
他终于给了她一个离婚的理由,她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可他怎会轻易答应?道歉、恳求、威胁,他使出浑身解数,她都无动于衷,只是若无其事地欣赏着她永远也看不够的木匣与发夹,还把它们放在不同的花布上,拍了许多照片,当成了笔记本桌面。
冷战消磨着双方的意志与信心,一次激怒之下,那个男人拿起了她珍藏的发夹,狠狠踩了几脚,又要扔出窗外,她奋力去抢,头却碰到了窗框上,额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
有些痛是再前沿的药也无法祛除的,最爱美的她,任凭父亲花多少钱请再好的专家也无法抹去她脸上的那道痕。
父母终于点头,让她拿到了结束婚姻的绿本本。
那天,走出整型医院,她心气平和地给爸妈讲:“我现在已不是什么公主了。以后,我的人生就让我自己来选择吧。”
一向心高气傲的母亲第一次垂泪:“你能幸福,比什么都好。”
看着折了翅膀的蝴蝶夹,母亲破天荒地暗示她:“你是不是该和老同学联系一下?”
她权当没听见,平生第一次剪了长发,梳起了利落的短发。
三年后,她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一头柔顺的中发,身边带着那个买不起发夹给她的他。是他的执着让她终于有勇气答应这多年后的重逢,他非让她留起长发,她则心疼他自制发夹的麻烦,头发便在双方的坚持中不长不短地滋长,直到他拿出五枚做工更为精良的木质蝴蝶夹。
他从没介意她离开过他,也不介意她脸上多了那道痕,提到这个他只会心疼。而她还是那个愿意与他在大街上吃煎饼的她,喜欢戴他自制的蝴蝶夹的她,在她心里,众多的发夹中,最昂贵的都是他亲手做的。
现在,他们终于能相知相拥夜夜看满天星斗了。“如果早知脸上的疤能让我们走到一起,也许我早该对自己的脸下手。”她笑着对我说。■
(王文周荐自《中国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