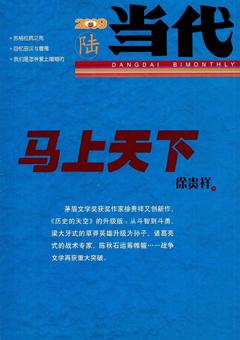苏格拉底之死
虎 头
虎头,本名冯晓虎,生于四川成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德国洪堡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德国语言研究院国际科学家委员会委员。出版过《沉浮莱茵河》、《永远的白玫瑰》等作品。
苏格拉底(Σωκρ?琢?子ηs,英文Socrates,前469—前399年)古希腊哲学“三贤”之首,西方哲学奠基人。
公元前399年,70岁的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法庭判处死刑。
雅典的民主,并非我们今天的民主。古希腊在奴隶社会就进入民主制,世界史上绝无仅有。世界其他古文明最后都发展成帝国,成为贵族封建社会,只有雅典实行民主制。
公元前683年,雅典废除国王,国家权力由9个终身执政官(archontes)掌管,其后执政官任期逐渐缩减,直至一年。到梭伦改革,雅典宪法诞生,所有公民获投票权,成为国家主宰。后又几经改革,到伯里克利执政,雅典民主发展到顶峰,贵族院司法权转至陪审团和公民大会,平民得以全面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因此,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充满自豪地宣布:“我们的制度之所以称为民主政治,就是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里,而非被少数人掌握!”
不过,伯里克利的“全体公民”其实并非“全体公民”,它仍然只是“少数人”,因为,只有纯正雅典血统的成年男子才算“雅典公民”,占雅典人口90%的奴隶、外国人和妇女均非公民。早期雅典公民非富即贵,经梭伦和伯里克利改革,平民方获公民权,如因贫穷不能履行公民义务,还会失去公民权。面临战争需要战士时,雅典又会特许外国人和部分被释奴隶升为“雅典公民”。
苏格拉底生逢雅典“黄金时代”(前461—前429年),希腊在希波战争中大胜波斯,雄霸爱琴海。苏格拉底25岁时,雅典与斯巴达签订30年和约,伯里克利一统“提洛同盟”,文化上,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好戏连台,菲狄亚斯的雕像和波吕格诺图的壁画精彩纷呈,雅典一跃而成为“全希腊的学校”。
伯里克利的成功,源于他戮力推行“权力普及到每一个公民手中”。他大量增加陪审员,恢复地方巡回法庭,除军事财政之外,所有官职均由公民抽签出任,用制度保证雅典公民全面直接参与政治生活,海量激发雅典民气,为国家蓬勃向上提供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
伯里克利完善的雅典国家机构,成为西方“三权分立”结构的雏形。
雅典最高立法机关为公民大会(Ecclesia),每月召开3至4次,年满20岁的公民都可参加。公民大会决定内政外交,审判重大案件,通过的议案经陪审法庭专门委员会批准即为国家法律。
雅典最高行政机关是500人议事会,它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召开和主持公民大会,执行大会决议,管理国家财政,监督建造船舰,控制商业,监督官吏,其成员还兼职警察。这500人又均分为10组,通过抽签轮流担任议事会执行委员会,负责处理国家日常事务。执委会再抽签决定一人出任500人议事会主席兼公民大会主席,掌管金库钥匙和国玺,任期一天,不得连任。
雅典最高司法机关是陪审法庭,陪审法庭权力甚至超过伯里克利,因为它随时可以宣布伯里克利已非“行政当局”。
伯里克利,让每一个雅典公民都能够获得罢免自己的权力。他因此获得雅典人民衷心拥戴,执政36年。
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正是陪审法庭。
公元前399年,检察官安尼图斯(Anytus)、来自斯科里亚(Skolia)的悲剧诗人美勒托(Meletus)以及修辞学者吕孔(Lykon)公诉苏格拉底,罪名有三条:不敬城邦认可的神、另立新神和腐蚀青年。
主持公诉的安尼图斯是个硝皮匠。他率领人民推翻“30僭主”统治,成为民主派巨头。反僭主时他与苏格拉底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当政后却骄横跋扈,苏格拉底讥讽说,安尼图斯当政的最大成果,就是他儿子不用再去当硝皮匠了。良言一句三冬暖。苏格拉底这句话让安尼图斯终生难忘。他带头起诉苏格拉底,让两千多年后的我嗅到浓重的公报私仇味。
在雅典,“不敬神”是重罪。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等在梭伦时代就被写进雅典宪法。“不敬神”成为重罪,归功于伯里克利老婆阿斯帕西亚。这个开设青楼的风尘女子美丽聪慧,苏格拉底常带弟子光顾其文化沙龙。尖刻的雅典人因其职业而鄙称她为“伯里克利情妇”,后世大批文人鹦鹉学舌也称她为“情妇”。其实,她乃伯里克利明媒正娶。她被一名喜剧诗人指控“不敬神”,差点被判重罪,后经伯里克利百般哀求才免于治罪。但为以儆效尤,议事会专门通过法律,规定凡不信雅典宗教和神灵或教授宇宙理论者,都为重罪。
苏格拉底并非第一个被控“不敬神”的名人。
从小亚细亚伊奥尼亚到雅典讲学30年的著名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被控“不敬神”,因为他宣布太阳是块红热岩石,月亮是块土。他是第一个说月亮光来自太阳光的反射并因此正确解释月食的思想家。在当时科学条件下,这些要算超级伟大的科学发现,值八个诺贝尔奖。他却因此被判逐出雅典。
这是人类历史上科学触犯政府而遭政治迫害的第一例,恰恰发生在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民主制的雅典。
苏格拉底案完全依雅典法庭完美民主程序审判。
说来也许没人信:雅典民主法庭没法官。法庭只设主持人负责组织审判和维持秩序,判决权完全属于陪审员。
每年初,雅典年满30岁的公民都可自愿报名参选陪审员,雅典10个行政区各从报名者中抽签选出600人,共6000人成为陪审员,任期一年。遇有案件,则根据案件大小从6000陪审员中抽签选出5到2000人组成陪审团,开庭之日再抽签将这些陪审员分配到各个不同的法庭。当时用来抽签的石嵌至今尚存。陪审法庭审理所有案件,还负责考核和监督公职人员。今天美国法庭采用的陪审团制度就源于雅典。
这个复杂的选拔程序完美体现民主政治的最根本原则:公民直接和广泛参与政治生活。它有效地预防了贿赂,因为被告几乎无法知道哪些陪审员会审判自己的案件,除非你有能力贿赂所有6000名陪审员,而且不被人知晓。
陪审员的报酬刚够一家人吃一天,因此富人多无兴趣,雅典的陪审员主要是下层公民。正因如此,陪审制度恰恰成为平衡贫富的一个伟大杠杆。
苏格拉底案陪审员500人,主要是鞋匠、裁缝和自由民。大案陪审员多达2000人,特别重大案件往往由公民大会直接审判。因此,所有说苏格拉底“由500名法官判处死刑”的文章,都是想当然的信口开河。
雅典法庭审判程序是原、被告先为自己辩护,然后举证,最后陪审团投票。陪审员都有铸着“无罪”和“有罪”的小金属牌各一块,最后选择一块投入铜罐。被告获“无罪”牌多,或“有罪”和“无罪”牌数相等,被告无罪。然后还要点算原告所得票数,如不足总票数五分之一,原告就要被反坐“诬告”。
如陪审团判决“有罪”,则当场由原、被告分别提出具体判罚,再由陪审团投票选取其中之一作为最终判决。
这一看似荒诞不经的程序,却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为让陪审团采纳自己提出的判罚,一般原、被告都会提出尽量合理的刑罚,不会随心所欲。
问题是,苏格拉底并非一般的被告。
原告控诉之后,苏格拉底开始为自己辩护。
雅典法庭民主完全彻底,即无论什么指控,无论有否证据,无论伤害大小,只要陪审团票决“有罪”,罪名即告成立。当时并无现代刑侦手段提供证据,因此,通过辩护争取陪审员同情,直接决定官司胜负。为保证双方发言时间平等,法庭以滴水计时,将陶盆盛水钻孔置于高处,辩护开始时拔掉塞子,水便开始滴到另一陶盆内,滴完为限。
正因为公民大会和法庭陪审团的无情现实,论辩术在古希腊成为最高学术。当时雅典的重大政治问题,最后通常提交陪审法庭甚至公民大会决定。因此,论辩术并非仅是语言华丽精彩的修辞法,它是政治斗争和法庭胜负的原子弹,是生死攸关的艺术,直接决定政治生命,或者物理生命。法庭论辩一般都事先拟好稿子,不仅讨论案件,还要夸耀自己的贡献或品德以博取陪审员同情。
对于唯美希腊人来说,面目英俊非常重要,长得漂亮恨不得就算美德。然而,在雅典说到论辩术,面扁唇厚、睛凸鼻大的苏格拉底如果认第二,就没人敢认第一。“30僭主”曾专门颁布一条法律“不许传授论辩术”,就是实在说不过他,不得不转而求助政治暴力的证据。
苏格拉底跟其他论辩名家最为不同的是论辩场所。每天雅典市场上出现商贩后他就站在市场上到处抓住过路人的胳膊发问,并以此开始辩论。他能在那儿站一天,而且从来没人说得过他!所以阿里斯托芬批评他“专耍嘴皮子”。
语不惊人誓不休。苏格拉底雄辩滔滔,两次引起陪审员全场哗然。
在法庭上苏格拉底说,他的学生凯勒丰去问天下有没有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的人,皮提亚回答很干脆:“没有!”
什么是智慧?
知识并不等于智慧。苏格拉底认为人只能获得部分和暂时的知识,人类能做的是努力接近知识,因为,接近知识就是靠近善。
苏格拉底得知神谕后很惊讶,因为他觉得自己并无智慧。于是他在全雅典寻访政治家、诗人和工匠,希望找到比自己更有智慧的人。
结果可以想像:所有的被访者都自认天下第一智慧。
两千多年前,人类就已经自作聪明多时了。
当苏格拉底指出他们并非天下第一智慧时,无不收获勃然大怒。于是苏格拉底找到了德尔菲神谕的答案,他向陪审团说:“我承认我无知,而他们不承认。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比他们更有智慧。因此,德尔菲神谕是正确的:惟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自己那点儿微末智慧毫无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醒悟到:只有神才能拥有真正的智慧。人能达到的最大智慧,就是认识到自己的无知。
我称之为“我知我无知”。
苏格拉底确信,让人类懂得“我知我无知”,是神交给他的“职守”。
两千多年后,“我知我无知”,仍是人类最大的终极智慧。
两千多年后,“我知我无知,仍是绝大多数人终生都没明白的真理。
苏格拉底雄辩。但是,这样的雄辩显然无法赢得陪审团的同情。
因为,此时的雅典,“黄金时代”早已不再。
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再度当选雅典领袖,随即病死,接着,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于斯巴达,斯巴达扶植“30人宪法起草委员会”专政,后被称为“30僭主”(tyrant,违宪篡权者),其统治如此暴虐,以至于后世把tyrant直接译为“暴君”。一年后他们被推翻,雅典民主派卷土重来。他们痛定思痛,矫枉过正,片面强调民主政治,结果走向另一个极端——人民独裁。
古希腊文中,“民主政治”(Δημοκρ?子ια,英文demokratia)由“demos”(人民)和“kratos”(统治)复合而成,因此,雅典的“民主”就是“人民统治”。不过,雅典的“人民”是集合名词,指公民这个整体。每一个“人”既无脱离“人民”的自由,也无言论自由。亚里士多德说个体只有属于雅典,其存在才有意义。不属于雅典的个体非鬼即兽,不算“人”!“人民”的意志和利益高于一切,为此可以牺牲任何“人”。现代民主中的政治主体是作为个体的“人”,而非“人民”,“人”虽然从属于“人民”,但同时充分享有“人”的自由和独立。
雅典民主制的骄傲,就是雅典城里只有一个权威——“人民”的权威。雅典民主制挂羊头卖狗肉,当时被雅典人民“民主”得满头大包的,也并非只有苏格拉底。雅典民主最伟大的典范是“陶片放逐法”。该法规定每年雅典可放逐一名政治家,人选由公民大会投票决定,因选票为碎陶片而得名(后选票改用贝壳,亦称“贝壳放逐法”)。投票者只需把政治家的名字刻在陶片上,无需任何罪行,无需任何证据,只要该政治家得票超过6000,即遭放逐10年。
雅典名将阿里斯泰德是马拉松战役指挥官,战功显赫,曾担任首席执政官,素以“公正者”著名,但公元前483年经公民大会投票,遭放逐!据说投票时有个文盲农民把陶片递给正好坐在他身边的阿里斯泰德代为刻字,阿里斯泰德大奇曰:“您都不认识他,为何要赞成放逐?”农民答曰:“经常听人歌颂他为‘公正者,很烦,干脆放逐了算了。”
这就是绝对“民主化”的终极结果。
因此,在雅典的民主法庭上,并无现代民主制必不可少的言论自由。
只有陪审团的言论自由。
两千多年后,I.F.斯东在其名作《苏格拉底的审判》中天真地说,如果苏格拉底以言论自由为自己辩护,就可轻易证明自己无罪。
斯东实在太聪明了。自作聪明,是后人评价前人时最容易犯的错误。
可惜苏格拉底是前人。他知道,在雅典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伟大民主国家,并没有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因此,他才在法庭上说:“世界上谁也无权下令任何人信仰什么,无权剥夺任何人自由思考的权力。”因此,他才大声疾呼:“我们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完全废除官方干涉。”
70岁的苏格拉底,何尝不知道自己定会为言论自由付出惨痛代价。
但是,他仍然自由言论!
因为他知道,将遭受后世谴责的不是他,而是那些判他死刑的人:“你们认为处死我就能使你们的行为免遭批判,但我要说,你们定会适得其反。你们会遭到更多的批判,至今我也不知这些批判者是谁,你们也不知道谁将会批判你们,但是这些人更加年轻,他们会更加苛刻地对待你们。”
苏格拉底主张“精英治国”。然而,“精英”却并未因此而喜欢苏格拉底。
首先,继承父业雕刻石像为生的苏格拉底经常上门踢馆,以滔滔雄辩证明“精英”们的愚蠢,让对方不得不承认他是天底下最智慧的人。
其次,他常年在雅典菜市场与风行雅典的“智者”辩论哲学,打得“智者”丢盔卸甲、落花流水。这些“精英”,各自都有一大堆朋友和学生。苏格拉底自己坦承,他因此“四面树敌,引来极为恶毒的诽谤”。
另外,苏格拉底也广泛得罪雅典“意见领袖”。伟大的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在公元前423年上演的喜剧《云》中描写苏格拉底坐在悬空吊篮里,在空中行走,举止怪异,衣衫褴褛,观天测地,开办私学,向学生教授颠倒黑白的诡辩。悲剧和喜剧是当时雅典城最主要的社交活动,社会影响甚巨,阿里斯托芬如此描写苏格拉底,无疑对24年后公诉他“腐蚀青年”提供了有力论据。
更糟糕的是,苏格拉底还广泛得罪“草根”。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依靠专业“精英”,不能靠抽签,一来破坏大批“自由民”眼中的“民主”,另一方面挡了他们官路,成为“草根”的眼中钉。苏格拉底还批评雅典自由民中风行的游手好闲:“做工不是耻辱,闲懒才是耻辱”。
本案的很多陪审员,就是“闲懒的”自由民。
苏格拉底自认是神赐给雅典这匹骏马的一只牛虻。他知道,被刺痛惊醒的骏马,在扬蹄狂奔之前,必得首先踩死牛虻。可是,苏格拉底觉得这是神赐给他的职守:“真理是,职守既已确定,不管自愿选择还是上峰差遣,我们都必得坚持职守,不辞危险,不惧生死,不生杂念,因为,清誉高于苟活……因为相信,所以懂得。这是神赐的差遣,他要我终生热爱智慧,省察自己,省察他人;如我贪生怕死,患得患失,擅离职守,才叫荒谬,才真正应当把我押送法庭,控我不敬神,因为那样才叫不遵神谕,贪生怕死,无知而自命有知。”
因为相信,所以懂得!
伟大人生,不外如此。
身材矮小的苏格拉底,是史上最高大的希腊人。他在法庭上矢言坚持职守,“哪怕要我死一百次!”他拒绝法庭有条件开释:“如果你们想按事先拟好的条件释放我,那么我的回答是:我尊敬你们,雅典男人,我爱你们。但我宁愿服从神,而非你们。只要一息尚存,体有余力,我就绝不会停止讨论哲学并刺激你们。”
苏格拉底的这番话,引来陪审团第二次全场哗然。
投票!苏格拉底以280票对220票被判有罪。
然后,双方提出刑罚。原告要求判处苏格拉底死刑。
苏格拉底却说自己对雅典民主贡献超过奥林匹克冠军,不仅无罪,且法庭应发给他执委会(Prytaneion)免费就餐券作为判决书。他嘲讽陪审员,批评雅典民主,公然蔑视法庭权威,说自己给学生上课不收费,所以没钱,建议法庭罚他1个“明那”(minas,合银436克,约等于100德拉克马)。当时智者厄尔努斯(Evenus)的讲座票都要5个明那。观众席上的学生柏拉图等人高声说愿替他出钱,苏格拉底才勉强把罚金改成30个明那。可他拒绝改变自己的行为:“只要良心和微弱心声还让我继续向前,我就要把通向真理的正确道路指给大家,绝不顾虑后果。”
陪审团从没见过像在菜市场上买橄榄一样拿死刑讨价还价的被告,苏格拉底彻底激怒了陪审团。投票!苏格拉底以360票对140票被判处死刑。80名第一轮判他无罪的陪审员转而投票判他死刑!
这当然不是公正的判决。这当然不是合法的判决。陪审员的愤怒杀死了苏格拉底。雅典公民大获全胜,雅典法律一败涂地。
要知道,雅典民主制下,这样的死刑判决,并不少见。
绝大多数陪审员希望看到苏格拉底丧魂失魄,面如死灰,磕头如捣蒜。
他们失望了。苏格拉底,并不怕死。从来就不怕死。他三次作为重装步兵为雅典出战,赤足走冰,救助伤兵,并把奖励让给战友。
这些都还只算匹夫之勇。苏格拉底的“天下大勇”,体现在法庭上。那一次,他不是被告。
七年前(公元前406年),雅典民主派执政,雅典海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在阿吉纽西岛击败斯巴达海军,自损25艘船与4000多人。当时狂风暴雨,无法按雅典海军传统打捞落水军人和烈士遗体,负责指挥的海军八大将因此被起诉。原告为置八大将于死地,提请议事会执委会将此案直接提交公民大会。
执委会第一天按律裁决不必提交公民大会,雅典全城民情汹汹。第二天,执委会180度大转弯,决定立即提交公民大会。当天执委会主席正是苏格拉底。他公开挑战“人民统治”,认定此议有违雅典法律,力排众议,驳回原告要求,一如七年后他作为被告站在法庭上时所说:“我绝不因怕死而错误屈从任何权威,坚决拒绝服从,哪怕因此丧失生命……即便面对危险,也要站在法律和正义一边,这就是我的职守!”
坚决拒绝服从“非正义”,哪怕因此丧失生命!
两千多年,古今中外,试看天下有几人?
一天后苏格拉底任期结束,主席换人,原告再次提议,顺利通过,最后八大将被公民大会判处死刑,雅典自废武功,最后输掉伯罗奔尼撒战争。
正义,即苏格拉底之“职守”。法庭上,当好心的海莫盖尼斯提醒苏格拉底仔细考虑辩护策略时,苏格拉底说:难道你不明白我一辈子干的就是这一件事吗?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为行正义和避免不正义而活,此外我一无所为。这就是我的最高辩护。
生命,就是“行正义”和“避免不正义”,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苏格拉底的精神核心就是正义,因为,“没有正义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正义。”
什么是正义?
守法即正义。这才是苏格拉底最终拒绝逃离死牢的精神支柱。生为此,死于此,他说“生死不渝地追求正义和其他一切美德,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对苏格拉底而言,追求正义,即坚守法律。正义,位于生死的彼岸。
其实,70岁被判死刑的苏格拉底并非第一次死去。
他都死了好几回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败于斯巴达。公元前404年,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舅父克里提亚(Critias)在斯巴达支持下建立“30僭主”统治。然而,曾经单枪匹马挑战“人民统治”的苏格拉底,却并未谄媚自己的学生来捞取在野党红利。克里提亚令苏格拉底带四个人去处死萨拉米的勒翁,苏格拉底认为此事违法,拒不从命,拂袖而去,还公开谴责克里提亚是个“坏领导”,后者恼羞成怒,下令禁止苏格拉底接近青年并威胁要处死他。
颇为自己“用行动而不仅用语言表明不惧死亡”而自豪的苏格拉底其实早晚要死在克里提亚手里,幸亏一年后民主派就推翻了“30僭主”。民主派大赦所有僭主统治期间被判有罪的人,可马上就有人密告政府苏格拉底是克里提亚的老师,两人关系密切。
四年后,推翻僭主统治的雅典在民主法庭上判处反对僭主统治的苏格拉底死刑。
历史看多了,我们就会明白,死于哪一年,真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为什么而死。
苏格拉底这个全雅典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尖锐批判所有的“非正义”,并不在乎统治者是“30僭主”还是民主派,他不遗余力地深刻揭露那些“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社会精英”,最终以生命践行自己的豪言:“只服从真理和法律,决不为苟活而奴颜婢膝。”
一生坚持“行正义”的苏格拉底,最终为正义献上生命。
求仁得仁,何憾之有!
苏格拉底不怕死,不仅因为他不怕死,还因为他视死如归。
何止视死如归。他根本就认为,与生命相比,死亡是更美丽的人生。
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的华彩演说详述了他对死亡的两种看法:
其一,如死后万般皆空,则死亡如无梦酣眠,这样的夜晚,何等美好?
其二,如死后灵魂真的进入冥界,则往生者势必济济一堂,那就能见到心仪已久的伟大诗人荷马、特洛伊战争统帅阿伽门农、名扬四海的英雄奥德修、滚石上山的西西弗斯等传说中人,这种乐趣,活人岂能得享?
苏格拉底说:“真正追求哲学,就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此话听来匪夷所思,实乃苏格拉底哲学精要,因为“灵魂从肉体中解脱时是纯洁的,毫无肉体给它带来的污垢,因为灵魂在此生从未自愿与肉体结合,它只是把自己封闭在肉体中,与肉体保持距离。换句话说,如果灵魂走正路追求哲学,并真正训练自己从容面对死亡,岂非‘实践死亡之意焉”?
苏格拉底之前,希腊哲学家主要探讨自然界到底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即世界的本体是什么。泰勒斯认为是水,赫拉克利特认为是火,德谟克利特认为是原子,这种哲学被称为“本体论”或“自然哲学”。自然哲学家研究过灵魂不灭,但他们从未明确地把“灵魂”从“肉体”中独立出来。
苏格拉底发现本体论无法拯救人类的灵魂,这才转而研究人,即什么是正义、真理、勇敢、诚实、智慧、知识,也就是说,什么是“善”。因此后人称他的哲学为伦理哲学。苏格拉底认为“善”是人类理想秩序,“善”等于自由(民主)加上自制(法律),他希望人类以“善”为行动指南,以“认识自己”为最终目标。他说人首先要认识善,因为,知善,就不得不向善。善是人生最高追求,也是最高道德价值——“善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目的,其他一切均为善而行,而非为他事而行善。”
西方哲学史上,苏格拉底的最伟大功绩是使哲学“从天上回到了人间”,他第一个提出“灵魂”是与“肉体”本质对立的精神实体:“灵魂在进入人的形体或肉体之前就存在”,因此,人并非自然的一部分,而是与自然相对的独立实体。
是苏格拉底让德尔菲阿波罗神庙门楣上的那句箴言万古长青:
γνωθι σεαυ?子?仵ν(认识你自己)!
据古希腊哲学史家第欧根尼·拉尔修(3世纪)考证,此话源自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公元前624—前546年)。每当有人问他世界上什么事最难时,他总是回答:“认识自己最难”。
但是,没有苏格拉底,世界不可能记住这句话。黑格尔说:“他使‘认识你自己成为希腊人的格言,他是提出用原则代替德尔菲神的英雄:人自己知道什么是真理,他应当观照自身……用人的自我意识,用每一个人思维的普遍意识代替神谕——这是一个变革!这种内在的确定性当然是一种新神,而非雅典人过去相信的神。”
这就是为什么安尼图斯控告他“教唆青年信新神”。
这个新神,就是人类自己。
这就是对他的第二个严重指控——“另立新神”。
是的,人第一需要的不是认识自然,不是认识他人,也不是认识天堂和地狱。
没有人,何来天堂与地狱?
人第一需要认识的,是人自己。
我们到底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为什么要来?我们来干什么?
今天,我们已经认识了自然,我们甚至已经部分改造了自然。
可是,沾沾自喜的我们,远远没有认识自己。
“认识你自己”,是哲学孜孜探索两千年仍然未能完成的任务。
两千年,逝者如斯夫。苏格拉底哲学,其实早已被超越。
然而,苏格拉底却依然矗立在那里,高不可攀。
让“灵魂”摆脱“肉体”而独立,苏格拉底开天辟地。西方哲学史,自此发端。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灵魂对抗肉体”的历史。自苏格拉底塑造“灵魂”,灵魂在西方文化中便逐步代表上帝、彼岸和天国,肉体则代表人世、今生和尘俗,是低级、庸俗和腐朽欲望的代名词。灵魂永存,肉体短暂;灵魂纯洁,肉体龌龊;灵魂引人入天堂,肉体诱人入地狱;灵魂决定肉体,肉体被灵魂决定。一言以蔽之,灵魂是善之峰,肉体是恶之渊。
苏格拉底从“肉体”中解放“灵魂”,却无心插柳,为基督教奠定理论基础,直接导致欧洲中世纪“灵魂”对“肉体”的千年压迫。
这,是苏格拉底始料未及的。
那么,用什么来从“肉体”中拯救“灵魂”呢?
哲学!苏格拉底说:“哲学接管了灵魂,试图用温和劝说让灵魂获得自由。她向灵魂指出,眼耳及其他所有感官得到的观感完全是一种欺骗。她敦促灵魂尽可能少用感官,除非迫不得已。她鼓励灵魂集中精力,相信它对物体的独立判断而非其他,不把间接得到的服从于多样性的那些东西当做真理,因为它们可感可见,而灵魂自身窥得的东西是理智和肉体根本无从得见的。”
《斐多篇》记载了苏格拉底面对死亡的从容。这从容并非来自对“天堂”的迷信(基督教的“天堂”要再过几百年才出现),而是来自苏格拉底的坚定信仰:“死亡只不过是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对吗?死亡无非就是肉体与灵魂脱离之后所处的分离状态和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之后所处的分离状态。”
在遥远的东方,比苏格拉底晚生几年的庄子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与苏格拉底,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文化上,都“相忘于江湖”。
然而,他们对生死的看法,却几乎“相濡以沫”。
所有的伟大者,都声气相通。
单论生死,苏格拉底甚至超过庄子。
庄子认为“生死一体”,所以他“不知说生,不知恶死”,生用不着高兴,死也用不着悲伤。
苏格拉底却认为死亡正好帮助灵魂摆脱肉体赢得独立和自由,从而让灵魂得以洞见真理,因此他对灵魂大声疾呼:“藐视和回避身体,尽可能独立!”
人生所有的疲于奔命,追根溯源,都是因为身体。几千年来,我们殚精竭虑,面无人色、熙熙攘攘、精神分裂,都是为了饮食、爱情、荣誉、恐惧和虚荣,说到底就是满足肉体的欲望。肉欲让人类没有时间停下来看顾自己的灵魂。到21世纪,资本主义据说胜利了,人类进步到一切以金钱为标准。2004年,我亲耳听到我们学校校长公然在全校教师大会上说:“学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他气宇轩昂,觉得自己在宣布一个全新发现的伟大真理。中国大学教育的彻底沦陷,始于这个伟大“改革”。它把教育贬低为以金钱换取证书的无耻交易。
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就厌恶金钱。他认为,你收谁的钱,谁就变成你的“主子”,而你“同时让自己变成卑鄙至极的奴隶”。
两千多年了,我们没有想通这个道理。
当时智者讲课都收学费,但苏格拉底拒收学费,因此在法庭上没钱买命。
苏格拉底当过重装步兵。重装步兵须自置盾、矛、剑等,贫民根本无法负担,所以苏格拉底并非赤贫。但他一生固守清贫,酷暑严寒穿件单衣,经常连鞋也不穿,赤足走雅典。
苏格拉底固守清贫,因为他不愿浪费生命来满足身体的那些低级欲望。
千方百计满足身体的低级欲望,就是浪费生命。
苏格拉底固守清贫,因为他不想变成奴隶。尤其不想变成自己学生的奴隶。
苏格拉底,万师之师!
苏格拉底不只是不怕死。他根本就认为死比活好。他认为身体的死亡即纯洁灵魂的诞生。而且,彼岸世界的人都是永生的。因此,“把死设想为最恶不幸,错莫大焉。”
因为相信,所以懂得!
在人类存在的最终课题上,苏格拉底第一个破解了“死亡”。
这个答案,至今仍是人类对“死亡”的最佳答案。
其实,当时在雅典,死刑犯并非真的都会死。他们至少还有三条生路:缴纳罚金赎罪、请求陪审团宽恕、自请流放。
苏格拉底没钱买命。
但是,不要钱的那条生路,他也不走:他拒绝请求陪审团宽恕。当时雅典很多被控重罪的被告都带着三姑六姨八大奶奶出庭,只要一听到“死刑”,立刻狂喊冤枉、呼天抢地,磕头如捣蒜,眼泪鼻涕流成河。
痛心疾首如仪之后,雅典民主法庭经常改判轻罪,甚至当庭释放被告。
让嘲讽陪审员、藐视法庭的苏格拉底下个彻底的矮桩,丑态百出哀告求饶,相信是不少陪审员投票赞成死刑的主要动机。
苏格拉底,拒绝从陪审员们的裤裆下爬过去:“我绝不后悔自己的申辩方式。与其苟活,我宁愿死于这种申辩。法庭如同战场,你我都不应费尽心机逃避死亡。”
法庭如同战场!苏格拉底宁愿死去,也不愿向“非正义”摇尾乞怜。
雅典民主法庭执意判处70岁的苏格拉底死刑,以彰显民主的独裁力量。
70岁的苏格拉底执意死于雅典民主,以彰显无法律的雅典民主之非正义。
相信死亡乃更加美丽的人生,是哲学家。
为正义而自愿选择死亡,是志士。
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哲学家苏格拉底自愿选择死于雅典的民主。
苏格拉底之死,点中民主的罩门。
民主的第一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它的罩门是“多数欺压少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断言:“人民易行专横残暴”,而“多数人永远且毫无例外地篡夺少数人的权利”。这位《独立宣言》的作者之一认为所有政体中民主政体最容易发生混乱。
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之父卢梭在奠定“主权在民”思想基础的名著《社会契约论》中说:“人民可以废除任何他们想废除的东西,没有也不可能有哪部法律可以约束全体人民……任何拒不服从公众意志的人,集体就要迫使他服从。”
随便举几个例子:1793年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民选上台;1852年拿破仑第三获80%的赞成票恢复帝制;1932年4月希特勒在德国总统大选中得票36.8%,仅次于兴登堡,后被总统兴登堡委任为总理。
这些例子的结果如何,大家都清楚。
最触目惊心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1793年1月21日,亲手参与发明断头台并亲自批准用它执行死刑的法王路易十六,在巴黎协和广场被送上断头台。巴黎人民万众沸腾的山呼海啸至今犹在耳边:“国王的血不是人血。斩首!斩首!”
奠定人类民主基石的法国大革命不仅杀死了路易十六,而且杀死了所有的革命领袖:马拉、丹东、埃贝尔、布里索、罗兰夫人、罗伯斯庇尔。一场旨在推翻国王统治、创立人民共和的伟大革命,掀起欧洲史上最惊心动魄的血雨腥风,赢得历史的大步倒退:巴黎人民斩首国王,为自己换回一个皇帝——拿破仑。
因此,民主不是通向人类终极幸福的万应良方。
还要看如何民主。
列宁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诚然!在政治、文化和科学领域中,能够提出新意见,能够迅速认同新知识,能够接受新真理,能够率先冲破旧传统束缚、慨然向新世纪放歌的,永远是“少数”,而且通常会被判为“不敬神”。正如萧伯纳所说:“许多伟大的真理刚开始都被视为亵渎。”
如果绝对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人类社会根本就没有进步。
因此,严格地说,民主的要义并不在于让少数服从多数。
一般情况来说,少数只好服从多数。
尤其一般来说,权贵往往比较容易获得“多数”。
民主的要义,在于保护少数。保护少数,经常就是保护社会发展和进步。
那么,用什么来保护少数?
法律!
民主无法保证自由。法律才能保证自由。洛克说:“人类天生自由、平等和独立,不能剥夺任何人这些权利,未经本人同意,不能让他受制于别人的政治权力。”而“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暴力侵犯”。
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
这不是洛克的首创。这是苏格拉底的首创。所有公民无条件尊重和服从的法律,是苏格拉底一生的理想和信仰。雅典法律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他却为了维护雅典法律的尊严而拒绝逃生。洛克仅仅重复苏格拉底的思想,就成为哲学大师。
苏格拉底用生命定义两千年后康德的“内心法庭”:“良心,就是我们自己意识到内心法庭的存在!”
严格遵守法律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
没有法律的民主,最后只能是民主暴政。
苏格拉底根本没考虑第三条生路:自请流放。因为,他从没想过离开雅典。
不过,拒绝这三条生路,仍然不等于你已经死了。
这时雅典监狱十分腐败,花钱贿赂,死刑犯便可以逃走。
很多伟人都逃走了。
伯里克利的老师兼密友、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被雅典法庭起诉,可能判死刑,伯里克利就暗中花钱安排他越狱离开雅典。
当时名气比苏格拉底大得多的普罗泰戈拉也逃走了,可惜乘船触礁,他很可能溺水而死。
不过,他确实逃走了。
苏格拉底有大把逃走的机会。他被判死刑的前一天,每年雅典派去提洛岛朝圣的大船正好离港出发。按雅典传统,这艘船返回前不能处决犯人。这次朝圣遇到特殊情况,迟迟没有返回雅典。雅典法庭规定亲戚朋友可以探望死刑犯。苏格拉底的访客络绎不绝,学生克里托、柏拉图和其他有钱朋友趁此机会打点让苏格拉底越狱。他们劝了苏格拉底一个月。
苏格拉底拒绝逃走。
他说,犯人逃跑就是摧毁法律。如果犯人都逃走,法律判决都无法执行,国家就会毁灭。他告诉克里托:“以错还错,以恶报恶,践踏自己订立的协议和契约,你就伤害了你最不应伤害的,包括你自己、你的朋友、你的国家、还有我们。”在苏格拉底眼中,法律是公民与国家达成的契约,你可以在制订法律时反对,也可以在公民大会说服大家修改法律,实在不行还可以在法律公布后移民。但如果你没移民,你就接受了国家发出的要约,默认了这个契约。
默认法律有效,你就必须遵守法律,哪怕你明知此乃恶法。
这就是史上著名的“恶法亦法”和“恶法非法”的争论。
托马斯·阿奎那和洛克认为“恶法非法”,圣·奥古斯丁认为不公正的邪恶法律“不能称为法律”,我们可以拒绝遵守恶法。
边沁和奥斯丁等人则认为:“法律是一回事,法律功过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用“好”和“坏”来决定法律是否有效,我们是否应当遵守。
因为,“好”和“坏”,绝大多数时候,是主观的。
那么,如果专制政府依据恶法任意剥夺人民的生命和自由,我们也逆来顺受不吭声吗?对这个问题,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给出了答案:如果人民的自由“被暴力剥夺,则被剥夺自由的人民有权革命,他们有权使用暴力夺回自己的自由。”
苏格拉底赞同“恶法亦法”。他认为不公正的法律也是法。作为公民,我们可以修正法律,却不能拒绝遵守法律。
这,就是法律的尊严。
否则,所有被告都可以借口法律“不好”而拒绝认罪。
世界上没有一个不遵守法律还依然存在的民主国家。
苏格拉底这个道理听起来不可思议,实际非常合理。
有法不依,恶于没有法律。
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可以制定法律来完善自己。
一个有法不依的国家,只能沉入地狱。
两千多年前,遥远的爱琴海彼岸,一位70岁的老者,为人类树立万世不晦之光辉典范。他自愿选择死亡,为真正的民主,为自由,为法律,为真理,为正义,也为自己的灵魂。
所有读懂苏格拉底内心世界的后人无不深深折服于他的智慧、勇敢和忠诚。
他的智慧在于发现“我知我无知”,从而揭示终极真理——“认识你自己”。
他的勇敢在于面对500人陪审团仍然顽强坚持自己的信仰。
他的忠诚在于他慨然用生命固守自己的“职守”。
法律在雅典与神同样崇高。古希腊法律最初是自然法,以神的名义颁布,后来城邦颁布的法律称为人定法。人定法源于自然法,雅典人服从人定法,相当于服从神的意志。
但“抽签民主”彻底破坏了这一秩序。苏格拉底认为严守法律是人民幸福和国家强大的根本保证,其价值远远高于个人生命。他认为法律同雅典一样,都来源于神,是神定的原则。
如果他逃离雅典,他就违背了自己与雅典达成的契约。
德尔菲女祭司被称为先知。然而,她们都只是习俗培养的不自觉的演员。
古希腊第一个真正伟大的先知,是苏格拉底。他说,“如果你们指望用死刑来制止人们公开谴责你们的错误生活方式,那你们就错了。这种逃避方式既不可能又不可信。尽善易行的办法不是堵住别人的嘴,而是尽力向善。这是我对投票判我有罪的人的最后告诫。”
他在法庭上宣布自己宁愿死去也不会逃走。
他践行了自己的承诺。
所有的华丽辞藻都是苍白的,生命的色彩来自于行动。
这是苏格拉底的最后一次雄辩。
他大获全胜,成功赢得为彰显法律权威死去的机会。
临刑前,苏格拉底妻子克珊西帕(Xanthippe)带三个儿子来送行。苏格拉底娶过两个老婆,第一个是法官亚里斯蒂德的女儿密尔多,她嫁给苏格拉底时没要陪嫁。克珊西帕是填房,据说比苏格拉底小40岁。她就是那个泼了苏格拉底一脑袋水的暴躁泼妇。其实她跟苏格拉底感情不错,看见丈夫将要离去,“哭得死去活来”。
苏格拉底打发克里托的仆人把家人带开,坐下来跟学生斐多、西米亚斯、西帕斯、克贝和克里托等讨论灵魂永生。他跟来自底比斯的克贝关于生死的讨论值得原文照录:
苏格拉底:“你承认死是生的对立面吗?”
克贝:“我承认。”
苏格拉底:“它们相互产生吗?”
克贝:“是的。”
苏格拉底:“那么从‘生中产生的是什么?”
克贝:“是‘死。”
苏格拉底:“从‘死中产生的是什么?”
克贝:“我必须承认是‘生。”
于是苏格拉底得到了他需要的答案:“只有在死去以后,而非今生,我们才能获得我们梦寐以求的智慧。”
不断发问,直到对方从其自己的回答中找到问题答案,这就是传说中的“精神助产术”。苏格拉底的妈是助产士,所以他自称雅典人的“精神助产士”。苏格拉底学生很多,但他认为知识都是学生自己大脑中孕育的婴儿,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他的任务,只不过是助产这些婴儿。因此,苏格拉底从不上课,只向学生提问。
这就是传说中的“苏格拉底诘讽”(Socratic irony)。
此乃古希腊论辩术必杀技。
苏格拉底诘讽完美地体现了哲学。从根本上说,哲学就是向人生发问,成功的哲学,就是找到人生的答案。苏格拉底认为一切知识均来自疑问,知识越多,疑问就越多,因此,他一辈子都在向雅典人发问。
最后,他死于发问。
从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代表西方哲学的起源和本质,一纳米都没有夸张。
当时雅典死刑非常人道,均免费奉送毒参酒(Conium maculatum L.)一杯,苏格拉底喝酒前洗了个澡,以免死后麻烦别人净体。当克里托询问葬礼安排时,苏格拉底再次提醒克里托,遗体只是个臭皮囊,已非苏格拉底,因为他的灵魂已经摆脱肉体束缚,“启程去天堂幸福国”,因此随便克里托处理。洗澡后妻儿来道别,又被苏格拉底打发走。克里托让苏格拉底点最后的晚餐以便多活几个小时。苏格拉底拒绝。因此,苏格拉底并非一般文章所说“死于黄昏”。
监刑官终于拿进毒酒,苏格拉底接过酒杯把玩片刻,说:“我将从这个世界前往另一个更繁荣的世界”,然后,性喜杜康的苏格拉底一饮而尽。学生们都为将失去老师而大放悲声,苏格拉底却颇为不悦:“朋友们,这是干嘛?我把老婆送走,怕的就是这种骚扰。临终之人应保持心灵平和,勇敢,宁静。”他在室内走了两步,说两腿发麻,便躺到吊床上。少顷,监刑官摸摸他身体已凉,就把他的脸盖起来。可苏格拉底突然自己掀起盖头来,说了他留给人类的最后一句话:“克里托,我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请不要忘了还他。”
很多文章因此争先恐后歌颂苏格拉底“人死债不灭”的诚信。
以其昏昏,使人昏昏。
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古希腊医神。古希腊人在疾病痊愈后都要向医神献祭一只公鸡,以示感谢。苏格拉底这句话的意思是,他马上就要通过“死亡”这道大门进入永生,他的灵魂将要马上从“肉体”这场大病中痊愈。
他并非真的进入死亡,而是进入一种“更繁荣的生命”。
因此,他要向阿斯克勒庇俄斯表示感谢。
苏格拉底说:推行不公正,恶于遭受不公正!(Unrecht tun ist schlimmer als Unrecht leiden)他遭受了最大的不公正,然而,他却以自己的死,判处那些陪审员的精神万世死刑。世界记住了他被判死刑时说的话:“好吧,先生们,要不了多久你们就会得到这样的名声——‘处死那个聪明人苏格拉底”。
是的,直到今天,那些陪审员的灵魂仍然在宇宙的某个地方遭受这一拷问。
直到今天,我们才明白苏格拉底离开法庭时留下的那句名言:
“我去死,你们去生,哪条路更好,惟有神知道。”
这句话,雕弓白羽,力射天狼,至今仍呼啸在人类思想史的无限时空。
我们不得不承认苏格拉底是最伟大的先知。
谁不知道苏格拉底?
谁知道那些陪审员?
我们不得不承认苏格拉底是最伟大的先知。
他说:“我离开法庭,将因你们的判决而赴死,但陪审员们,也定将被真理判为堕落和邪恶。”
第欧根尼·拉尔修说,雅典人不久就后悔杀死苏格拉底,他们判处美勒尼死刑,为苏格拉底树立铜像,而安尼图斯去赫拉克利亚(现意大利)访问时被当地居民轰了出来。
柏拉图愤怒控诉:“这个就是被你们谋杀的人,看看他吧,听听他吧!”
苏格拉底之死,成为雅典民主衰落之始。希腊衰落,罗马帝国崛起,苏拉、恺撒、屋大维、安东尼、尼禄、戴克里先、君士坦丁,个个挂共和之羊头而卖独裁之狗肉,中世纪基督教千年专制统治的庞大阴影已经隐隐出现在遥远的地平线。
苏格拉底之死,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第一起意义深远、影响至今不坠的重大事件。世界哲学史上,再没有第二个伟大的哲学家既是自己哲学的圣徒,又是自己哲学的殉道者。
苏格拉底之死成为一则寓言、一个影谜、一个传说、一个神话。
两千多年了,人类再未复制出同一重量级的思想史神话。苏格拉底主动选择自己死亡的时间和地点,亲自决定自己死亡的方式。他策划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审判,在历史和人类面前审判了雅典的民主。他用自己的慷慨就义,为“法律”两个字镀上了永不褪色的金环,为“正义”两个字施行成年洗礼。他的法庭申辩,就是他为自己撰写的气吞山河的悼词。“民主”杀死了他,但却并未因此作为凶手坠落地狱——它以苏格拉底之死为桥梁,走向霞光万丈的法律和正义。
其实,苏格拉底当时并非“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当时在希腊比他名气大的哲学家比比皆是: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芝诺、阿那克萨戈拉、恩培多克勒、第欧根尼、留基伯、德谟克利特、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塞拉西马柯、欧绪德谟和苏格拉底的老师阿凯劳斯等,个个青史留名,均非等闲之辈。
然而,苏格拉底,这个以口舌为刀剑的思想忍者,这个独孤逐日的古希腊夸父,死后躯体化作西方哲学从此无法逾越的高峰,和西方哲学史上最大的分水岭。他之前的古希腊哲学都被称为“前苏格拉底哲学”,所有那些大腕儿,都被称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柏拉图,这个在文字上为西方哲学奠定万年基础的大师,对自己的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智慧、最高贵和最优秀的人。”他们师徒的哲学也难分难解:苏格拉底的思想大多记载于柏拉图的著作。因为诗人美勒托控告苏格拉底,柏拉图甚至把所有诗人逐出了他的《理想国》。
苏格拉底慷慨赴死,真正把他自己摆上了神坛。
基督教早期,苏格拉底之死一直与耶稣之死相提并论。巧合的是,他们都未留下自己的著作。他们的思想,都只见诸弟子的纪录。
从此,这个菜市场演说家马踏时空,绕梁历史,得到后世著名哲学家万众一致的推崇,伊拉斯谟、卢梭、康德、黑格尔、齐克果,这些谁也不服的超级大腕,独向苏格拉底低下高贵的头。尼采这个文化史超级狂人称他为“知识的神秘启蒙者”,黑格尔说:“他的遭遇并非只是个人浪漫遭遇,这是雅典的悲剧,希腊的悲剧,它不过是借此事件,借苏格拉底表现出来。这里有两种力量在对抗,一种是神圣的法律,是朴素的习俗……另一种同样是意识的神圣法律,知识的法律,是主观的自由,这是那教人识别善恶的知识之树的果实,它源于自身的知识也就是理性,这是后来一切时代哲学的普遍原则。”
民主制,是雅典伟大的实践;法律与正义,是苏格拉底伟大的理想,这“两种力量”都有充足的存在理由,但却必得你死而后我方可活。
76年后,苏格拉底徒孙亚里士多德被当时统治雅典的反马其顿派指控“不敬神”。亚里士多德无疑想起了祖师爷的命运。这个亚历山大的帝师毅然逃离雅典,边逃边说:“我不会再给雅典第二次机会来犯下攻击哲学的罪行。”
亚里士多德因此给我们留下了皇皇《亚里士多德全集》。
然而,他也因此而永远无法超过没有一个字传世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之死,即“言论自由”之生。
苏格拉底之死,即“灵魂”独立于“肉体”之生。
苏格拉底之死,即“人”面对“人民”之生。
苏格拉底之死,即哲学、真理、正义之生。
苏格拉底之死,即伦理、民主、法律之生。
苏格拉底之死,即“我知我无知”之永生。
苏格拉底之死,即“认识你自己”之永生。
苏格拉底,创世纪!
责任编辑 洪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