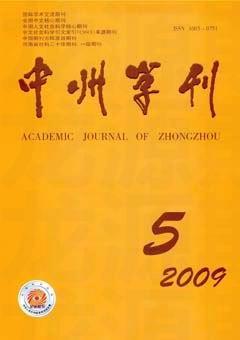从“婚变叙事”看新时期小说中进城乡下人的边际人格
李 达
摘 要: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中进城的乡下人形象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形成了一种边际性人格。它直接反映在爱情婚姻的冲突上,具体表现为情感与功利的冲突,冲突的结果往往导致一场“婚变”事件。新时期小说作家套用我国传统文学的“负心婚变”叙事模式,演绎进城乡下人的爱情婚姻故事,流露出作家的传统文化情结和乡村道德立场,折射出知识者自身价值观上的矛盾与困惑。
关键词:进城的乡下人形象;边际人格;婚变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5—0241—04
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中塑造了大量进城的乡下人形象,如高加林(路遥《人生》)、金狗(贾平凹《浮躁》)、赵巧英(郑义《老井》)、冯家昌(李佩甫《城的灯》)、连科(阎连科《情感狱》)、邹艾(周大新《走出盆地》)、鲁风(张宇《城市逍遥》)、吴福(焦祖尧《归去》)、远子(邓一光《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国瑞(尤凤伟《泥鳅》)、方圆(吴炫《发廊》)、老陈(荆永鸣《外地人•哭啥》、香香(李肇政《傻女香香》),等等。
此类形象大都生活在20世纪后期,我国社会处于全面转型的历史时期,他们的人生经历也都是由乡村到城市,跨越了两种地域空间。这种相同的时代背景、相似的人生经历铸就了他们共同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的核心特征借用社会学者的称谓就是“边际人格”。“边际性是人的时间与空间,身份与区位的两重性矛盾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道德和文化条件下的表现方式,‘边际人既是两种文化体系对流后的产物,又是新旧时代接触后的文化结晶,因而在边际人身上不仅具有两种以上的文化期望和文化冲突,他的角色行为也常常是困惑的、矛盾的、边际性的。边际性角色和多元文化取向在单个个体中的交织重叠,便产生了边际人格”①进城乡下人的特殊经历,使他们处于时代变迁、城乡互动等各种矛盾的扭结点上,道德、伦理、文化诸方面不同的价值观在他们内心冲突碰撞,从而形成了一种困惑迷惘、矛盾重重的性格特征。本文拟从新时期以来小说对进城乡下人情感冲突的叙述,或谓之“婚变”叙事,对这种性格作以分析。
一
爱情婚姻在中国是一个与伦理道德关系最密切、最敏感的话题,它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心理内容。对那些进城的乡下人来说,爱情婚姻的选择往往成为这类人从乡村挺进城市之路上的转折点,有时直接关系到他们人生追求的成败。对于他们来说:“任何爱情选择其实也是人生道路的选择”。②因此,爱情婚姻问题最易引发他们内心激烈的冲突,而这种冲突正是他们二元矛盾的边际人性格的直接反映。
新时期小说中进城的乡下人在面临爱情婚姻时,虽因每个人物的个性气质、婚姻背景等方面的差别,表现出不同的心理状态,但总的心理特征是情感与功利或者情感与理智的冲突。新时期小说中,那些进城的乡下人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改变自身命运,他们必须走向城市,去追逐权力和地位,去参与残酷的生存竞争。这种带有功利主义的奋斗方式必然与他们当初在乡村获得的以感情为基础的爱情发生冲突。不过,这在不同作品的不同形象身上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这种矛盾冲突在高加林的爱情中表现得最为激烈,他对两个女性刘巧珍和黄亚萍选择时难以决断的矛盾心情,从高加林内心独白时前后抵牾的语句中可以清楚的显示出来:“他在内心深处是爱巧珍的”,“感情上来说,我实际上更爱巧珍”,“从内心上说,亚萍以前一直就是他理想中的爱人”,“单就从找爱人的角度来看,亚萍也可能比巧珍理想得┒唷薄…许多人在分析高加林的这场情感危机时,因当时社会体制造成的城乡悬差的语境,加之作者对主人公行为强行的价值干预,结果往往使他们容易看到高加林选择的功利因素及其与情感的冲突,而忽视了这种冲突实际上是同属于爱情的两种情感本身之间无法取舍的矛盾。刘巧珍身上东方女性的美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德顺爷爷所说:“巧珍是一块金子”,她值得高加林去爱也是勿庸置疑的。但黄亚萍也同样是理想的爱人,这并非指她拥有城市户口和正式工作等世俗的条件,而是指她与高加林在精神上能够彼此理解沟通,有共同的语言和精神追求,这难道不是现代爱情观首肯的原则吗?如果说巧珍是一块金子,那么亚萍也算得上是一块“美玉”,舍谁都是终生遗憾。这着实是一个无法求解的二难命题,是一个即使用爱情心理学也难以解释的现象。这怎不令高加林作难呢?
我们再来看金狗在爱情婚姻上遭遇的矛盾。其中除了“情感”与“功利”的对立外,还搀杂着另一种因素即“情欲”。金狗生活中先后结识了三位女性:小水、英英、石华。金狗在心目中把小水当作“菩萨”,何时何地都忘不了她,金狗对小水的感情可以说是最为真挚纯洁的。随后他认识了英英,虽然他打心眼里并不喜欢英英,但后来还是跟她定了婚而抛弃了小水,这主要是为自己能进城当记者作出的一种利益交换。“当社会还没有充分发达,爱情还不能成为纯粹意义上的爱情时,人们更多地考虑了它的附加物——它是否有利于自己才能的发挥,理想的实现”。③显然,他与英英之间毫无爱情可言,只是纯粹的“功利”关系。后来金狗在州城报社正当为婚姻而烦恼、情绪低落时,石华闯入了他的生活,并很快与她发生了不正常关系。金狗的这种行为我们只能理解为情欲本能,是以前在小水身上长期被压抑的情欲释放。其实,金狗与高加林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性格中有一种被欲望驱动着的野性和叛逆精神。金狗在与三个女性关系中自始至终都夹杂着情欲冲动,但在小水面前之所以没有实现,其原因除了小水对身体的坚决守护外,更重要的是小水在金狗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男人面对着她所尊重的女人,性行为总是颇受威胁,只有在对付较低级的性对象时,他才能行动自如,为所欲为”④于是金狗就这样陷入了情感、功利、情欲的漩涡中。他尽管感情上深爱着小水,但出于功利目的不得不抛弃她,抛弃后却又感到愧疚和思念;他虽然选择了英英但并不爱她,然而出于家族关系和自身前途的考虑又迟迟不能了断;情欲使他渴望接近石华,理智又让他设法摆脱石华。金狗性格中多种矛盾冲突的交织,也使他比高加林形象更为复杂。
与高加林、金狗在爱情上遭遇两个对象无从选择的困惑不同,赵巧英面临的是回城与爱情的矛盾。一方面是“梦梦都是进城”的那种执着的城市向往;一方面是“宁愿再死一千遍”的对孙旺泉刻骨铭心的爱。正是这种扯心扯肺的情感纠缠使巧英的回城脚步显得那样滞重、犹疑,去而又返、返而又去。另外,赵巧英作为一位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女性角色,她与孙旺泉的爱情又是一种非正常的“婚外恋”情形,在乡村社会里,这是道德领域中最敏感的问题。巧英置孙旺泉已与喜凤结婚的事实于不顾,大胆向旺泉示爱,这与孙旺泉死守无爱的婚姻形式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示了向传统婚姻道德挑战的勇敢姿态,这是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正如作者所说:“她有缺点,甚至令人生厌的浅薄、尖刻,但她的追求代表了人类的生存方向,她的生命如火!”⑤
高加林、金狗、赵巧英等人在爱情婚姻中遭遇的功利与情感的冲突,这种功利寓含了乡村人对城市文明的向往,对理想事业的追求。如果说他们的“功利”还具有某种积极因素的话,那么,邹艾、冯家昌等人的心理冲突中的“功利”则包含着权力地位等更多的个人欲望成分,是赤裸裸的功名利禄。矛盾冲突的一方是乡村初恋的情人,一方是诱人的权力地位和家族利益。对此,作家们虽然也描写了他们内心的思想斗争和“抉择”,但对这种斗争和抉择的痛苦程度的描写已远不如80年代作家笔下的高加林、金狗、赵巧英那样强烈了,功利性的欲望很快把他们脆弱的乡村情感说服。邹艾泡一杯浓茶就做出了决定:要巩厚!弃开怀;冯家昌的“磨脸”心也被磨得铁硬,以至于他的四个弟弟的下跪术和刘汉香的“九主意”都无法使他的移情别恋有丝毫动摇。因为对冯家昌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⑥
功利与情感的这种矛盾冲突在香香(《傻女香香》)身上是以婚姻与爱情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乡下姑娘香香特别渴望取得城市户口,拥有一个三室两厅的家,这种功利性目标只有通过与城市男人结婚才能实现,婚姻就等于三室两厅。因此,婚姻也演化成极具功利性的目标,于是她就与刘德民这个大她24岁的城市男人做起了“双赢”的利益交换。然而这种婚姻的出发点注定就不包含爱情,是与爱情相对立的,要婚姻就不要爱情。香香后来见到刘德民那充满青春朝气的儿子后的委屈、失落,正反映了她的这种爱情婚姻无法两全的痛苦。这是当代弱者小人物在严峻的生存环境面前普遍面临的“爱情缺失”,“当‘生存的需要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的时候,‘爱情显得多么蹩脚可笑。”⑦
二
新时期小说中的进城乡下人在爱情婚姻上面临的“情感危机”决不仅仅是纯粹的爱情问题、婚姻问题,而是一个伦理问题、文化问题。在作品的具体语境中,它具有更广泛的象征意义,恋人爱人已经成了某种道德观念、文化观念的化身。他们之间的对立冲突实际上蕴含着两种道德文化观念的对立和冲突,对人生伴侣的选择也代表了对某种价值理想的选择和追求。高加林、金狗、赵巧英等人在爱情婚姻中的困惑和冲突,在80年代经济改革刚刚在中国大地上兴起而引起社会剧烈变化的语境下,凸显出城市与乡村两种文化观念之间激烈碰撞的时代意义,他们在爱情婚姻上作出的选择,代表了对现代城市文明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向往和追求,对传统的农业文明、乡村道德的怀疑和动摇,这种爱情婚姻中包含的文化象征意义在贾平凹反映农村现实变革的两个中篇《小月前本》和《鸡洼窝人家》中得到典型的传达。在这两篇小说中,作者分别用才才、山山象征农村传统思维方式、生活观念,用门门、禾禾象征一种现代的新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小说通过小月在才才和门门两人间难以取舍的困惑和烟峰与麦绒两个家庭之间的分合聚散,显示了当时农村历史性转变的背景下,农民精神世界的变化和农村生活的新动向。90年代,我国开始全面实行市场经济,精神领域出现了信仰危机,以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商业主义得到空前的鼓励和推崇。于是,邹艾、冯家昌、香香等人的爱情婚姻在这一新的语境下也具有一种新的象征意义,他们在爱情婚姻中的内心冲突,实际象征着商业伦理文化与朴素的乡村道德之间的冲突。他们最终主动地选择了代表权力、地位、实惠的爱人的做法,象征着在一个重利轻义的商业社会里商业伦理法则的巨大威力,以及重情守信的传统人伦规范多么不堪一击。
三
非常有意思的是新时期小说中进城的乡下人在爱情婚姻上遭遇的矛盾冲突往往会演化成一场“婚变”事件,那些反映乡下人进城的作品中几乎都涉及到这类婚变情节,如《人生》中的高加林、《浮躁》中的金狗、《老井》中的赵巧英、《走出盆地》中的邹艾、《城的灯》中的冯家昌,等等。而且在一些作家的文本叙述中形成了一种叙事模式——“负心婚变”叙事。我们通过对这种叙事模式的研究,可以深刻地把握作家的价值立场、创作观念及其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这里的“婚变”简单地说就是指婚姻关系的改变或重组⑧,“负心”指婚姻中的一方爱情不专、移情别恋,在传统文学中负心的角色往往以男子居多,因此有“负心汉”之说。“负心婚变”叙事是我国传统文学中常见的一种叙事母题,即“痴心女子负心汉”的主题,千百年来,它被文学家反复使用,形成一种固定的叙事模式。关于这一主题模式早在先秦《诗经》中的《氓》里就已初露端倪,后来唐朝蒋防的《霍小玉传》、元稹的《莺莺传》;宋代南戏《王魁负桂英》、《赵贞女蔡二郎》;明清《赛琵琶》(后演变为戏剧《秦香莲》、《铡美案》)等作品均是这方面的代表。这种模式具体说来,一般有这样五个阶段:“出身寒微,公子落难——淑女钟情,情意缠绵——一朝得势,声名显赫——弃旧迎新,另觅佳配——公堂受审,断送前程。”⑨新时期小说中一些进城乡下人的爱情婚姻也被一些作家用类似的模式演绎出来,如路遥、贾平凹、周大新、李佩甫等作家对高加林、金狗、邹艾、冯家昌等形象的塑造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套用。只不过在这些新时期作家笔下把传统文学中的那些负心汉,即贫寒书生、落魄公子换成了进城的乡下人,把公堂受审、断送前程的结局改写成由于一场意外导致主人公的命运突转从城市回到乡下。虽然新旧文学的“负心婚变”叙事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差异,但他们的整体特征、命运轨迹却是一致的。新时期作家与传统文学在运用负心婚变叙事模式上惊人的一致性,说明这些作家在价值立场、创作观念上与传统文学思想精髓上的相通。传统文学中对“负心婚变”的叙述明显体现出谴责始乱终弃、忘恩负义,颂扬富不易妻、恪守妇道的道德立场。“其实,传统意义上的‘负心婚变,并不完全与婚姻情感相关,而是一种恩报观念的结果。”⑩往往因为过分强调婚姻中男女间施恩受恩、知恩必报的义务,而忽视了对婚姻中情感的重视与关切以及对人的正当追求的肯定,这是一种封建传统婚姻道德观。路遥在《人生》中明显流露出这样一种道德观念,这从作者运用负心婚变的传统模式,批高(加林)褒刘(巧珍)贬黄(亚萍)的态度可以得到体现和印证。路遥对高加林的批评有时直接出面,如当高加林失掉工作重返黄土地时,作者说:“他的悲剧是他自己造成的!他为了虚荣而抛弃了生活的原则落了今天这个下场!”有时以文中人物代言,如德顺老汉的那番话:“你把良心卖了!……你现在是个豆芽菜!”作者对刘巧珍的褒扬无须赘述,对黄亚萍的贬抑则是通过对她与高加林的“现代”恋爱方式的渲染,把她丑化成一个充满资产阶级情调的洋小姐而达到的。我们通过这些或直接或间接地描写可以十分明显地感受出作者的主观倾向,尽管作者极力想把人物当时的心理描写得真实客观,但我们还是能从字里行间察觉到作者的影子。正如韦恩.布斯所说:“我们绝不能忘记,纵使作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他的伪装,他决不可能使自己消失”(11)作者在叙述中明显怀抱着乡村传统道德的偏见和黄土地情结,如果排除了这种偏见,从现代爱情观来看,高加林的追求和选择实际上也合情合理、无可厚非,决不是用“负心”二字就能简单加以否定的。贾平凹在叙述金狗的负心婚变时,并没让这种“负心”行为进行到底,而在结尾让金狗再一次回到小水身边,这种团圆式的结局在冲淡了由负心婚变带来的悲剧意味和道德谴责力量的同时,也从反面印证了作家深受崇尚自然和谐、宁静淡泊的道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李佩甫在《城的灯》中运用“负心婚变”叙事时的传统道德立场最强烈地表现在对婚变的受害者刘汉香的塑造上,作者完全是把她作为封建时代的“节妇烈女”和“弃妇”来描写的。文中写自从冯家昌离家参军后不久刘汉香就主动搬到冯家,做起了冯家实际上的媳妇。她在夫家极尽孝道:孝敬公爹,疼爱小叔,操持家务。对冯家昌更是忠诚专一,为此,作者这样写她对异性的态度:“只有一样是冷的,那是见了男人的时候。恁是怎样的男人,无论是戴眼镜的学校老师还是围了围巾的昔日同学,无论是公社的干部还是县上的什么人物,只要是主动凑上来跟她搭话的,那神情就很漠然。眼帘儿半掩着,眉头一蹙一蹙的,不看人,那眼里根本就没有人。仿佛是早就存在了什么,很警觉,也很距离。”作者也许本意在于表现刘汉香对爱情的忠贞,但读后让人非但对这一形象生不出丝毫的喜爱,反倒私下里有种“假正经”的反感。我认为纵然是心有所属,再痴情专一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吧!她对“男女之大防”神经质的敏感和警觉,完全像是用“既嫁从夫”、“烈女不嫁二夫”、“男女授受不亲”诸如此类那套“三从四德”的封建纲常伦理教化出来的。这哪里是现代女性,分明是封建时代烈女的复活。虽然冯家昌走后再没有回家,但刘汉香冲着他寄回家的奖状上的空头诺言,为了这个名分上的丈夫,甘愿为他“守节”八年。“她每晚在油灯下抚摸着冯家昌的五好战士奖状,抚摸着‘等着我三个字沉沉睡去的情景,实在可悲,恍然间映现出自古以来节妇和孝妇的凄凉身影”(12)。从作者对刘汉香的赞美并且把她作为理想的典范来推崇看,李佩甫思想深处有一种更浓厚的传统道德情结。他们有时虽然也明白现代意识、新的道德观念必将打破传统的乡村文化之梦,但下笔写作时,那种传统文化情结和牢固的土地意识就会不自觉地驱使这种观念外化在作品的人物中,结果就会出现作者的主观意图与作品的客观效果相背离的有趣现象。郑义的《老井》就是如此,不过这不是因为传统道德,而是缘于对土地的痴迷。作者在塑造孙旺泉和赵巧英两个形象时,本意是“偏爱赵巧英的”,以她“代表未来,代表民族的新生”,对孙旺泉则是有所批判的,认为他“中庸、隐忍、压抑个性”,“将他由半人半神降格为井,而将巧英从狐狸精(非人)升格为人”。(13)然而由于作者历史传统的包袱过重,作品呈现出来的客观效果却是孙旺泉形象更为深沉浑厚,而赵巧英形象则显得单薄苍白。正如赵园所说:“郑义的《老井》以巧英旺泉为对照,或如作者所说,旨在肯定巧英式的人生追求,但作品给人的印象却是,作者更倾心于旺泉式的人格与价值立场。又正是知识者自身价值论上的矛盾。”(14)
结语
边际性人格特征使进城乡下人这类人物成为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中一类独特的人物形象,其性格中的多元性、矛盾性也使形象的内涵异常丰富,张力十足,发散出耐人品味的艺术魅力。同时,透过他们,我们也可以窥见当代一批移居城市的乡土作家,自身价值观上的矛盾与困惑。
注释
①叶南客:《边际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②李书磊:《乡土观念的弱化与强化——评从<人生>到<老井>的主题变迁》,《光明日报》1985年11月28日。
③张华:《互窥中生辉、映衬中臻善——于连和高加林比较谈》,《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3期。
④[奥]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林克明译,作家出版社,1986年。
⑤(13)郑义、刘润为:《关于<老井>及其评论的通信》,《文论报》1986年6月11日。
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⑦何西来、杜书瀛:《新时期文学与道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⑧虽然本文论述的主人公大多并未正式缔结婚约、建立家庭,他们关系的改变只是恋爱情感的转移,确切地说属于“情变”。但根据乡村婚姻习俗,实际上男女双方的关系已经得到默认,可以视为确立了婚姻状态。因此,我们在此仍笼统的称作“婚变”。
⑨干与:《灰色的困惑——<人生>、<平凡的世界>的原型分析及其它》,《延安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⑩黄世忠:《婚变、道德与文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11)[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付礼军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12)雷达:《<城的灯>中的圣洁与龌龊》,《中华读书报》2003年6月11日。
(14)赵园:《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自序》,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
责任编辑:凯 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