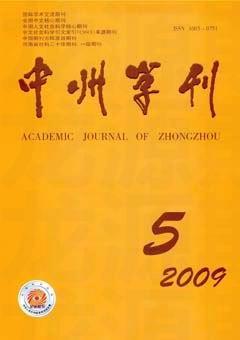七律的定型者究竟是谁
龚祖培
摘 要:考查诗体定型要以诗人群体的作品符合格律为依据,但不是全部诗人的全部作品符合格律。明人胡震亨“自景龙始创七律”的经典论断虽然对后世影响很大,但与史实不符;李峤的七律尽管全部合律,但写作年代不是最早的,因此不能作为七律定型的唯一代表。武则天统治时期的“石淙诗”是研究七律的重要材料,可以证明七律在此时已经定型。沈佺期的七律写作年代早,作品多,影响突出,无论如何也是这一诗体定型的代表人物。
关键词:七律;“石淙诗”;四韵七言;群体合律;沈佺期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5—0215—05
近年来关于唐代律诗形成的研究,有一个趋同的认识,即批评定型于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的传统说法。怀疑这一传统观点者有之,否定这一传统观点者亦有之。甚至有人提出新观点,认为“七律定型于李峤而成熟于杜甫”①;另有人认为“律体是人们经历了两百年左右的不断探索、反复实践才得以形成的,很难想象它的最后定型竟然是由沈宋两个人说了算……”,并提出“律体定型于初唐诸学士”②的观点。说李峤是定型者,依据是李峤今存4首七律完全合律。笔者认为,所谓完全合律的标准,讨论诗体定型有可商之处;持论者还有一个大的破绽:没有认真考察这4首七律的写作年代。如果有早于这4首七律的证据,其论点当不攻自破。说律诗定型于初唐诸学士,仅是一个推论式的结论。“诸学士”这一群体有很多的个体差异,不一定观点相同,也不一定人人都对律诗的形式感兴趣并有意识促进诗体形成。笼统地说定型于“诸学士”没有确定性,也不符合事实。何况讨论这个问题必须要以诗歌作品为依据,而且只能以现存的材料说话。很多初唐的宫廷学士没有诗作流传下来,或者流传下来的数量有限;也有可能他们原本就不写诗,或者写得很少,或者有的人只专注于某一种诗体,比如只写古体等。要让他们分享律诗定型的成果,显然不妥。另外,所论“诸学士”诗作合律的数据还有问题,比如粘式律为100%,居首位的所谓“双料学士”③徐彦伯,至少有3首诗失粘,统计有误。其实,定型于李峤之说站不住脚,定型于“诸学士”之说也无实际意义。下面首先讨论诗体定型的标准,再以新考证的材料为依据,检验新说和旧说,以寻求科学的结论。
一
要考查一种诗歌体裁定型的年代,就首先得确定考查其定型时所遵守的准则。换句话说,一种诗歌体裁怎样才叫定型,必须有一定的标准检验。
唐以前的诗歌体裁没有十分固定的格式。即使有四言、骚体、五言、七言之分,也还有字数的多少、句数的多少、押韵转换的不同等明显差别,很难确定其统一的格式,笼而统之地称之为“古体”是恰当的。
自唐代始,才开始有字数、句数、押韵乃至平仄都固定的诗歌体裁,即五绝、七绝、五律、七律等。这些诗歌体裁什么时候固定下来,然后成为众人写作遵行的形式,是应该搞清楚的学术问题。如果对各体格律诗的定型年代都有一个科学考查的结论,那么才能说这一笔“遗产”的清理有了结果。从唐代以来,研究这一问题的人不少,但结论却很不相同。究其原因,除了研究者各自受时代、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制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研究者之间没有一个共同遵守的确定诗体定型的准则。结果往往是各执一端,就其一点立论,甚至凭感觉说话,当然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难以形成共识。清人袁枚说:“七律始于盛唐,如国家缔造之初,宫室粗备,故不过树立架子,创建规模;而其中之洞房曲室,网户罘罳,尚未齐备。至中、晚而始备。”④袁氏随便下个结论,就把初唐时期近百年的时间和很多作品都抹掉了。
考查诗体定型的准则该怎样确定呢?这几个要点恐怕值得重视,应该为研究者共同遵守:第一,要考查相同时代的诗人群体创作的作品,最好是有他们相同时间写作的同一题目的诗歌为据。第二,同时有多人的作品合律,不一定是每人的作品合律,就可以认定为诗体已经定型;考查的重点为诗人群体是否共同遵守一种固定的格式写作,而不是检验每一首诗的平仄粘对是否全部合律。第三,一个诗人的作品,或者某一单篇作品一般不能形成定型的结论,但可以作为结论形成的辅助证据。如果以一个诗人的作品为据,那就必须证明有他的相关理论主张以及其他诗人遵循其写作的因果联系。第四,得出诗体定型的结论,最好是进行综合考查,让几个方面的问题形成逻辑关联,能够互为支撑、互为印证。
遵照第一个要点所考查的诗体定型年代最有价值。举一个例子说明,明人胡震亨“自景龙始创七律”⑤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一直到今天都如此。初唐中宗景龙三年(709)二月,有9人同写《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七律⑥。有人据此考查,得出“内有七首通首合律”⑦的结论。七八个诗人都按照一种固定格式写诗,一字一声都不出错,事实上这就证明七律已经定型,有确切的年代,比笼统地说定型于初唐更为科学,更有学术价值。至于有少数甚至个别的诗作局部出现粘对格律问题,并不能否定这一诗体已经定型。
诗歌作品出现局部或某一处粘对方面的格律问题,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诗人构思写作时追求好句、意境,表明文学理论主张、审美倾向等,最可能有意地违犯诗歌格律,使粘对不合,更不要说有的人对平仄格律本来就掌握得不好,有的人无意犯了规则等情形。李商隐的名作《登乐游原》,开头一句就连用5个仄声字“向晚意不适”,可以说是严重违犯诗歌格律,但不能因此说李商隐的晚唐时代五绝还没有定型。杜甫晚年写的诗,自己标题《夔州歌十绝句》,第一首第一句就是连用7个平声字的“中巴之东巴东山”,能说七绝还没有定型吗?也是杜甫晚年写的《雨四首》之一的五言律诗,有“微雨不滑道”一句,第二字、第四字都是仄声,失对,能说五律还没有定型吗?黄庭坚欣赏瘦硬风格,不写弱句,于是《寄黄几复》就出现“持家但有四立壁”5字皆仄的情形,总不能因此说宋代七律还没有定型吧。今天考查诗体是否定型时,千万不能胶柱鼓瑟,只注意格律的局部细微之处,只以完全合律、通首合律为标准。其实从来就没有全部诗歌都合律的时代,即使格律诗体定型以后也如此。但是,讨论平仄格律必须有一个度的标准:局部的、很少的不合格律之处不影响诗体定型的结论;大量的、重要的地方不合格律,肯定应视为诗体还未定型。
二
景龙三年群体创作的七律,肯定已是诗体定型的标志,但可不可以认定这就是七律定型的最早年代呢?考查的结果是否定的。
武则天统治时期创作出的“君臣嵩山石淙赓和诗”(以下简称“石淙诗”),参与写诗的人相当多,作品都是七律的体式。《全唐文》卷97有武后《夏日游石淙诗序》一文,其中明确要求参与写诗的人“各题四韵,咸赋七言”⑧。当时有哪些人参与呢?《全唐诗》卷46狄仁杰《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题下的一段说明文字很重要,特移录如次:
石淙山,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三十里。有天后及群臣侍宴诗并序刻北崖上。其序云:石淙者,即平乐涧。其诗天后自制七言一首。侍游应制皇太子显、右奉裕率兼检校安北大都护相王旦、太子宾客上柱国梁王三思、内史狄仁杰、奉宸令张易之、麟台监中山县开国男张昌宗、鸾台侍郎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夏官侍郎姚元崇、给事中阎朝隐、凤阁舍人崔融、奉宸大夫汾阴县开国男薛曜、守给事中徐彦伯、右玉钤卫郎将左奉宸内供奉杨敬述、司封员外郎于季子、通事舍人沈佺期各七言一首。薛曜奉敕正书刻石。时久视元年五月十九日也。按此事新旧唐书俱未之载。世所传诗,亦缺而不全。今从碑刻补入各集中。
根据提示,在《全唐诗》卷61、卷64、卷65、卷68、卷69、卷76、卷80、卷96分别检出了所列有关人员的作品。君臣相加,一共17首诗。有清楚的时间记载——“久视元年”(700),且又是群体的同时同题之作,值得重视。
《全唐诗》卷52宋之问下有一首《三阳宫侍宴应制得幽字》“离宫密苑胜瀛洲”七律。这首诗也有“侍宴应制”的标记,地点也是嵩山三阳宫。《通鉴》卷206《唐纪•则天顺圣皇后中之下》久视元年有“作三阳宫于告成之石淙”和“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阳宫避暑”⑨的确切记载,说明三阳宫就建在石淙附近,因此石淙和三阳宫都可作写诗之处的标志。《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中说武则天在圣历三年(700)和大足元年(701)夏天都到过三阳宫,避暑的时间还很长。因此,可以说宋之问的诗也与这一次或这两年的另一次群体写作有关,他绝不可能单独一个人侍宴应制。高棅《唐诗品汇》选入此诗,标题是《三阳宫石淙侍宴应制》⑩。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也入选,标题为《嵩山石淙侍宴应制》,题下注云:“此武后游幸石淙而作也。”(11)加上宋之问之作,君臣一共作诗18首。不管是一次还是两次群体创作,时间都只能在公元700年和701年这两年的五月至七月两个时段。
为什么这样讲?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还有三大证据:第一,如果是其他时间,那就与参与人员的履历不合。第二,武则天在大足元年以后没有再去嵩山,到神龙元年(705)去世这4年之中,她长时间住在京城长安。自石淙君臣赋诗回洛阳后,紧接着三阳宫也被拆除,不可能再在此作诗了。据《旧唐书》本纪记载,大足元年冬十月武则天到京城长安,一直到长安三年(703)“冬十月丙寅”才从长安返回,“乙酉,至自京师”,回到洛阳,并说“(长安)四年春正月,造兴泰宫于寿安县之万安山”。《唐会要》卷30有修建三阳宫与兴泰宫的记载:“长安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毁三阳宫,取其材木,造兴泰宫于寿安县之万安山。”(12)武则天回到洛阳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三阳宫就被拆掉了。这时是冬天,即使又去过石淙,也与写诗季节不合。第三,狄仁杰死于久视元年,作诗当然不会超出这一时限。《旧唐书•狄仁杰传》:“是岁九月,病卒。则天为之举哀,废朝三日。”由此还可以确认与其诗同题之作也作于这一年的夏天。至于宋之问那一首为什么不刻石,要从众作之中剔除,很可能是他的声名太糟,被睿宗赐死的原因。
如果这18首诗都作于公元700年,至迟也不超过公元701年,那就可以考查诗体是否定型,从而确定七律定型的年代,最终否定胡震亨的经典论断。
在18首诗中,有5首完全符合格律,一点问题也没有,它们是李峤、苏味道、崔融、薛曜、沈佺期的作品;剩下的其中6首只有一联失粘,其他全合,它们是姚崇、阎朝隐、徐彦伯、于季子、宋之问、张昌宗的作品;杨敬述和武则天的作品有两联失粘;狄仁杰的作品只有尾联失粘和失对,其他三联全合;中宗和睿宗的作品有两联失粘,还有失对处;张易之的作品颈联失粘,尾联失对;武三思的作品全部失粘,有一处失对。
这样的状况能不能说七律诗体已经定型了呢?根据上述标准,可以肯定地说已经定型了。首先,有5个人的作品完全合律,这绝不是巧合。如果没有诗体固定的格式遵循,怎么可能有5人的作品形式,连一字一声的细微之处都完全相同?数量已经达到5人,当然可以视为诗人群体;群体合律是判定诗体定型最重要的标准。其次,另外的作品尽管有不合律之处,但总的来说是极少的局部之处。如果把只有一联失粘,其他全合的作品以基本合律的标准统计,加上完全合律的5首,就有11首,接近总数的2/3了,从概率上讲已经占多数;即使11首之外的作品,也只是少量的局部有格律问题,总体还是合乎七律体式的,并不是相差悬殊的格式,只有武三思的例外。就这18首诗而言,皇室、宗室、弄臣的作品问题较多。其原因不难分析。他们对格律或许还不完全懂,或者还有故意不按格律写的情形。当年梁武帝不懂四声,听了解释之后仍然不按沈约的四声理论写作。(13)明代学者张溥甚至认为“声病牵拘,固非英雄所喜也”(14)。梁武帝不喜欢受约束,小瞧一字一声的学问;武则天、中宗、睿宗、武三思等人有没有那样的心理,很难说。还有,张易之、张昌宗的作品真伪不好讲。《旧唐书•张行成传》附二张传说:“易之、昌宗皆粗能属文,如应诏和诗,则宋之问、阎朝隐为之代作。”同书《阎朝隐传》亦云:“张易之等所作篇什,多是朝隐及宋之问潜代为之。”《新唐书•文艺传中•宋之问》下也有相同的内容。《唐诗纪事》卷3“武后”下还说:“大凡后之诗文,皆元万顷、崔融辈为之。”(15)有这样不确定的因素,将他们的作品按完全合律的标准衡定,没有什么价值。再次,即使是学士的作品也可能因追求好句而不得不犯格律,这也不影响讨论诗体定型。最后,作为一种诗体,此时已经有确定的名称:“四韵”、“七言”。这是唐人所指七律诗体的明显标志。唐人没有“七律”、“七言律诗”连称的,使用最普遍的是“七言四韵”、“四韵七言”,简称“四韵”和“七言”、“七字句”,还有就是普遍称“长句”、“长句四韵”,直到晚唐也是如此。杜甫的七律中只有一首有称谓标志,那就是《江陵节度使阳城郡王新楼成王请严侍御判官赋七字句同作》。羊士谔《西川独孤侍御见寄七言四韵一首为郡翰墨都捐逮此酬答诚乖拙速》,韦庄《辄吟七言四韵攀寄翁文尧拾遗》,元稹《卢头陀诗》的小序有“列而序之,仍以四韵七言为赠尔”,韩偓《余寓汀州沙县病中闻前郑左丞璘随外镇举荐赴洛兼云继有急征旋见脂辖因作七言四韵戏以赠之或冀其感悟也》,李商隐《奉同诸公题河中任中丞新创河亭四韵之作》,杜牧《长安杂题长句六首》、《柳长句》、《李侍郎于阳羡里富有泉石牧亦于阳羡粗有薄产叙旧述怀因献长句四韵》等,都是指七言律诗。《夏日游石淙诗序》有明确的“四韵”、“七言”标示,事实上这就是限定诗体写作,为众人所认可的一种诗歌形式。这种诗歌形式就是后人所称的七言律诗。
三
讨论七律形成的问题,沈佺期是一个无论如何也得面对的人物。以《全唐诗》统计,沈佺期今存16首七律,很多完全合律。就算把《红楼院应制》等几首有争议的减去,其数量仍为初唐诗人最多之一,而且初唐诗人七律在10首以上的只有两人,另一个是苏颋,但他的年龄比沈小得多,其中还有盛唐时期的作品。李峤的只有4首,写作年代最早的就是“石淙诗”,其他都作于中宗朝。沈佺期不仅有“石淙诗”完全合律,还有大名鼎鼎的“卢家少妇”一首。此诗写于万岁通天元年(696),也完全合律。最早见于崔融编选的《珠英集》,诗题是《古意》(16)。稍后于《珠英集》的《搜玉小集》也入选,诗题也是《古意》。唐末的《才调集》则题作《古意呈乔补阙知之》。崔融与沈佺期是同时代的人,彼此熟悉,诗题应该是《古意》。《才调集》的诗题是后人知道这首诗的本事后补充的,虽不是原题,但并无错误。至于诗题一作《独不见》,那是《乐府诗集》等选本根据诗的内容和风格附会妄加的。此诗并非乐府诗,只因诗句有“独不见”字眼,与梁代柳恽《独不见》诗作巧合而误收进《乐府诗集》。(17)诗题用“古意”,有所隐晦但又暗示现实,这是当时甚至全唐诗的惯例。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一诗,明明要讽刺当时京城长安的权贵,但标题却用“古意”,字面的所指意义都用汉代的人和事,这是既含蓄又透明的表达,“汉”即“唐”也。沈佺期的《古意》,表面上看是泛写思妇和征夫的相思痛苦,但当时的人知道它所指什么,是为乔知之惑溺于情而发。唐人刘餗《隋唐嘉话》卷下、张鷟《朝野佥载》卷2都记载乔知之与他的婢女悲欢离合的故事。说乔用情太专一,宠爱婢女以至于不娶妻。后来婢女被武承嗣夺去,乔思念寄诗,婢女感愤而自杀,武承嗣大怒,罗织罪名将乔杀害。(18)唐人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的记载大致相同,只是婢女的名字不是碧玉。(19)这个故事有小说家的虚构成分,但并非毫无根据,正如《四库提要》评价《朝野佥载》所云:“耳目所接,可据者多,故司马光作《通鉴》亦引用之,兼收博采,亦未尝无裨于见闻也。”(20)两《唐书》乔传也记载有其事。其他史事所载,也与沈诗相合。万岁通天元年(696),乔知之以左补阙的身份为武攸宜随军参谋,东征契丹,沈佺期写诗相赠。诗就乔知之和他的女人两方面下笔。“辽阳”、“白狼河”、“丹凤城”都不是虚写。一指东征之地,代乔;一指京城,代乔的女人。两地相隔遥远,偏偏又是用情很深的男女,其情就倍加感人,再加上风流韵事,足以促其流传。这就是为什么此诗能让沈佺期享得大名的原因之一。古代高度赞美这首诗者大有人在,如沈德潜评论说:“云卿《独不见》一章,骨高气高,色泽情韵俱高,视中唐‘莺啼燕语报新年诗,味薄语纤,床分上下。”(21)就现在已知的材料,此诗是写作年代最早的七律。因此,就七律作品的数量和年代上来比较,李峤都不及沈佺期,岂能轻言由李峤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