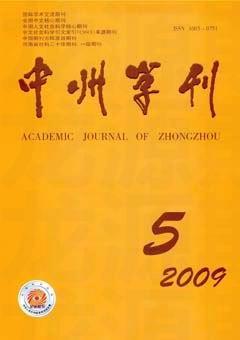如何利用出土文献进行古代文学研究
赵敏俐
摘 要:利用出土文献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主要看文献本身提供多少有用的信息,而不是通过某一出土文献的研究作无限引申的猜想式研究。日本汉学家清水茂和中国学者李庆可以作为引申猜想式研究的典型代表,但这种研究背离了“以实物为证”、实事求是的考古学的基本原则,是不可取的。以对汉乐府“行”的本义的阐释为例,假如没有可信的经典文献或出土文献记载作证据,就不能凭推测认定它是“一种特定形式的音乐”,而应该遵循《宋书》和《晋书》记载的定义:“‘行者,曲也。”“行”与春秋战国之际的“行钟”没有任何联系,在汉代也不存在“行”这种“依‘行钟音阶的乐曲”。
关键词:出土文献;实证材料;实事求是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9)05—0205—04
出土文献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影响之巨大,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笔者在1999年12月召开的“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上,曾发表过《20世纪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一文,从三个方面进行概括:“一、出土文献本身即为文学作品,如何改变了以往对于文学史的认识;二、大批与文学相关的出土文献,如何从历史、文化、艺术、民俗等各方面深化并扩展着我们的文学研究;三、本世纪的出土文献,如何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①然而在利用出土文献进行文学研究当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何正确地将出土文献与现存历史文献有机结合,通过正确的分析鉴别而对文学史上的某些问题进行新的研究并得出新的结论,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本文拟从日本学者清水茂《乐府“行”的本义》一文入手,就如何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中所存在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行”是汉乐府歌诗题目中常用的一个词语。查沈约《宋书•乐志》,平调曲中有《短歌行》、《燕歌行》,清调曲中有《秋胡行》、《苦寒行》、《董逃行》、《塘上行》,瑟调曲中有《善哉行》,大曲中有《东门行》、《折杨柳行》、《艳歌罗敷行》、《西门行》、《煌煌京洛行》、《艳歌何尝行》、《飞鹄行》、《步出夏门行》、《野田黄雀行》、《满歌行》、《棹歌行》、《雁门太守行》。郭茂倩《乐府诗集》则辑录了更多以“行”字为题的汉魏相和歌辞作品。正因为如此,什么叫“行”的问题也受到了当代学者的关注,如丘琼荪、逯钦立、王运熙、杨荫浏、李纯一等的论著中都有涉及。近年来更是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日本学者清水茂《乐府“行”的本义》一文,在1955年安徽寿县出土的乐器中有“歌钟”和“行钟”和李纯一的相关考证文章的基础上写成,近年来颇受人关注。
清水茂的考证文章依据的是1955年5月24日治淮民工在安徽寿县西门取土时发现的乐器。其中八个编镈中有四个上面有“诃钟”(歌钟)之名;还有九个编钟,其中五个刻有“诃钟”之名,四个刻有“行钟”之名。②这些乐器制作于春秋战国之际,郭沫若考证认为墓主蔡侯当是申侯(前471—前457在位)③,陈梦家考证则认为是昭侯申(前518—前491在位)④。其后,李纯一对这些歌钟和行钟进行了包括音高、音分与频率三个方面的测音,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对它们的音乐性能进行了详细研究,最后他说:“总上所述,暂可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歌钟与行钟的区别不仅在于应用场合之不同,还在于定音和组合的差异。即:歌钟用于上层贵族日常燕飨之时,所以它是按照一个完整音阶(或调式)而定音而组合;行钟为上层贵族巡狩征行时所用,因而它的定音和组合是以一个音阶(或调式)的骨干音为根据。当然,由于目前所能依据的资料十分有限,所以这个初步结论正确与否,还有待于将来新的考古发现和更多的测音结果来检验。”⑤可见,李纯一虽然对出土歌钟、行钟进行了测音研究,但是,关于这些歌钟和行钟的具体用途以及何以被称之为“歌钟”和“行钟”的问题,因文献资料所限,他只是得出了一个推断性的结论而已。至于其音高、音阶等之所以会与宴会所用歌钟有差别,则完全是“为了适应出征出行的条件和要求而使然”(李纯一语),并不是一种音乐类型得以命名的原则。更何况,这些乐器作于春秋战国之际,也不可能与汉乐府的“歌行”发生联系。但是李纯一的研究却激发了清水茂的联想。按清水茂的说法,“李纯一论文并没有把这里的‘歌钟、‘行钟与乐府的‘歌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但我们却可以由此进一步推论:依‘歌钟音阶的乐曲是‘歌,依‘行钟音阶的乐曲是‘行”⑥。而支持清水茂作出这种联想的根据,则完全是他自己的推测:
我们可以推测,在使用编钟演奏的音乐中,其他乐器也可能同时被使用,但在演奏时,如果使用歌钟,就按歌钟音阶演奏,如果使用行钟,则依行钟音阶演奏。这样,按歌钟音阶演奏的乐曲,因其具有完整的音阶,就被题名作“歌”,或者不作特别命名;与之相对,用于旅行的音乐,即依行钟简单的大音程跳跃的音阶演奏的乐曲,因其具有旅行音乐的意味,而被题名作“行”,或即使乐曲并非用于旅行,但“行”的名称照样保留了下来。众所周知,音乐中有不使用某些音阶的乐曲,这就是与西洋音乐的七音阶相对的东方音乐的所谓“4、7不用”的五音阶。由此我们似乎也可以推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曾经有过一种与五音阶旋律相对的、极其简单的三音阶旋律。⑦
分析上文我们会发现,清水茂研究问题的逻辑起点,并没有建立在李纯一关于行钟测音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李纯一关于行钟“可能是因为这些乐器用于贵族们的出行才名之为‘行”这一推测的基础上。然而,李纯一的推测是有实物考证为根据的,而清水茂的推论却完全没有汉代出土文献与相关历史记载的支持,成为纯粹的空想。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汉乐府中的“行”是按照行钟的音阶来演奏,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汉乐府歌行用的是“极其简单的三音阶旋律”。这种通过某一出土文献的研究而做无限引申的猜想式研究,已经背离了“以实物为证”的实事求是的考古学的基本原则。
可能是由于这种想象过于大胆,所以清水茂在文章中给自己留下了余地。他说:“这种三音阶的乐曲,即使依李纯一氏的推测,也仅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与东汉以后出现的乐府诗能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似有疑问。从战国至汉代的二三百年间,这种三音阶的旋律是否继续留存,因‘文献不足征,现在只能试作推测。”在文章的最后他又说:“本文虽然推测颇多,求证不足,但探求‘行为‘曲之本源,与历来的解释相比,可能性似乎较大,故试作假说,以求教高明。”⑧正是由于清水茂在自感证据不足却又充满自信的这篇文章的引发之下,李庆发表长文支持清水茂的观点。文章对《乐府诗集》中凡是标有“行”的题目都作了搜集,并且进行了分析,同时又引用了大量的汉代文献来试图证明汉代存在着和先秦行乐相关联的“一种特定形式的音乐”。他最后的结论是:“总而言之,歌行之‘行,就其本来意义说,是一种在古代祭祀、宴乐、出行等仪式时演奏的一种特定形式的音乐。‘行,和歌、引、弄、操、吟、拍等的乐曲,在音阶、使用的乐器,在运用的场合、范围,在历史展开过程中的表现形态,都有明显的不同。随着礼乐制度的变更,到了魏晋时代以后,经一些文人改编的歌行之‘行,除了音乐之外,还指和这种音乐相对应的诗歌作品。”⑨但是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在李庆的长文里,除了引用李纯一的考证结果之外,并没有发现任何一例标有“行钟”字样的出土文献,也没有任何现存纸本文献可以直接证明“行”是“一种在古代祭祀、宴乐、出行等仪式时演奏的一种特定形式的音乐”。我们考察现存有关汉代歌诗演唱的记录,都没有发现标有“行”字题的作品之演唱与“行钟”之间有任何关系的直接记载。反之,我们却可以找到大量的材料来反驳李庆的观点。首先是关于相和歌的性质,沈约《宋书•乐志》说:“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郭茂倩《乐府诗集》综合汉魏六朝诸多文献所作的关于相和歌清、平、瑟、楚各调和大曲的解题,详细记载了这些相和歌曲在演奏时所用的笙、笛、篪、筑、琴、瑟、琵琶、筝等各种乐器和演奏方法,不要说没有说到“行钟”,连“钟”都没有提到。这说明相和歌的特点是“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其演出根本就不可能用“钟”这种乐器。其次是关于相和歌的起源,《宋书•乐志》说得很清楚:“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晋书•乐志》也有同样的说法。可见相和歌最早的起源当在汉代的街陌谣讴,这与李庆所引录的祭祀四方山川、食举宴乐、君王出行的有关记载也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不对李庆的这一研究结果表示怀疑。退一步讲,假设汉乐府中“行”的演唱虽然没有用“行钟”类乐器,虽然汉乐府相和歌最初属于“街陌谣讴”,是否仍然会受汉代祭祀燕飨出行之乐的影响,仍然有依“行钟”的音阶来演唱的可能呢?李庆同样也拿不出出土文献的证据。反之,我们考察有关汉乐府相和诸调演唱的文献记载,发现只有“平调”、“清调”、“瑟调”、“楚调”、“侧调”等说法,也没有发现其音阶与“行钟”有关的记载。《乐府诗集》引《唐┦•乐志》曰:“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又有楚调、侧调。楚调者,汉房中乐也。高帝乐楚声,故房中乐皆楚声也。侧调者,生於楚调,与前三调总谓之相和调。”《魏书•乐志》载陈仲儒论乐:“其瑟调以角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宫为主。五调各以一声为主,然后错采众声以文饰之,方如锦绣。”以此而言,汉魏六朝清商三调的演奏,并不是以所谓的行钟的“音阶”来进行的。关于清商三调的音律和调式问题,杨荫浏、冯洁轩等人有过很好的探讨。⑩所以,无论是李庆的说法还是清水茂的说法,都是与汉魏六朝有关相和歌诗的记载相背离的,因而他们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其实,关于汉乐府中“行”的问题本来很简单,前人已经有过比较简明的解释:“行”即“曲”也。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司马贞《索引》:“乐府《长歌行》、《短歌行》,行者,曲也。此言‘鼓一再行,谓一两曲。”《汉书•司马相如传》:“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颜师古注:“行为曲引也。古乐府《长歌行》、《短歌行》,此其义也。”又如《文选•饮马长城窟行》李善注:“《音义》曰:行,曲也。”再如《尔雅•释乐》“徒鼓瑟谓之步,徒吹谓之和,徒歌谓之谣。”郝懿行疏:“步犹行也。”可见,乐府诗中的“行”即“曲”,唐以前人无异议。而清水茂却根据“为鼓一再行”这句话的句法结构,认为“再”是副词,不应该用在名词之前,所以这句话里的“行”应该是动词,自然也就不应该解释为有名词意义的“曲”。其实,“再”在古代,它的最初意义恰恰是量词,表示第二次的意思。《玉篇•冓部》:“再,两也。”《史记•苏秦列传》:“秦赵五战,秦再胜而赵三胜。”所以,《史记》和《汉书》的表述没有问题,司马贞把它解释为“一两曲”也是正确的。“行”的意义就是“曲”,那么汉乐府清平瑟调与大曲歌辞中有标有“行”字,就可以有很简单的解释,《长歌行》就是“长歌曲”,《猛虎行》就是“猛虎曲”,《东门行》就是“东门曲”,以此类推,本无深义。它与春秋战国之际的“行钟”没有任何联系,在汉代也不存在“行”这种“依‘行钟音阶的乐曲”。
在此,我们还要解释清水茂和李庆等人的一个疑问,为什么在汉代歌诗作品里,主要在平调、清调、瑟调、楚调和大曲中的歌辞题目中标有“行”字呢?逯钦立有一句话富有启发性,他讲:“我们试从现存的‘相和歌辞看,凡是‘相和歌本身不分解,都不叫‘行。”(11)的确,如果我们考察《宋书•乐志》,会发现“相和”下面各首歌的题目中均无“行”字,各诗中也没有“解”,而平调、清调、瑟调和大曲下面各首歌的题目上都有“行”字,各诗又全部都有“解”,少则两解,多则八解。因此我认为,汉乐府相和诸调歌诗中之所以标有“行”字,最初只是为了区分相和曲与清、平、瑟、楚诸调以及大曲的区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平、瑟、楚诸调曲和大曲的歌辞大多数都在二解以上,因而才把这些没有“解”的歌曲称之为“行”。当然,歌辞分解,也就是歌曲分章;歌辞分几解,曲调也就重复几遍,重复乃是其应有之义。这也正是这些清、平、楚、瑟和大曲在标题上加一“行”字以标示其与相和曲不同的原因。
顺便提一句,李庆在统计《乐府诗集》中标有“行”字的作品时,把从汉到魏的所有作品一样看待,这种做法也有问题。其实,魏晋以后许多标有“行”字的作品已经属于文人的拟作,它们根本就不入乐,只是沿袭了乐府旧题。这对于弄清“行”字本义没有帮助,反而容易把问题混淆。作为现存汉乐府歌诗,最早最可靠的文献记载就是《宋书•乐志》。其中所辑录的相和曲标题均没有“行”字,而自平调曲以下诸调曲则全有“行”字,并且每一首歌辞都有“解”字。这正证明了汉乐府相和诸调发展的历史——它由最初不分“解”的相和曲,发展到可以分“解”的平、清、瑟、楚诸调,再发展到前有“艳”曲、后有“趋”与“乱”的大曲,其艺术形式在不断发展。同时,这些标有“行”字题目的乐府歌诗也代表了汉代歌诗艺术表现的最高形式,所以后人便把由此引申而来的乐府体诗歌也称之为“歌行”,从而成为一种由此而演化出的一种新诗体即“歌行体”的名称。
以上,我们由清水茂《乐府“行”的本义》一文说起,不但是为了辨析汉乐府“行”的本义,而且想要说明的是:利用出土文献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这要看出土文献本身提供多少有用的信息,而不能把它的文献价值无限扩大,企图解决所有与之相关甚至毫无关系的问题。我们之所以看重出土文献的价值,是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实证材料。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可能就会变成谬误,因为它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
注释
①《文学前沿》第2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②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考古学专刊乙种第5号。
③郭沫若:《由寿县墓器论到蔡墓的年代》,《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④陈梦家《寿县蔡侯墓铜器》,《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⑤李纯一:《关于歌钟、行钟及蔡侯编钟》,《文物》1973年第7期页。
⑥⑦⑧清水茂:《乐府“行”的本义》,《清水茂汉学论集》,中华书局,2003年,第339、339—340、340页。
⑨李庆:《歌行之“行”考——关于郭茂倩〈乐府诗集〉中“行”的文献学研究》,《中国诗歌研究》第五辑,2008年,中华书局。
⑩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第132—133页。冯洁轩:《清商三┑•笛上三调》,《音乐研究》(季刊)1995年第3期。
(11)逯钦立:《“相和歌”曲调考》,《文史》第十四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225页。
责任编辑:行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