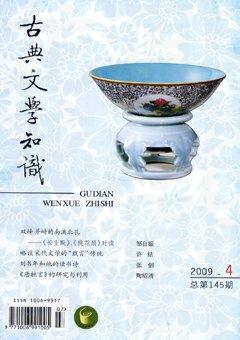王勃在初唐“文儒”发展中的价值和意义
李 伟
前人虽没有直接评价王勃在初唐“文儒”发展中的价值意义问题,但是以往对“四杰”文学的认识仍然可以启发我们深入思考作为其重要成员之一的王勃在初唐“文儒”史的位置。其中以日本学者道坂昭广先生的认识最具价值。他认为初唐“四杰”是初唐时期失意文人的代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怀才不遇的精神痛苦和悲凄无奈。因此道坂昭广先生说:“怀着对自身才能的强烈自负却不得不作为下级官僚辗转各地,这种苦涩的情感不仅属于四杰,也属于众多同时代的人们。四杰正是他们的象征,起着代言人的作用。他们是由自身所属的新兴士大夫阶层选出的,决不等同于那种南北朝时期基于单一文学理念的沙龙的代表者。而且,正因是代表者所以或多或少具有一种‘模范的意义。相对于此,四杰则具有从同一立场出发的人们的代言者的意义。”(道坂昭广《四杰考》,《唐代文学研究》第十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由此可见,“四杰”具有与当时其他失意文人同样的遭遇和情感,只不过这些遭遇和情感在“四杰”身上更突出、更强烈,因此就具有一种“代言人”的作用和“模范”的意义。这种研究心得与傅璇琮先生用《艺术哲学》提供的方法论研究唐代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傅先生在《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序言》中曾引用过《艺术哲学》的一段话:“艺术家本身,连同他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流派或艺术家家族。……到了今日,他们同时代的大宗师的荣名似乎把他们淹没了:但要了解那位大师,仍然需要把这些有才能的作家集中在他的周围,因为他只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只是这个艺术家庭中最显赫的一个代表。”(《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自序,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这里傅先生倡导的是以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尽可能地恢复文学发展的社会大背景。就唐代文学来说,傅先生认为唐代的大作家“是这个艺术家庭中最显赫的一个代表”,但他的背后却有着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因此在研究大作家的同时必须把他放置于“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流派或艺术家家族”中,才能尽可能真实地探究本来面目。可见这种大作家与其身后背景的深层关系正好可以印证道坂昭广先生所言之“四杰”作为“代言人”对当时他们“自身所属的新兴士大夫阶层”的作用和意义。就这个方面来讲,王勃作为“文儒”之对于初唐“文儒”的价值正在于他是这个时代中最具“文儒”本质的士人,不仅有着世业不坠的儒家文化传统,其祖父隋末大儒王通的文化思想沾溉初唐的文化建设,这对王勃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王勃能把这种儒家文化思想与文章创作紧密结合,真正实践了“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的儒士文艺观念,因此王勃在理论认识和创作实践方面都堪称初唐时代最具典型意义的“文儒”。葛晓音先生在《盛唐“文儒”的形成与复古思潮的滥觞》一文中对此的认识可供参考,兹不赘述。
王勃作为初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儒”型士人,他与所处的时代是极不协调的。在王勃之前,太宗以圣明君主的气魄和雄才伟略在国家安定之后积极发展文化事业,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讨论坟典,商略政事。这种发扬儒家思想以应用于政治建设的风气影响所及,太宗周围的许多文士在文化个性和文章创作上以“文儒”的标准自期,并在编撰史书中贯彻了这种理论思想,与太宗积极倡导的文化建设构成了思想深层的回应。在王勃之后,玄宗结束了从高宗到中宗的动荡政局,积极改革弊政,任贤举能,大兴礼乐,把儒家思想中的礼乐文化真正落实到现实政治的运作中,由此产生了一批以张说为代表的“文儒”型文士。他们不仅在政治实践中遵循玄宗发展礼乐文化的方针,并以自己丰厚的文章创作更加充实了这种文化建设。但是王勃出生于高宗永徽元年(650),于高宗上元三年(676)溺水而卒。他生活的主要时段是在高宗时期,因此既没有赶上太宗“贞观之治”的文化复兴,也没有遇到玄宗“开元盛世”的文化鼎盛,这两个“文儒”得其幸的时代恰好与王勃擦身而过。而王勃生活的时期却是文吏受到重视的时代,《旧唐书•儒学传》曰:“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于是醇日去,毕竞日彰,尤火销膏而莫之觉也。及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其国子祭酒,多受诸王及驸马都尉,准贞观旧事。祭酒孔颖达等赴上日,皆讲《五经》题。至是,诸王及驸马赴上。唯判祥瑞按三道而已。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是时复将亲祀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岳,将取弘文国子生充齐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选,前后不可胜数。因是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矣。”可见高宗朝已与太宗的文化政策大不同了,武则天也开始笼络人心,为夺取帝位作准备。因此儒学的地位极为势微,经学生徒亦放弃儒学大义而转向“苟希侥幸”。生于这样的时代,世奉儒学的王勃可谓大不幸了。而且当时朝廷选拔官吏的标准也以“吏才”为上。最明显的是裴行俭认为王勃等人“华而不实,鲜克令终”,其所赞赏的李峤、苏味道等人都是以“文吏”见长,这与黄永年先生分析的裴行俭选才时重吏才而轻文华的倾向是一致的。(黄永年《“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正义》,《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版)因此在这些文吏眼中,儒家提倡的礼乐王道思想不合实际,“文儒”所学空疏迂阔而不能适应社会政治的复杂情势,有脱离现实的危险,根本不能与那些具有现实行政经验的文吏之才相提并论。由于这样的不同,王勃被裴行俭摒弃于入仕之外,无法实现儒家灌输给他的治国平天下的宏愿。
虽然这种偏见对王勃的仕途不啻为毁灭性的打击,但是这正好成全了王勃可以成为出色的文学家。儒家思想中的抗礼王侯、独立自由的人格让他以非凡的姿态面对仕途的艰险,总是在自己的理想中以一种近乎梦幻的情结编织着平交王侯的快意和君臣风云际会式的遇合。这使他在现实的残酷面前总是显得那么天真自然,给他的文章中贯注了不受拘束的个性之气。而仕途受阻的打击带来的沉重并没有使他退缩逃避,而是将一腔愤激悲慨的怨情以“不平之气”的形式发泄于文章创作中,接续前人“发愤以抒情”和立言以不朽的优良传统,在继承了梁陈文风华美的基础上又加之以深厚郁勃的情感气质。不论王勃是在积极入世时高扬“拾青紫于俯仰,取公卿于朝夕”的豪迈,还是在失意困苦中忍受“志远而心曲,才高而位下”的沉郁,他的文章中都充满了士人由追求理想、坚持独立人格而自然生发出的“气势”,从而在创作中显露了文风变革的新趋向。
文学的演变不一定与政治的剧变完全一致,王勃虽然没有生逢儒学昌盛、“文儒”得势的幸运时代,但是他的文学却呈现出承前启后的过渡性特征,从文化的深层联系了太宗朝和玄宗朝“文儒”创作发展的延续脉络。王勃积极入世时所创作的颂体文和干谒文章,其宏阔壮大和气势雄豪的艺术风格是对太宗时期艺术审美特征的继承。太宗曾于贞观十八年(644)作《帝京篇》十首并序。在诗序中,太宗表达了创作此诗的文化目的,即“追踪百王之末,弛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簟!…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神人,皆节之以中和,不系之以淫放。……释实求华,以从人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致云尔”。可见太宗是以创作《帝京篇》意图恢复儒家王道理想,推进儒家文教思想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完成“皆节之以中和,不系之以淫放”的中和审美观的建立,因此太宗的《帝京篇》创作主要是从国家的文化制度方面着眼,带有浓厚的儒家礼乐文化色彩。但《帝京篇》在艺术风格上继承的是汉大赋的美学特征,以诗歌的形式辅之以汉赋的铺叙写法和壮阔气势,从帝都规模、游览林苑、宴饮歌乐、军事田猎等各个方面细致描绘当时政治安定、国家繁盛的恢弘景象,具有壮阔张扬的豪放之气,胡应麟《诗薮》曰:“唐初惟文皇《帝京篇》藻赡精华,最为杰作。视梁陈神韵稍减,而富丽过之。”当时太宗赞扬李百药对此诗的和作“才壮思新”,其中便流露出太宗欣赏“壮美”气势和“富丽”的审美观念。这深刻影响了王勃那些颂体文的创作动机和艺术风格,即杨炯赞赏的“容气以广其灵”和“争发大言”的特色。“争发大言”是对描写物象如宫殿、礼仪的全面细致的描绘,如《乾元殿赋》等;“容气以广其灵”是铺张扬厉带来的气势。这种铺叙的写法和壮阔的气势极类似于汉赋,具体到汉赋作家,就是对初唐文化有深刻影响的班固。杨炯曾以“壮思之雄宗”和“反诸宏博”评价王勃的文学特点,而这与班固及其《汉书》的审美特色是相似的,如颜师古《上汉书注序》:“观炎汉之余风,究其始终;懿孟坚之述作,嘉其宏赡。”因此,王勃文学特征的形成与班固文风影响下的太宗朝文化审美风尚密切相关,即以“宏博”之气变革梁陈以来的“积年绮碎”。
王勃对玄宗朝的影响主要体现于文学观念的总体认识上。《上吏部裴侍郎启》曰:“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骛,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这里就把孔子礼乐文化与屈宋的辞赋创作看做中国文学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关键点。正如《诗薮》中所言“四言典则雅淳,自是三代风范。宏丽之端,实自《离骚》发之”。王勃认识到这种美学上的转变实际有其价值观念上的“正邪”之分。葛晓音先生于《论建安南北朝隋唐文人对建安前后文风演变的不同评价——从李白〈古风〉其一谈起》一文中有精当的分析:“如果说刘勰还承认《离骚》的忠怨同于风雅的话,那么,自王通以来,‘大雅的含义已越来越明确地被归结到‘颂美这一点上,这一观念正是唐人批判楚骚之哀怨的基本出发点。”因此王勃既然要以颂美的观念规范《诗经》代表的儒家诗教传统,那么屈原那些“发愤以抒情”的辞赋自然不合其观念主旨。这一点在当时很多文人那里得到回应,其中以卢照邻和杨炯最突出,卢照邻的《驸马都尉乔君集序》:“昔文王既没,道不在兹乎?尼父克生,礼尽归于是矣。其后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衰衣;屈平宋玉,弄词人之柔翰。礼乐之道,已颠坠于斯文;雅颂之风,犹绵连于季叶。”(《全唐文》卷一六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杨炯的《王勃集序》曰:“仲尼既没,游夏光洙泗之风;屈平自沉,唐宋弘汨罗之迹。文儒于焉异术,辞赋所以殊源。”两人都把孔子到屈原的文学发展视为文学史的剧变,以后凡是不合儒家审美规范的文风都被归咎于屈原创作的不良影响。这与王勃的认识是一致的,与把“大雅”传统归结于“颂美”一端紧密相连。这种认识深刻影响了盛唐时代的文人,如李白的《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萎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就是明显继承了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的文学观念,把“大雅”视为“正声”,而把屈原的创作排斥于“正声”之外,不合儒家审美标准。其他如张说、张九龄等人都是如此,张九龄《陪王司马宴王少府东阁序》云:“《诗》有怨刺之作,《骚》有愁思之文,求之微言,匪云大雅。”(《全唐文》卷二九〇)可见“他在理论上则是将《诗经》中的怨刺之作和楚骚的愁思之文统统排除在‘大雅这个概念之外的”。因此王勃的《上吏部裴侍郎启》对盛唐“文儒”的文学观念影响很深。
综上所述,王勃在唐代文学史和“文儒”的发展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前承太宗开创的文学艺术风格,后启玄宗时期成熟“文儒”的文学观念认识。而王勃的文学成就中也明显带有过渡色彩,如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曰:“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虽是针对四杰而发,王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也与此一致。因此美国学者宇文所安说:“初唐诗比绝大多数诗歌都更适合于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研究。孤立地阅读许多初唐诗歌似乎枯燥无味,生气索然,但是当我们在它们自己时代的背景下倾听它们,就会发现它们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活力。”(宇文所安《初唐诗•致中国读者》,三联书店2004年版)这即是启示我们以一种文学史的流动眼光对待王勃这样的初唐作家,其伟大价值才能走出以往那些大家的阴影并得到应有的肯定,王勃在初唐“文儒”的发展中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