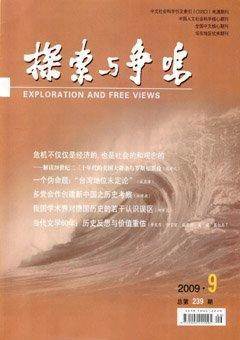逃离与回归:乡土中国教育发展的两种精神路向
内容摘要 20世纪初,以鲁迅和沈从文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乡土中国与现代性的相遇时,传达各自不同的立场,一种是启蒙—改造型,一种是回归—保守型。不同立场意味着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全然不同的价值位序。由于现实的危难,中国社会的历史选择乃是启蒙—改造型的社会发展路向,以致乡土中国与外援性的现代化之间的内在紧张问题被遮蔽。这直接导致当下置身现代化的过程中个体的内在精神资源的缺失。今天,在乡土价值在现代教育体系中阙如的背景下,沈从文的立场难能可贵。怎样面对乡土中国的悠远传统,深度阐发乡土社会的内在意蕴,并以此作为现代教育的精神基础,拓展当下教育的可能性,理应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
关 键 词乡土中国 现代性 教育 教育发展 启蒙—改造型 回归—保守型精神路向
作者 刘铁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985”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5)
历史进入21世纪,乡土中国以何种方式迈入现代性的门槛,不仅涉及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当然,更直接涉及乡村社会在现代化中的位置,也更深刻地影响了我国乡村社会教育发展乃至整个现代教育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理路。对此,鲁迅与沈从文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对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
鲁迅与沈从文:面对乡村社会的两种姿态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精神杰出代表的鲁迅和沈从文,由于他们的出身、性情、文化背景等的差异,以及他们与乡土中国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精神联系,使得他们在关注乡土中国的同时,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与乡村教育的内在理路呈现出全然不同的精神脉象。
鲁迅对乡村社会的姿态,经历了一种由起初充满着美好的幻象而变得消极的过程。留给鲁迅的印记,主要是阿Q、祥林嫂等一批代表国民劣根性的人物。鲁迅面对乡村社会的姿态更多的是一种启蒙的姿态,或者叫做铁屋子里的呐喊,他是要喊醒在乡村大地上沉睡的人们。而从小生活在湖南湘西凤凰小城的沈从文,因为年少时期与湘西美丽乡土的亲密接触以及对湘西少数民族民风民情的耳濡目染,形成了一种以“乡下人”自居的生命姿态。当沈从文从远离现代性的边缘进入到现代性的中心,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是对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生活的惶恐和对乡下人生存姿态的坚守。他正是置身于对现代性的必要的芥蒂与惶恐之中来寻求自我精神本体的存在,他极力表现的就是与现代性保持着必要距离的生命世界,传达古老的湘西大地孕育出来的一种充满田园诗意的生命姿态。
如果说鲁迅的乡下人身份是客串的、临时的,那么沈从文的乡下人的姿态就是源自生命深处的,甚至可以说是其全部文化精神的源泉。而作为启蒙者的鲁迅,他身上的文化精神显然并不是来自他的乡村生活经历,而是 “别求新声于异邦”[1]。乡村社会对鲁迅而言乃是他者,对沈从文而言就是自我存在本身。沈从文成就于湘西这一块风土人情和他所浸润其中的乡土文化,而他所生活的乡村文化又通过他表现出来,沈从文和他所代表的乡村文化是互为一体的。鲁迅和沈从文也因此代表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乡土中国与乡村社会的两种姿态,一种是作为乡土世界的他者的姿态,一种是作为乡土文化的言说者的姿态。由此,实际上他们所代表的正是现代中国如何应对乡土社会的两种姿态,一种是文化启蒙的、改造的姿态,一种是回归乡土的、略带保守的姿态。当然,这里的“保守”并非简单的怀旧,或者维护旧的社会形态,而是一种生命的姿态,一种接近民族、历史底层,来呵护人性之自然、优美与崇高的文化姿态。更进一步说,这里的“保守”并不是相对于社会变革,而是指涉个人精神生命的守成。
乡土社会在现代性中的不同位序
鲁迅和沈从文尽管都对巨变中的乡土中国怀抱忧虑,但各自面对乡土社会发展的立场大不一样。两个人的差异,源自出发点的不同,一个由于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而使自己置身现代性之中来看待乡土社会,另一个则始终在内心固守着处于现代性边缘的湘西山水世界。现代性意味着一种生存方式的变化,它和传统生存方式表现出一种时间观上的差别。一个是动态的时间观,一个是静态的时间观;一个是站在动态的现代性时间之中看待乡村,一个是站在静态的乡土世界之中来看现代性,两个人持守着不同的时间观。鲁迅的时间观就是以进化论作为重要的思想基础,他看到的历史是滚滚向前的。既然历史朝着向前的方向直线进化,我们就应该剔除时间长河中那些落后的因素,显现出一种维新的品格。在他眼中,乡土及其代表的文明形态,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藏污纳垢的大本营,诸如人身买卖、一夫多妻、缠足拖辫、灵学、吸食鸦片、劫掠残杀等等,“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2],乡下人——无论是闰土、祥林嫂、华老栓、七斤,还是阿Q——身上的“奴隶意识”像传家宝一样代代相传,从不舍得丢弃,他们“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3],麻木又愚蠢,可怜又可憎。“鲁迅以麻木、愚昧、顽固、残忍为乡土作出的定义,参照的背景是一系列现代性的观念,诸如科学、启蒙、进步等知识分子话语。”[4]原始的乡村在他的言说中被作为待启蒙的他者,而被整体地纳入现代性的知识话语体系中。
鲁迅所遵从的生命姿态,就是要去旧维新。“改造国民性”乃是鲁迅一生持守的主题,实际上也是他的乡土社会教化的根本立场。正因为站在这种去旧求新的现代性的门槛上,鲁迅看到的是乡村社会的顽固、静态、守旧,以传统作为基本特性的、停滞不前的乡村社会在转向现代性的过程中是如此迟钝,缺少自我更新的力量。由此,在鲁迅看来,我们必须要进入现代性的门槛之中,中国的乡村社会必须完成现代化。鲁迅以启蒙者的姿态,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他的目标是把传统的乡村社会带进现代性之中,所以才会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如果我们只看到乡村社会落后的一面,乡村社会就只能作为现代化的他者与被改造对象而被动地进入当下的时间中。
沈从文提供的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时间观。他站在静态的时间观上,看到的正是在日益变化的、捉摸不定的现代性的时间中,不变的乡村社会所呈现出来的优美和自然。他执著于自己的“乡下人”姿态,对现代性心存惶恐与芥蒂,他把自己的心安顿在他年少时耳濡目染的湘西田园世界中。在那里,他讴歌人性的自然和优美,并以此来对抗现代化对自然人性的侵蚀。“沈从文的世界是一个取消了时间性的世界。在日升月落、四季更替、生命的轮回这些自然现象的启示下,这里的时间表现为循环时间,时间的指向不是前方。它是圆形时间——如同周而复始的钟表,而不是线性时间。”[5]沈从文在多变的20世纪,守住了一份不变的宁静的乡土。
很显然,在沈从文看来,静态的乡村社会恰恰不是现代化中纯然被改造的对象,因为它是超越现代性的,超越时间的,具有某种永恒性。田园世界中具有的诗意和对自然人性的呵护恰恰应该是现代性的底色。这里体现了沈从文对历史、对人性、对社会发展的整体的、智慧的把握。他敏锐而深切地看到了现代性的变故中,如何“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的书写就是要“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6]。他正是要在这一个变幻的时代中留住某种永恒的依恋,以此来作为变化社会中可以持守的永恒的依据,置身变化世界中的年轻人可以坚守的精神家园。沈从文的执著,乃是要提示我们,现代化不是一切,我们在迎接现代化的过程中,还需要超越现代性的时间,达到对永恒的把握。正如胡塞尔所说:“我们还是必须要坚持,我们始终意识到我们对人类所承担的责任。我们切不可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我们切不可为了减轻我们的困境而将一个又一个的困境作为最终无法根除的恶遗留给我们的后代。”[7]
改造还是保守:对立与互补
鲁迅和沈从文代表了现代中国面对乡土社会的两极。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面对乡村社会显现出的基本姿态是逃离,试图以启蒙者的姿态来唤醒民众,改造乡土社会的愚昧。沈从文则站在另一极,传达出来的是对乡土的依恋,是回归乡土。他呈现的不是一种启蒙者的姿态,而是一种保守的姿态。两个人作为20世纪中国杰出知识分子代表,都是建立在对现代中国内在的焦虑之上,都看到了乡土中国置身现代性之中的民族的危机,只不过由于各自的立场不同,应对危机的路径也各不相同。
鲁迅看到的是国民性中的愚昧,要把国民带入到现代性的追求之中。鲁迅提出要建立“人国”,先“立人”,再“立国”。他是要让现代国民如何不被时代所淘汰,要让乡土中国置身于现代民族之林,走出在中国传统社会“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的循环,给中国人赢得现代国民的资格。建立人国,这是鲁迅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他改造国民性的基本旨趣。沈从文看到的是同样的问题,他同时又对现代性有一种刻骨的芥蒂,对未来的命运不可知。同时他也发现国民,特别是湘西村民,在现代性的各种变故之中凸显的自私、狭隘、愚昧等。但他提出的救治药方是不一样的,他要以民族的底色、自然的人性来救治现代性可能带来的存在的虚空,同时矫正乡村世界中正在荒疏的人性。他选择的方式不是逃离、出走,恰恰是回归,回归民族的底色,回归自然的人性,试图从这里开始,重新激发年轻人的正直和热情,同时又保有民族的底色。鲁迅是要争取个体置身现代社会的资格,而沈从文是给予生命根底的一种温润。一个关注的是可见的,和时代步伐的吻合;一个关注的是不可见的,是超越时代的。一个提出的是改造型的教育路向,一个提出的是保守型的教育路向。
如果说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教育设计理路乃是要培育“真的猛士”[8],在现代民族国家之林中建立中国作为人之国;那么,沈从文的教育设计则是要给在现代性的旋涡中淘空了民族底色的现代国民以鲜活、自然而丰盈的人性内涵,让人们“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热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刺激人们,引起人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的怀疑”,[9]“让正直和热情……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或梦里”,并“重新燃起年青人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以“坚韧和勇敢”,战胜“民族忧患”。[10]
在民族遭遇千年未有的大剧变之时,鲁迅更多地在不变的现实中求变, “表明了他全面接受西方主导的现代生存原则的决心,开始以‘人类的眼光代替‘民族的眼光”[11];而沈从文则强调在变动的现实中求不变,直面“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12]。如果说鲁迅的启蒙与改造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主流,体现了民族国家生存与发展在现时代的根本性需要;那么沈从文的回归与保守则体现的是民族国家融入现代性的背后赖以维系的、千百年来纠结于乡土中国深处的人性的、民族的生命底色,是对于置身现代性中的国民何以安身立命的生命根底的温润。单从个体安身立命的视角而言,鲁迅更多地关注的乃是人格的建立,而沈从文则更多地关注的是个体安身立命的人性基石和情感孕育;鲁迅更多地关注人格的独立,沈从文更多地关注人性和人情的丰富性,以抗衡个体人生可能遭遇的现代生活的单一性的冲击。
变与不变,无疑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的根本性主题。不变不足以求生存,变是绝对的;但变中又应有所不变,不变是为了孕育个体生命与民族生存的精神根底,不至于浮躁,失去朴素的底色。设计性的发展理路是要使民族与教育的发展从过去的窠臼中摆脱出来,使民族走上新生的道路;保守性的发展理路则是要使民族保持自然与历史深处的精神血脉,保持民族朴素而生动的精神根底。不管怎样,鲁迅和沈从文都是站在乡土中国的大背景上,都真切地把握了置身现代性之中的民族发展的危机,并从各自的立场开出了至今依然发人深省的疗治的路径。他们在面对乡土中国说话时,实际上是在面对整个民族社会的发展说话,他们关切的乃是我们民族发展的历史与命运。
乡土中国的历史选择与时代处境
鲁迅和沈从文,面临相同的背景,都怀着对“历史上能负一点儿责任”[13]的态度,以及对乡土中国何以进入现代性的忧虑,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看到乡土社会不同的一面,从而传达出乡土中国教育发展的不同精神脉象。他们在表面上是两种对立的立场,但实际上是我们今天置身现代性中何以面对乡村社会与乡村教育的两种互补的态度。两个人的思想结合起来,足以构成现代中国教育精神的完美结构,既能适应时代的脚步,又能保留民族的底色。但历史的选择并非如此,由于现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吁求压倒一切,社会发展的精神脉络是由五四运动的启蒙,到随后的革命,再到1949年后的建设,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成为贯穿其中的、压倒一切的主题。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历史选择的是鲁迅所开创的启蒙—改造型的设计理论,尽管鲁迅启蒙的“改造”和后面以革命主题为中心的“改造”有很大的区别,但后来革命中的改造理路,以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改造理路,实际上都是鲁迅等人所开启的去旧布新的设计—替代型教育理路的延续。
由于现代中国的核心问题是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一现代性的中心问题,长期贫弱中的中国社会首要的目标是急切地迈入现代性的门槛中,乡土中国的问题实际上遮蔽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这一中心问题中,从启蒙到革命,从革命到建设,不同阶段不同主题的嬗变,都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之中。就整体而言,乡土中国的内在意蕴并没有进入现代中国的教育视野之中,沈从文的教育理路在宏大的社会主题面前是被遮蔽的,仅仅保存在少数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之中。以陶行知等人为代表的乡村教育运动,实际上所体现出来的教育精神也不是保守的,而是以适应现代生活为目的,显现出改造乡村社会的精神旨趣。尽管他们在外在形式上和乡村社会靠得很近,但更多地倾向于对乡村社会表层的适应,而并没有足够深入到沈从文所开启的民族的、文化的、生命的世界之中,其内在的教育理路,迥异于沈从文的教育理念。实际上,沈从文扎根乡土的教育理念一开始就是寂寞的、非现实化的。
中国的现代教育在不断地谋求与西方接轨的过程中,首先是学日本,然后学美国,再学苏联,实际上失去了民族的生命的底色,这直接导致了20世纪现代中国教育内在精神的整体贫乏。值得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后期应试教育之所以风起云涌,长盛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世纪的中国没有充分地立足于乡土中国的现实背景,有效地培育出现代中国教育的内在精神血气。这种精神血气的来源,一是千百年来沉淀在历史深处的民族精神底色,一是生命原初的底色,也就是自然人性。我们在追求现代化的宏大目标中,失去的恰恰是对历史深处的民族精神底色的悉心呵护和对自然人性的眷顾,使得我们社会的教育设计疏于去培育个人生命的精神之根,也就失去了当下教育本身的鲜活血气。
中国社会在谋求以城市化为内容,以物质的现代化为中心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忽视了乡土中国的社会底蕴。直白地说,就是我们的现代化并没有积极面对乡土社会的问题。我们不乏浪漫的现代化想象,一开始表现出来的就是设计型的思路。我们急于从传统中脱身而出,以致在走出传统的伦理化社会的同时,也把乡土中国民族与历史的底蕴全部抛开,从而使得我们的现代化并没有扎根于乡土中国的历史底蕴之中,并直接导致我们的现代化追求的本土性问题。这从我们当下的教育改革可见一斑。乡土社会自身的价值意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而更多的只是作为革命、历史、民族国家、现代化、城市化等宏大主题的点缀。教育与乡土中国内在价值的剥离,乃是我们当下教育精神贫乏的重要原因。大量移植的西方教育理念与教育现实之间构成了某种紧张,其根源之一正在于我们的现代教育追求与乡土中国底蕴之间的疏离。今天,我们的教育更多地是建立在对当下生活世界的适应之中,教育的形式喧哗,但教育的内在视野并不开阔;教育的外在条件与形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教育的深度和广度,教育的境界并没有相应的扩展。不仅如此,由于现代化无所不在的卷入性特征,直接导致当下教育的同一化、去个性化,导致教育品质的单一性。回顾鲁迅和沈从文当初的思考,让我们重新面对乡土中国这一当下中国社会与教育发展不可忽视的基础性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重新回归鲁迅和沈从文他们思想出发的地方,回到现代教育的原点,重新审视、探寻现代教育与乡土中国之间内在而生动的联系。
乡土中国的价值选择与教育重建
今天,我们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乡土中国历史传统对当下个体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造成的我们与现代生活之间微妙的紧张,由此而启迪我们思考,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现代化,更直接地,我们需要哪种作为现代化内在支撑的精神资源?乡土中国与当下教育发展的内在精神联系问题,再一次严峻地显现在我们面前。
由于历史的选择更多偏向设计改造型的教育理路,就目前而言,我们在全面审视当代教育与鲁迅立人理想之间的距离的同时,更需要关注沈从文的教育理想,关注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回归乡土的保守型教育理念。换言之,沈从文的教育理念在今天有着特别的意义,表现在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一是对民族精神底蕴的理解;二是对人性自然的回归。重温沈从文的乡土理念,就是要给予我们当下越来越多沉迷在技术训练、流行文化、物欲的追求之中的青少年,以另一种形式的精神滋养激活他们的生命形态,激活他们人性自然中被遮蔽的热情、正直、温热的生命世界,从而给他们的生命存在以质朴的、富于民族底蕴的精神滋养,以对抗当下教育的功利化、同质化、去民族化,这是我们今天重温沈从文乡土理念的根本要义之所在。就这个意义而言,沈从文的教育理想不仅仅是面对乡村社会,而是面对整个现代中国。他直接关涉的是当下国民的精神脉象,关涉当下国民置身现代性中依然难以勾销的内在紧张的缓解。鲁迅下的是猛药,沈从文下的是温补的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正是温补,一点点裨补精神的根基。
接近乡土,回归自然,并不是要彰显现代人的优越感,而恰恰是弥补我们当下生命的缺失,是重新甄定我们生命的出路,是我们当下生命发展本然的需要。只有我们认识贴近乡土、回归乡土,乃是生命本然的需要,是置身现代化过程中的国民精神发展的需要,我们才可能发自内心地去呵护自然、理解乡土,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其中就包括人与外在自然、人与自身的和谐。当代教育涉及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今天的孩子们是否还有可能把乡土作为自己生命的资源?乡土中国作为教育背景的缺席,直接导致乡村社会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被边缘化,即使是乡村社会在教育中得到了足够的呈现,但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我们对乡土的利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功利的色彩,不足以作为儿童发展的本体性精神资源,即以乡土中国作为个体生命认同的基于审美的精神支持。乡土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某种宗教的意味,所谓叶落归根,魂归故里。这意味着在现代性的社会中怎样重建乡土社会的本体价值,而不是以俯视的姿态把乡土作为工具,简单地纳入当下中国人的生命品质之中。这实际上是缓解当下国人的生存的焦虑,扩展生命意义的可能性的重要的途径。这不仅仅是立足于乡村,而是立足于现代性,立足于国民精神的健全发展。正因为我们是要面对现代性来谈论乡土社会与乡村教育,乡村教育的空间就大大地扩展,它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今天中国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我们又要避免把乡村社会与乡村教育过于理想化。这里至少有两点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当下的乡村社会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不同于鲁迅笔下暗淡的故乡,同样也早已不是沈从文的带有乌托邦意味的纯美的边城。我们需要直面当下乡村社会本身的问题,发掘潜在的教育资源,而不是一味地把乡村社会浪漫化。实际上沈从文同样表达了对乡村社会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忧虑,他不过是要以其中还存留着的鲜活的人性来对抗日渐衰微的人心,他是要“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来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加以解剖与描绘”[14]。理想的乡村同样需要、甚至也只能在我们的想象世界之中,在对现代教育的整体筹划中建立起来,以甄定个体精神发展的方向。换言之,现实的乡村生活同样是需要建设与引导的,以鲁迅的思想为中心的改造与建设的乡土教育观实际上很长时间都还是我们乡村教育设计的主导性路径。二是乡村社会与当下社会整体的现代化是紧密相连的,我们不可能让乡村游离在社会的现代化浪潮之外,哪怕这种现代化是单一的、有问题的,我们也没有阻止乡村社会求富裕的权利。因此,我们在教育中、实际上不存在过分地渲染乡村价值与乡村生活的可能性。我们只可能是在促进乡村社会适应现代化的过程中,促进乡村生活的内在转向。
不管怎样,改造国民性是我们社会没有完成的主题,乡村怎样以积极的姿态融入现代性之中,重温鲁迅的主题乃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重要的社会主题,也将是我们乡村教育的基本出发点。我们需要看到乡土社会对现代性不适应的一面,而不至于重新陷于保守与封闭。与此同时,我们又不能不重新面对这些基本问题:究竟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教育的现代化?什么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何以面对永恒?人的现代化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有着本质性的区别,自然与人文之间的平衡乃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教育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必须要在自然与人文之中保持恰当的平衡。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和沈从文,一个都不能少。
参考文献:
[1][2]鲁迅. 鲁迅全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5、 327.
[3]鲁迅. 我谈“堕民”. 鲁迅全集(第5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17.
[4][5][11]祝勇. 出走与归来. 十月,2006(4).
[6][12]沈从文.《边城》题记. 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82.
[7]胡塞尔,吕祥. 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109.
[8]鲁迅. 鲁迅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77.
[9][13]沈从文. 从文小说习作选. 上海:上海书店,1990:代序、7、8.
[10][14]沈从文. 沈从文小说选(下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341、344、341.
编辑 叶祝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