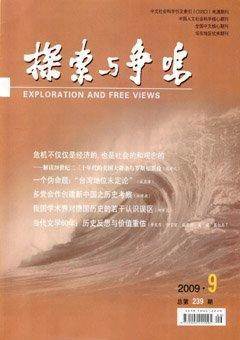从医保制度的内部权力结构看医改路径
内容摘要 在医保制度中,作为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医方,是医疗服务需要的实际创造者,具有左右医疗服务消费需求的能力。由于现行的医保制度仍然主要停留在需方策略的层面进行成本制约机制建设,医保成本过高的问题未能得到有效遏制。要成功架构医保制度的成本制约机制,医改的路径必须实现从需方策略向供方策略转变,重构医疗保险制度中各利益主体间的权力结构,削弱医生控制其收入的权力,彻底改革某些医方主导市场来为自己所属部门、所属群体谋私益的局面。
关键 词医保制度 权力结构 供方策略
作者 程福财,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博士。(上海:200020)
医疗资源浪费严重、成本过高,是当前我国医疗保障制度(以下简称“医保制度”)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一问题的出现,固然与人口老龄化、慢性病的滋生蔓延等因素有关,其根本原因却是现行医保制度的成本制约机制的滞后、失效。医疗消费过程中医患双方出现的败德行为,严重侵蚀了有限的医疗资源。如何在有效保障国民基本健康的同时,把医疗成本控制在政府财政可以支付的范围内,是中国医保制度改革一直试图有效回应、却仍未能如愿的课题。本文试图从对医保制度内部权力结构的分析开始,探讨医保制度的成本制约机制的重构问题。
医保制度的内部权力结构
从客观上看,除医疗保障机构与作为受保人的患者外,医疗保障制度的实施还需要医方(即医疗服务机构)的介入。而由于医方的介入,医疗保障制度中的利益关系格局变得错综复杂,形成了“病人看病,医院行医,保障机构出钱”的第三方付费的特殊消费模式。正是这种特殊消费模式的存在,造就了医保制度内部独特的权力结构,进而为医疗消费过程中的资源浪费提供了制度性可能。
具体而言,在对医院的补偿机制由完全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向政府投入与医院部分自给转变之后,因为维生赢利的需要,作为医疗服务“供方”的医疗服务机构被迫(也是十分情愿地)把“创收”摆在重要的位置上。医院数量庞大的职工的工资奖金、逐年累积起来的离退休人员的生活费、对利益本身的理性追求等都使得医院把相当的精力用于创收,以维持医院自身的运转。但是,一方面医院的创收行为、以赢利为目标的医疗服务,与传统的医道医德习俗格格不入,备受人们怀疑与贬斥;另一方面,医院之间的竞争,使得患者的分流势不可挡。同时,保方(为民众享受医疗服务提供保障的医疗保险机构)的“总量控制、结构调整”等成本制约机制的实施,也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医院的收益。因此,在医改中,医方常常陷入缺乏足够资金维持自身运转的窘迫境地。
上述窘迫境地的存在,迫使医方采取行动,最大限度地调动自己的资源以扩大自身的自由余地。在这里,医院、医生手握的专业权力成为了医方扩大自身自由余地的最重要资源。从资源分配的角度看,医疗服务供求双方的信息严重不对称。病人生了什么病,该吃什么药,应实施怎样的治疗康复方案等问题的决定权,统统都归属医生医院。这使得医方在医疗服务消费过程中实际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权力:既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又是医疗服务需要的创造者,具有左右医疗服务消费需求的能力。这种关系结构和医保的“第三方付费”的特点相结合,为医方主导市场、诱导医疗服务消费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医方的道德风险,提供了制度性基础与可能,为医方的“创收”开辟了足够的空间。现实中,医方的道德风险通常表现为:利用医保制度的缺陷,采用过度使用医疗资源的方式“以药养医”、“小病大治”,大量吞食有限的医疗资源,而非以最有效的方式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可见,在医、患、保三方关系中,如何制约医方的行为,让医院、医生合理地使用医疗资源,是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必须处理好的重要课题。
1990年代医改前的患方基本上是无偿消费医疗服务。这种拿国家的钱为自己看病的对患者的补偿机制,使得来自患方的道德风险严重生发。“小病大医”、“一人劳保,全家受益”等浪费医疗资源的行为频频出现。为了形成对患方的成本制约机制,现行医保制度强调了个人部分付费的意义。从逻辑上讲,这对患者费用意识的树立、对医保成本过快上涨之势的遏止等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医疗消费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医治的持续时间与必需的医疗费用始终决定于防治疾病的实际需要。因此,对于一个以确保民众基本健康为目标的医保制度,控制来源于患者方面的道德风险的措施,效度并不明显。一方面患方付费太多不利于对民众健康的保护、违背医疗保健的社会性与公共性;另一方面在医疗服务消费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患方,而是医生、医院。如何把医方从“医患合谋”中剥离出去,正是医保制度成本制约机制建设的关键所在。
作为医疗保障机构的“保方”,是医保制度的组织者、监护者,担负着维持医保制度良性运转、保证民众基本健康的责任。如何杜绝医保领域中道德风险的发生、提高医保制度的效率、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又不妨碍民众基本健康的保障,是保方在医改中必须处理好的矛盾。
现行医保制度的成本制约机制分析
显然,医疗保障制度成本制约机制建设面临的困境主要源自其中利益主体的增多、医疗服务的第三方付费的消费模式、医方在医疗服务消费过程中的特殊权力。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现行的医保制度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规约医方的行动,而是通过提高患方的成本意识来努力达成成本的节俭。近10年的运作实践表明,这种制度安排并未奏效。
我国现行的医保制度是以国务院在1998年颁布的《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为蓝本构建而成的。这个《决定》试图同时限制患方和医方的道德风险行为。为了规范患者的医疗消费需求,《决定》施行“统账结合”制,规定个人需要为自己的医疗消费预先缴纳医疗保险费,并在消费医疗服务的过程中支付一定比例的医疗费。例如,《决定》确定统筹基金的起付标准原则上控制在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左右,最高支付限额原则上控制在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的4倍左右。起付标准以下的医疗费用,从个人账户中支付或由个人自付。起付标准以上、最高支付限额以下的医疗费用,主要从统筹基金中支付,个人也要负担一定比例。为了防范医方滥用医疗资源,《决定》还加强了对医疗服务的管理:一是引进竞争机制,促进医疗市场的公平竞争;二是加大对医疗费用的监督;三是改进对医院的财政补贴办法,医院实行医药分开的财务核算办法。
然而,这种制度安排运转的效果并不理想,医疗资源浪费严重、医疗经费过快增长的问题始终存在,它使政府财政不堪重负,也直接使得医疗保障制度的运转陷入窘境。在各地陆续准备出台新医保方案的细则时,我们有必要对《决定》版的医保制度成本制约机制失效的原因进行分析。根据前文关于医保制度内部权力结构的分析,笔者认为,现行医保制度的成本制约机制在以下两个方面明显滞后。
其一,对患者的制约机制尚不健全,投保人消费医疗服务时须支付的边际成本远低于其收益,患者的费用意识依然淡薄。目前,对患方的制约主要是通过费用分摊制进行的,即使比例偏高,通常也无济于事。约瑟夫•斯蒂格里兹在《政府经济学》中深入浅出地说道:“如果一个居民知道他在医院多住一天,保险公司会替他付80%的成本,他就会决定在医院多住一天,尽管这的确没有必要。他也不会关心医院每间房每天是收300美元还是200美元,因为他知道多收100美元实际上只花费他20美元,医生也会毫不犹豫地给病人开昂贵的药,尽管这种药对身体健康所起的作用极小。”[1]此外,医疗消费所具有的刚性对本就脆弱的制约机制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存竞争的日趋激烈,人们日益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身体健康无限投资。
其二,缺乏对医疗消费的供方——医院的成本制约机制。在医疗消费的供求关系中,由于信息拥有的不对称性,医方始终处于主导市场的支配地位。因此,当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疗保险机构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利益主体,而后者又对前者施行“按服务收费”的补偿机制时,医院必然会在利益驱动下把医疗服务的提供当作创收的手段。遗憾的是,这种状况正是我国当下医保制度的反映,它直接使得来自医方的道德风险、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和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之势难以遏制。据有关部门调查分析,不合理的医疗费用支出约占全部医疗费用的20%~30%。[2]在我国医院的收入中,药费与高精尖设备的使用费所占的比重远远超出了发达国家的同比数字。小病大养和盲目重复引进高档医疗设备的现象普遍生发,城市的垃圾箱里经常可以发现患者吃不完的药品,一些医院CT扫描查出有严重疾病的比例只有10%,大大低于国外50%的比例。[3]所有这一切都应归咎于现行医保制度在医方成本制约机制的滞后。
应该说,对于医疗服务的供方——医院的制约,1998年的《决定》是加强了。但是, “医药分家”的规定可能做到的仅仅是部分消除了医院“以药养医”的行为,它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根本局面——医方权力过大并主导市场的改变没有治本之效。而增加医院之间竞争的做法,固然可能部分强化医院的服务意识,但是必须注意到:第一,这种竞争仍然是不完全竞争,医院、医生的相对垄断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4]第二,它也可能进一步异化医院,使其在创收的路上越走越远,而忘记治病救人的社会责任,如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提高手术费、诊断费等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的服务价格。降低过高的大型医疗设备检查费的做法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医疗服务系统的权力结构,医生仍然可以“擅自”创收,如可以通过增加运用大型医疗设备的频度来弥补其价格降低的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讲,《决定》版的医保制度并没有形成对医方有效的成本制约机制。
供方策略的合理性及其行动逻辑
要在医改的过程中形成有效的成本制约机制,我们需要牢牢把握医保制度内部的权力结构。如前所述,我国医保制度面临的困境与医改不彻底的原因,主要源自其中利益主体的增多,来自医、患、保三方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来自医方在医疗服务消费过程中的特殊权力以及医疗服务的第三方付费的消费模式。因此,改革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医改的重心就应相应转移至此,实现从“需方策略”向“供方策略”的转变。
“统账结合”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患者的费用意识,但是来自医疗服务的供方的道德风险依然广泛存在,医院以营利为目标的趋势不仅未得到有效扭转,反有加强趋势。从世界范围看,在医疗保险制度的成本制约机制中,加强对医疗服务提供方的管理与约束,实现成本制约机制向“供方策略”的转变是大势所趋。德国医疗保险公司建立了MDK制度[5],美国的管理保健计划中设置了“病例管理者”[6],法国的医疗保险管理机构则聘请了3000多名精通医术的监督顾问[7]。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健全对医方的成本制约机制的关键在于彻底改变医院的运作机制,改变“医”、“保”双方的互动关系。这种改革的目标在于重构医疗保险制度中各利益主体间的权力结构,削弱医生控制其收入的权力,彻底改革某些医方主导市场来为自己所属部门、所属群体谋私益的局面。
在医改中要尽快改变医务人员的报酬与医院收入挂钩的异化做法。倘若以“救死扶伤”、“看病救人”为职责的医院,医生还要靠自己的“创收”来维持生计,公正与人道将被束之高阁,国民的基本健康保证将付出高昂的成本。由于医方在医患关系、医疗服务消费过程中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身兼医疗服务提供者与医疗服务消费需求的创造者二重角色,在医方要靠自己“创收”维生的体制下,他们就完全可能利用自己的专业性以及由此派生的权力为一己牟利,而放弃自己的道德责任,有组织的医学界也可能为了自己的群体利益而背叛公众利益。前文所谓的削弱医生、医院的权力,不在于削弱医生职业的专业性,而在于安排相应的制度来割断医生在医疗服务提供方面的主导权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医改之初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而让医院“创收”的做法有些“作茧自缚”。现在,医院运转的必需经费应得到政府的充分保证,医务人员要文员化,其工作报酬须相对固定、完全来自国家财政。这种对医生的补偿办法,可以避免传统的“付钱看病法”与“按人头计算法”造成的对医生滥用医疗服务的“奖励性”作用。
同时,可以借鉴美国商业医疗保险中的“医保一体化”的经验(由一家机构同时控制医疗保险经费的使用和医疗服务的提供),由医疗保险机构经办医院或者把医疗保障的业务交由医院所属的卫生部门管理,实现对医院的补偿机制从“按服务付费”到“医保一体化”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医保制度对医院的补偿机制都是“按服务付费”。在第三方付费的医疗消费模式下,这种补偿机制势必孕育医方过度提供医疗服务的预期。因为医院的收入与其提供服务的量成正比,所以,只要通过延长住院时间、增加服务项目等措施,医院就可以达到增加自己收入的目的。于此体制下,任何对医方的成本制约机制的效度都十分有限。20年来,我国的医改曾经在“按服务付费”的大前提下,施行过结构调整、总量控制、把医疗费包干到医院等“按合同偿付”的补偿机制。但是,疾病千差万别,不同的病人需要不同的治疗,不同的治疗发生的费用也必然不一样。保方和医方在签定合同的过程中很难准确度量医疗费用,几乎不可能制定一套价格系统来测度医疗服务消费的差异。
反之,在医保一体化之后,来自医方的道德风险就可能得到有效防范。由于医方与保方的一体化,医疗服务机构与医疗保险机构不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竞争性利益主体。由此,在医保方面,卫生部门与保障部门的部门利益之争将可能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所谓的“第三方付费”和来自医方的道德风险将彻底消散,医与药的“合作”关系将和“医患合谋”一起丧失制度基础。
参考文献:
[1]约瑟夫•斯蒂格里兹. 政府经济学,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
[2]王东进. 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险制度的若干思考.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999(2).
[3]吴兴刚、李金辉. 医疗机构:制约医改的“瓶颈”. 当代社会保障,1999(6).
[4]盛洪. 医治制度之疾. 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Article.asp?ArticleID=2046.
[5]威廉•科克汉姆. 医学社会学.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50.
[6]岳颂东. 法国医疗保险制度及其启示. 社会保障制度,2000(10).
[7]F.D.沃林斯基. 健康社会学.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500-501.
编辑 阮子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