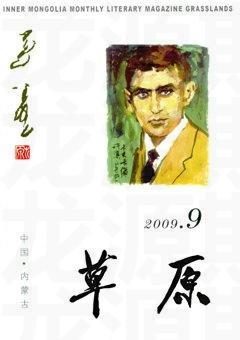市长回家(小小说)
乌新宇
从宾馆保龄球俱乐部出来,秘书小心地问:“回家吗?”他想了一下,轻声吩咐:“去我父亲家吧。”坐在奥迪A6宽大的后座里,他微胖的身材一点也不觉得局促。
周六下午四点多钟的城市街道上车不算多,司机赵师傅让他的车子走得很轻松。其实他的车号满城的交警都知道,即使堵车也能响着警笛先冲出来。
只要有空闲,他都会在周末去打打球,市委杨副书记是他首选的球友。杨副书记与自己是大学同学,虽说不同班,但在茫茫人海中,同系同届的缘分已经让他们具备了足够的默契,况且作为常务副市长的他和杨副书记多年来一直彼此帮衬,已经将缘分锤炼成无坚不摧但又没有多少人真正洞悉的同盟关系。杨副书记的秘书小张和自己的秘书李峰球打的也不错。在他看来,这种打球其实更像私人派对,就应该放下一切,换上宽松舒适的衣服,让体育精神超越地位和阶层,尽情发挥球技,也让汗水冲淡忧虑和烦恼。
李峰从副驾座位上扭过头来,试探着说道:“周市长您在伯父家要呆一阵吗?如时间长的话我想让赵师傅和我回一趟家,您看我们几点来接您比较合适?”
“哦!你去吧,用车的时候我提前找你们。”
父母住在他们工作了一辈子的二十六中教师宿舍楼,自从妻子为了照顾在京读高一的儿子,调到驻京办工作以后,父母那套位于二楼的老旧窄小的房子里更难见到他的身影了。父母都年事已高,当然希望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但知道他工作忙,对他从不苛求。每次回去,他至多呆上一两个小时,但父母依然忙前忙后,泡茶,洗水果,拿他喜欢吃的葵花籽。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那就是父母陪他喝茶时总会叮咛他要正确做人,要为老百姓尽心做事,千万不能犯错误。说实话,他知道父母是为他好,但听多了,他还是觉得父母过于罗嗦。
敲开门,父母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家里没有一丝热乎气,这让他有些猝不及防,上楼前被寒风瞬间揪疼的耳朵和鼻尖好像更加灼痛。
“怎么没暖气啊?”
“今年热力公司改造供热管线,向学校收取配套费,学校没有钱支付,向市里打报告申请减免,现在还没回音,热力公司就不给供暖,学生们还冻着呢。”
父亲话音刚落,母亲也接过话茬说起来:“老同事都让找你给过问一下,我和你爸怕给你找麻烦,就没找你。几千老师和孩子都挨着冻,我总觉得市里不会不管。”
他想起了那份报告,市长已经签批,让他牵头处理,他觉得应该召集财政、教育、城建和热力公司开个协调会,拿出一个执行方案就行了,但前一段时间带队去欧洲八国周游了一大圈,这事儿就放下了。
屋里真的很冷,窗子上是厚厚的霜花,窗外呼啸的寒风好像在对着他示威和呐喊。他注意到卧室里一向齐整的床上摊着两床呈睡袋状的棉被。
“先搬到我家去住吧。”他愧疚地说。
父亲摆摆手:“不用不用!三楼肺癌晚期的李老师还能扛着呢,我们活蹦乱跳的怕什么,多穿点,早点睡,估计再坚持两天也该供暖了,这项工作市里面谁负责啊,要不你给呼吁一下吧?大人还好说,还有几千个孩子呢。”
“嗯。”他低沉地应承了一声。
“家里冷,你快走吧,你支气管一向不好,别感了冒又咳起来!”母亲下了逐客令,他也想走了。
走出院子,拐出一条小街就是主干道。走在人行道上,冷空气从各个角度揉搓着他,把他步伐的节奏都搞乱了。他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路边一棵棵举着秃枝的白杨树都在盯着他瞅。前面是一个公交车站,站牌像旌旗一样召唤着他,他决定坐一坐。他已经不记得自己多久没有坐过公交车了,但还依稀记得这条路上有两路车都通往他住的政府小区,儿子去北京上学前,父母就时不时坐这两路车去看孙子。从父母家出来时他没有叫车,现在坐公交车是为了避避寒风,还为了什么呢?
公交车上竟然还有一个空座,虽然坐上去冰凉,但还是暖和多了。到了下一站,又涌上来几个人,一位头发花白,年龄和母亲相仿的老大妈费力地挪到他前方站稳。他下意识地站起来:“大妈您坐吧。”大妈显然没想到他会让座,惊愕、推让后还是道声谢坐下了。大妈侧转头反复打量了他几眼,微笑着说:“你长得可真像电视上常出来的周市长,哪都像,简直一模一样,不过市长大人可不会坐公交车!是吧?”
大妈的嗓门有点大,他微点头,面孔有一股血潮涌起,不过他坚信大妈没看出来。
〔责任编辑辛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