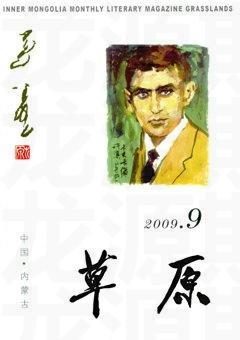散文三篇
云 珍
城中村
(一)
不是麦穗,不是白菜,也嗅不出郁金香和玫瑰那种薰得人晕头转向的光辉。
——在城市的根部、在密集的楼房中央,一朵村庄半闭半开。
(二)
犁、镐头、镰刀……生死相依的兄弟一件件脱手而去,正如渐渐白皙、丰润起来的手掌和梦想曾经是那么粗糙和无奈。时间披了一件灰色的斗篷,在撂荒的田原上踱步,孤独的村庄只能借助头发——那红的、绿的、黄的头发,一刷子一刷子地打扮季节。
(三)
男人和女人们早早上了桥头,在那里他们举起手牌,排着长队。
大孩子背着书包在楼缝里穿,说着高价买来的普通话。
陪伴村子的只有老人和娃子以及村中央那株五百岁的老榆树。
有人坐了“号子”,说是贩毒,说是撬了保险柜子……
有人“发”了,盖起的小二楼脖颈挺得生硬,但那砖头怎么看都像是一张张毛票。
有人撞了车,出事的地方在城市的十字路口,人被抬进省医院,X光、CT,该查的查过,怎么查也查不出病来,“病人”嚷着住医院,医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家里人牵了娃子跟着医生哭,哭,就是哭……,直到那捏在手中的钞票翻了又翻。
一句话开启着村人的灵感:要想富,过马路。
日日,当一领暮色覆盖了村庄,外出的男女应归未归,村庄便愈加萎蔫和病态,只有湿淋淋的狗叫横横斜斜地落下,为口渴的花骨朵儿送去几滴露水。
(四)
嫁女或娶媳是村庄里花事开得最盛的时刻。一溜轿车齐刷刷打住,脚下的汽球嘎巴巴响,炸碎的红皮满街飞。笑得最灿烂的当数来自娘舅家的大舅,大妗子……他(她)们在磨磨蹭蹭地等,等那个宴席上早已为他(她)们空出来的“正席”和代东的那一声穿云破雾的吆喊:×××请——啦——。请是请啦,是先请的赵书记、李乡长,是三姑、二姨、七婶子一块请的,一群人闹闹嚷嚷进了一家大馆子,不分东西南北男女长幼,统统围了没棱没角的圆桌子,一边吃喝一边看表演。大舅气醉了,挺起一颈红脖子骂娘,大妗子悻悻地嘀咕:我们村……
(五)
像补丁。
像被烟蒂灼穿的窟窿。
像猩红的疮疤长在漂亮的脸蛋儿。
是微弱的律动颤动在城市的末梢神经。
是一颗心脏的声音。
既然……那么……
如果……当然……
有人围着老榆树吵嚷:就那么几个“铜子儿”,够喝西北风?
有人关起门来,守住老宅,任凭雪花般飞舞的钞票压下来,压下来埋住。
有人呼朋唤友,在撂荒的田野上种楼房。
村庄终究被扼住了脖颈。
村庄终究被判了死刑。
家家户户的墙上背了一个鲜红的画了圆圈的“拆”字。
半闭半开的萎蔫浴进晨露,浴着一个涅槃般飞升的梦。
(六)
推土机正式开进村子的时候已是日头西斜。
鸡飞狗跳,孩子哭闹,女人尖叫,将白天一直拖到深夜。
八十二岁的老汉走过来拦住,扔开拐杖,躺在车轮下,眼皮子也不眨。
村民们为他送水、送烟、送饼干……
几个带头起哄的黄头发被局子里的人带走了,围在一起的人炸开了锅。
有人想起另外的法子——小四轮拉了男男女女,浩浩荡荡向市政府开进。头车高高地扯起一块白布,上写:我要吃饭!
路人一律行注目礼。是啊,吃饭,多么普通而神圣的需求!
被判死刑的村庄在上诉中苟延。
(七)
最终村庄还是被铲去了。
作鸟散的村人,如一粒粒经年的种子播进一方不明气候的土地。
老榆树已被点缀成风景了。只有那条以村子命名的马路令人或浓或淡地想起那些年轮般曲曲弯弯的往事。
是涅槃还是烟灭?
是萎落还是盛开?
三年后,两个吃“低保”的汉子在老榆树下相遇,一边抹泪,一边喃喃相语:我们不过是些被吹飞了的谷子皮……
锁子哥,魂兮归来……
一
麻油灯点亮孤零零的泥屋。
——在小巷的尽头,在童年记忆的长廊。
凌乱的影子在灯火熏染的黄麻纸上摇晃。
这是锁子哥通常为村人所熟悉的情境。
——熟悉它就像熟悉村中央那眼老井,熟悉得几近忘了它的存在,忘了它的喷涌和想望。
有时,灯未点亮,有心人会自言自语:他又扎进哪个相好的屋里去了……
二
锁子哥娶过两次媳妇又离了。
“无妨,丑呀,脏呀,像稀牛粪,像泥地里拨出来的胡萝卜……”离了婚的锁子哥这样说。
锁子哥把衣服洗得灰白灰白的。
锁子哥的衣被是自己做的,针脚齐整、绵密。
锁子哥把孤零零的泥屋拾掇得清静、利索。
锁子哥比女人还女人!
三
独身的锁子哥乐呵呵的。
乐呵呵的锁子哥仿佛一阵携雨的夏季风。
锁子哥不会作务庄稼,他的责任田年年稀稀拉拉、蔫蔫萎萎。锁子哥说:够吃就行!
其实锁子哥不懒。
李家娶媳、张家聘女、王家盖屋、赵家收秋,锁子哥一马当先。
盖屋和泥,“办事宴”当厨子、秋收操镰刀……
锁子哥爱损人。
锁子哥边做营生边逗乐,王家盖屋那一回,干活的人疲累得不行,锁子哥就当面锣对面鼓地学着村里两个女人的腔调互相吹牛:“俺娘家,那豆角,那个大呀,大得能当打麦的楗枷片……”又用另一种女腔说:“俺娘家,那个鸡呀,三条腿,一天能下五颗蛋……”
沐了风、润了雨的乡亲,如打碗碗和青草,笑得张开了嘴折弯了腰。
其实锁子哥的心不赖。
那一年张家死了爷爷,出殡的那天,可村村就是找不着一个“引魂”的叫花子,代东的四处吆喊,锁子哥跳出人群,一把抢过扁担,担起破瓦烂罐,摇摇晃晃走在队伍的最前边。
有人笑:疯了。
有人嘲:贱骨头。
锁子哥听见,看看,呵呵笑。
四
锁子哥也有笑不起来的时候。
老张家的媳妇人长得俊,只是儿子瘸了腿,光景过得皱巴巴。
锁子哥圪蹴在老张家的炕头,明着来,直着去,他拍了一把张家儿子的断腿:
“嗨,我替你‘拉边套……”
锁子哥出门走了半个月,一回来首先进了张家的门,直把那媳妇揪住胳膊拽住腿,大白天就要干那事儿。张家儿子实在看不下,操起锅铲,照住门面戳去,直戳得血流满面……
锁子哥想不通——
他想不通,平日里千般温顺,万般恩爱的那媳妇竟然帮着那个瘸腿!
有人说:看见锁子哥喝醉了,守着孤灯又哭又说,我把全部家当给了她……
五
锁子哥长我六岁。
锁子哥是个娃娃头儿。
七三年冬天,锁子哥领着我们搂柴火。日头已落,我把柴火捆起来,看看,整整比小伙伴少了一大截,我闷闷不乐坚持不回家,锁子哥走过来:我的给你。可是我气力小,绳子扣住肩,却就是坐在地上起不来,急得哇哇直哭。锁子哥急了,一边摆手一边高叫:算了,我背回去,再给你还不行?
烈日炎炎的盛夏,老泥塘是孩子们最爱去的地方。
锁子哥当然不落后。
我们在泥塘打水仗、抹泥巴、抓泥鳅,锁子哥也脱得一丝不挂,像个最大最肥的泥鳅。我们一起爬在锁子哥的背上让他当老鳖,锁子哥不推迟,任我们压得他浮上来又沉下去,还伸臂蹬腿咕咕叫。有一回玩险了,锁子哥连呛了几口水,一时噎得直瞪眼,好一会儿才缓过来,缓过来也不恼,还冲着我们呵呵笑……
六
我考学离开村子的时候锁子哥在岔路口送我,两个人长时间闷着不说话。
许久,只见锁子哥解开裤带,掏出一个绣了花的布袋,抖了抖,便见一些油腻腻的毛票和黑乎乎的钢蹦儿抖出来,锁子哥说:拿着,四块半。看见我眼睛里掉出了泪,锁子哥没话找话地逗我:我还舍不得给她哩……
我再也没见着锁子哥。
我隔三差五地总要梦见锁子哥。
家乡来人说,锁子哥疯了,整天乱吼乱蹿,有几次还高喊着我的乳名。
我给村委会寄了几次钱,托他们转交锁子哥,但不知他收没收到。
又有人说,锁子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回来住在乡里的敬老院,可是他住不惯,一不留神就溜回村子,溜去老张家,有几次被人家拖出来、撂倒……
又有人说,锁子哥上吊死了,就在他那间孤零零的泥屋。他是死了好多天才被人发现的。锁子哥的葬礼办得还算红火,是乡民政所和村委会为他操办的,乡亲们也凑了份子,宴席吃了十二盘,还请了两班子“鼓匠”,乡亲们说,也值了,只不过送葬的前面缺了一个“引魂”的!
七
2006年我执意回老家过了一个春节。
我回老家过年的原因很复杂,很模糊,却有一点再清楚、简单不过——我是要重温一些逝去的日子,我是要寻觅一个影子,那属于我的锁子哥的影子。
我有些对不住锁子哥!
年夜,我独自伫立在那个熟悉的小巷口,直勾勾地望过去,那里一排齐整整的砖瓦房灯火明亮,竟然将当年锁子哥那间孤零零的泥屋所占的空间也没有了,哪里还能见得到那盏悠悠的麻油点亮的灯火,那摇晃在灯火熏染的黄麻纸上凌乱的影子!
我失望了。
年初二,我踩着吱吱的积雪,找到了锁子哥孤立在荒野里的坟头。欣慰的是,终归看见了黑色的细碎的纸烬在衰草间乱飞。
我跪下,将从城里买来的假钞票和烧纸点燃,翻来翻去,看着它们一点不剩地燃尽,我向着坟头深深地叩下去。
起风了,空荡荡的旷野一个声音在飘荡——锁子哥,归来……
婚变
一
她的高跟鞋嘎吱吱地一路踩去。
踩着那个女娃尖锐的哭喊,踩着那曾是她丈夫的目光,像踩死了一条条虫。
她优雅地拉开,“咣当”一声拉上车门,将窈窕的身躯埋进了黑色的小轿车——
她将这里与自己彻底断开,她嘘了一口气。
干燥的小院里,即刻弥漫开汽油混合胭脂的气息。
他两手托着破旧的自行车把,目光踌躇。车的后架上驮了那个神情呆滞的女孩。一股燥热浑浊的夏风卷了沙尘扑过来,扬起他(她)们的头发,一个卷曲、萎蔫、 污浊,一个灰白、发嗲、发直,像苦旱的正午盼雨的沙蓬和枳机……
了啦?
我自语。
二
我不愿却不由得又一次翻开了这件婚案的卷宗,下面的一行字我几乎背熟。
女:他曾经是林子里一颗拔了尖的白扬,我则是白扬树下一朵盖了帽的花朵,我们再自然不过……
白杨林蓄存了我们过多的呢喃与羞涩,至今,哪怕一阵风拂过,秘密便会溢出。清水塘那轮偷偷张开的红月亮摄录了无数我与她相偎相拥的影子,只要一脉涟漪就能漂出一张……
男:羞死啦,说甚哩,怎就怎哇。
男、女:(后来)之后,(我们有了一个娃)。我们有了一个女儿。
女:七六年他当兵走了。
男:七七年她考上了中文系。
女:之后四年,我坐了机关。
男:后五年,我进了工厂。
女:之后下海,我进了省城。
男:后来……后来……我下了岗。不,法官,她进城是做了小姐,再后来,她就做了一个“大款”的“二房”……
女:不,书记员,他哪里是棵白扬,他甚至不如一只蛤蟆,蛤蟆尚且不说谎。
我的钱是凭本事一点一滴挣来的,你看他那熊样!
男:那你就是走俏的母猪!
女:听听,法官,我们确实已无共同语言!
三
那一幕,我永生难忘。我尚未见到有哪个女人是那么冷漠而又大方。
那天,我为他(她)们协调财产的分割和女儿的领养。
男的说:只有房子两间半,是平房,我只要一间,其余给她……
那女的连连摆手:不要,不要,都给他,才值几个钱!边说边白了那个男的一眼。(这应该是个意见,我赞赏她的大方)。
接下来是女儿的领养。我刚提到,那男的就激情四射,他嗫嚅着嘴唇,却说不出半句像样的话,但我仿佛看见一只手掌自他的嗓子眼儿伸出,紧紧搂住他的孩子,那神情怕是钢筋铁臂也难以扳开。
那女的表情平静,许久不言,她翘起二郎腿,优雅地抽着一支细烟,像旁观者欣赏一场别人的闹剧,眼睛始终乜斜着的那种不屑。
沉默。
冷不丁见她拉开华丽的手提包,嗖嗖地将好几叠钞票扔在了我面前的桌上。
她说:我不在乎,这是无比坚挺的美元,他(她)们一辈子也享用不完。顿了顿,长嘘一口气,接着说:论理吧,未成年的孩子应跟妈妈,可是,我们毕竟已分开几年,感情没有了,要人有何用?但她毕竟淌着我身上的血……法官,还望您高抬贵手,把钱收下给他!
(我的心怦然一动!)。
这时,一个保姆样的女子领进来差不多一般大的一个女孩,喳喳地尖叫着扑向那个女的——她的妈妈。她像突然看见了宝贝,俯下身来,一边亲吻一边抚摸:乖乖听话,妈妈正在了断……
未了,我为一件事而震惊,为一件事而担心。
我为她这第二个女孩的前景担心,我不能不担心!
我为那个男的一个坚决的动作和他的恪守而震惊。只见他将那叠移至他面前的钞票推得远远,说:最多只要两间半,宽敞,那样就可以为娃腾开一个学习间……(我不能不震惊于他的动作和语言!)
四
黑色小轿车冒了一股白烟,吱的一下就飞上了进城的柏油路,甩下来的是黄土尘封的乡道和乡道牵系着的大山。
那个男的歪歪斜斜地蹬起了他破旧的自行车,朝着老家的方向行去。车架上驮着他藏在嗓子眼儿的娃。
此刻,老家的那边正当浓云翻滚,山雨欲来。他(她)们愈行愈快,我想,那是盼雨的沙蓬和枳机正赶着要去吸水……
五
了了吗?
了了也罢!
〔责任编辑阿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