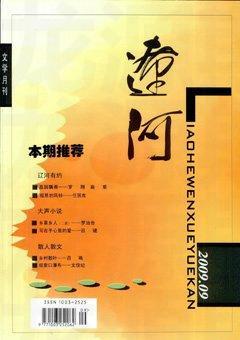孤鸟
杨恩智
一
电话响起来的时候,二相正在车一颗螺丝钉。二相没有接。电话响了两声,二相就把手伸进兜里,摁了。
老板曾多次重申过,上班期间不准员工打电话。老板还说,要是谁打了,就一次扣二十元钱。二相心疼钱,二相也知道老板说得出就做得出。二十元,那可是半天的工钱了。出来打这工为的是什么,不就是这点钱吗。家里欠的那贷款可是说好要在年底还的,那可是请人担保了才贷出来的,怎么能让担保人去担过、担风险呢?还有,那建房证已经办下来一年多了,再不修就要过期了。建房证过期不说,要再不修间房子,回去就连住的地方都没了。以前住的那一间破草房,都快两年没人住没人管了,说不定都已垮了。更让人担心的是以前赊肥料来种庄稼欠下的那些钱,那可是高利贷,利息像春天的拔节草,与日俱增着呢。
电话又响了起来。二相的心里掠过一丝不悦。谁这么烦?二相抽出一只手又把电话摁了。连看都没看,想都没多想。他一直都是这样。虽然他的电话平时就很少,甚至常常一天接不到一个,但只要是在他上班的时间打来的,他都不接,等下了班后才给回过去。电话第三次响起来的时候,二相开始烦躁起来,他甚至都有些恨起了这个电话。但他又想会不会是有什么急事呢。这个想法一掠过二相的心头,就让二相不由自主而又贼精精地抬头环扫了一遍车间,这时刚好监工不在,于是二相贼头鼠脑地把电话从裤兜里掏了出来。那是一个柴疙瘩样的黑色直板手机,是花一百元钱从一个工友手里买来的。二相按了一下接听键,把电话紧紧地贴在脸上,像个娇小姐样的“喂”了一声。
二相的嘴大大地张了一下,脸上的肌肉突然地凸起,他的脸上瞬间轮回了一个春夏秋冬。
二相弹起身来,没有跟已站在他身旁的监工说上一句话,就冲出了工厂。
二相刚到县医院,就看见妻子小米歪靠在医院门诊部门前的台阶上。小米的脸上还在流着血,整个脸部已很明显地肿了起来,惨白惨白的。咋了?二相抢上前去扶着小米问。小米抬起头有气无力地说,被他们骑车撞了。二相这才注意到旁边还站着一个陌生男人,小米的一只手还在抓着男人的一只衣角。男人瘦瘦的,一副马嘴脸,穿着一套白色西装,头发梳成两片瓦。男人的旁边停着一辆摩托车。
二相蹲下身拉着小米的手问,撞到哪儿了?小米探了探头,说,就是走不成路,腰疼。二相说,走,赶快进去看看。小米说,他没带钱。二相一下子站起身来,拎着男人的衣服虎凶凶地说,还不赶快找钱来?男人说,我都打电话找过好几处了,找不着。面对二相愤怒的目光,男人又说,要不,你先找来医了再说。如热锅上的蚂蚁的二相又望了望小米,小米正在那儿闭着双眼,龇着嘴喘着粗气。二相回头望了一眼男人,说,走,送我回去拿钱。男人“嗯”了一声,望了望小米。小米像是感应到了什么,随之放开了手。
二相在床下的鞋盒里把他们的钱全部拿了出来,那是准备再等这个月的工资发下来一起寄回老家去还账的。二相醮着口水认认真真地数了两遍,钱还是五千六百元。二相把门锁了,边往兜里装钱边往楼下赶。等他下了楼来,却不见了男人。
男人会不会是先回医院去了呢?二相想。
二相没有再找男人,他打了一辆的士,又返回了医院。小米显得更加无力无神了,整个的人都匍匐在了台阶上。二相抢上去把小米的头抱了起来,摇了摇小米。看着小米睁开眼,二相说,那个没回来吗?小米说,哪个啊?二相说,就是刚才那个男的。小米仰了一下头,说,他不是跟你去了吗?没跟你在一起啊?二相说,我上楼去拿钱下来他就不在了,我还以为他先回来了呢。小米闭上了眼,投在二相怀里的头无力地歪了一下。二相急了,抓住小米的手急切地问,怎么啦?小米,你怎么啦?
二
一天以后,小米醒来了。醒来了的小米看着站在床前的二相,两眼蒙眬地说,跑了。二相不知道小米说什么跑了。小米仰望了一下粉白的天花板说,骑车撞我的人跑了。接着小米又像昨天那样把头歪了一下,歪在同样粉白的枕头上,万念俱灰般的说,他撞倒我的时候就想跑了,他早就想跑了,他一听我说我站不起来了的时候就挣着要跑了,是我拼了命地揪住了他,叫他打电话给你,叫他把我送进医院。怎么就跑了呢?都把我撞成这样了,怎么就跑了呢?
那一下一下滴落的液体,锤子般地敲打着二相的心。二相觉得自己太没用,竟然让肇事者跑了。二相一来就没想过肇事者会跑。都把小米送进医院来了,怎么还会跑呢?
护士来量血压的时候,小米想撑起身子来。可她刚撑了一下,一种锥心的疼痛就把她疼得龇牙咧嘴直喘粗气。护士赶紧按住她,说,别动,你不能动,你的脊椎已经骨折,而且还很严重。小米不知道脊椎骨折是怎么回事,她连脊椎是哪儿都不知道,她只感到自己周身都疼痛,钻心的疼痛。小米只有这种疼痛,她却不知道自己这伤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二相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小米这伤严重到什么程度。他的脑子里早已乱成了一团麻。自从医生让他至少要准备一万元钱的医药费时,他的脑子就开始乱了。也是从那时起,他知道了小米那伤的严重。要一万元钱才能医好的伤有多严重,二相根本想不出来,他从来没有遇上过要一万元钱才能治好的伤,连看都没看过。二相六神无主。肇事者跑了,二相不知道从哪儿去弄这一万元钱。
护士已经把量血压的绷带绑在了小米的胳膊上,她边捏着一个胶制球体往绷带里挤气边问小米,你这是怎么伤着的?
小米说,被车撞的。
护士用一种充满怀疑的眼神看了看坐在床边的二相。是你撞的吗?
二相把目光从点滴瓶上移了下来,无神地看着护士说,跑了。
护士急切而又像是有些怀疑的说,跑了,肇事者跑了?
二相“嗯”了一声。
护士张了一下嘴,那一下张得有那么一段时间,像是要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
病房里一溜儿地摆了四张床,一张不空地都住满了病人。也有车祸致伤的,还有挑砖块从楼上摔下来的。那些病友以及在那儿看护病人的人都向二相看了过来,眼神里有惊讶,有同情,更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护士说,跑了,怎么会跑了呢?你们报案了吗?
二相说,没有。
护士说,怎么不报案呢,被撞了的时候就应该报案啊。
一个病人也撑起了身子来,说,就是啊,无论如何,被车撞了还是报个案。
二相说,当时就她一个人,她是骑着自行车去上班的路上被撞的,一撞到她的时候那人就想跑了,是她硬揪着,那人才给我打了个电话的。
护士说,听口音你们是外地人吧?
二相“嗯”了一声,说,云南的。
另外一个病友说,我们说的话和这儿的区别就很大,你们云南的就更大了,一听就能分出来,那人一定也是听出你们是外地人,才敢跑的,要不他根本就不敢跑,他的车有牌照呢,他跑得了吗?
护士已经在收她的器具了。在起身要走了的时候护士说,你们记得那车的牌照号吗?
二相摇了摇头。
小米说,我记得,好像是9787。
护士说,那你们赶快去报个案,看能不能找到这车,要不,你们这就要白挨了,这么远的来打工,挣点钱不容易,再受上这份苦,就……
一个病友显得有些兴奋地说,能,肯定能,只要记得牌照号,就一定能找到肇事者。
三
按照当地摩托车牌照号9787,二相跟着两个警察走进了一个村庄,找到了一个叫李志辉的人。李志辉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青年男子,穿着一件红色的背心,剃了个光头。面对站在他面前的警察,李志辉显得有些惊恐。
你叫李志辉,是吧?一个警察问。
李志辉有点迷惘,似乎不知道该说“是”还是“不是”。但他最终还是点了点头,说,是,我是李志辉。李志辉有些胆怯地扫了一眼他面前站着的人说,我怎么啦?
问话的那个警察转过身看了一眼二相说,是他吗?
二相左看一眼,右看一眼,上上下下的都看了,现在站在这儿的人怎么也不像那天送他回去拿钱的人。二相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他一点儿也不敢说就是这个人。但他又不敢说不是。他在心里就不敢肯定这是不是。这可是根据牌照号9787找出来的。这应该不会错的。但怎么一点儿都不像呢?这会不会是他逃了以后,为了防止被认出来,就改变了穿着,还把头发也给剃了呢?二相又仔细地看了看李志辉的脸,他想把这张脸拿去和他印象中的那张脸对照一下。可任他怎么对照,也老是对照不上。这下二相有些心急了。会不会是小米把牌照号记错了呢?二相的心颤栗了一下。如果真是这样,那……二相不敢想下去了。一下子,找肇事者的事就在二相的脑子里烟消云散了。后怕,恐慌,不知所措,二相的脑子里爬满了蚂蚁,乱糟糟的。
看清楚了没有,是不是他?警察又问了起来。
噢……二相又看了一眼李志辉,然后像个小学生在老师面前做了错事样地说,好像不是,那天送我回去拿钱的人的头发是长的,而且梳着个两片瓦。
牌照号9787的摩托车是你的吗?警察转向李志辉问。
嗯,是我的。李志辉说。
前天你是不是在城里骑车撞了人?
前天,没有啊,我这几天都在家里。我没有进过城。
那你的车借给别人骑过吗?就是前天!
也没有。
真的?
真的。
二相的心一阵紧似一阵。
你的车呢?在哪儿?
就在屋里。
你去弄出来。
二相一看到那车,心里就又咯噔了一下。那车也一点儿都不像那天他骑过的车。一定是小米给记错了,一定是。二相想。二相的心里咚咚咚的跳了起来。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牌照呢?怎么没挂?警察问。
牌照被一个朋友借去用了。
借去用!这牌照能借的吗?他在哪儿,你赶快给我把他找来。今天之内,你把他带到事故处理中心来,要不然所有责任你全部承担!
四
二相心喜若狂地回到了医院,一走进病房就说,找到了,找到了。
小米撑着身子想坐起来,但一阵锥心的疼痛让她最终也只能半卧在那儿。那脸虽然依然苍白,但却明显地露出了喜色。病房里的病友们也跟着惊喜了起来,异口同声地问,人呢,人在哪儿呢?
二相说,警察让他今天之内到事故处理中心,警察说他到了会叫我去确认的。
一个病友说,就是嘛,只要记得牌照号,他还能跑了?
又一个病友说,这下找到背家了,他是骑机动车的,小米是骑非机动车的,而且他肇事后又逃走了,这责任一定是他的,全部是他的,你们可以安安心心、放放心心地治疗了,这也算是你们不幸中的万幸了。
二相赶紧说,是啊,是啊,这下好了。
准确地说,那逃走的人二相他们还没有找到。这一点二相心里很清楚。但二相觉得没必要担心这一点。人都已经落实在那儿了,警察都说今天之内必须到事故处理中心了,那还跑得了吗?
二相的心里只有一种急切的等待。二相希望他的电话一下子就响起来。他紧紧地把电话握在了手里,像是随时准备接听样的。
但这一天二相并没有接到警察的电话。这让二相一夜里都毛抓火燎的。他不知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故处理中心会连个音信也没给他。是那人没来吗?那人会不会不来?那人会不会跑了?跑到一个他们找不到的远远的地方去!要是那人真跑了,找不到了,那怎么办?怎么办呢?二相不知道。不过二相又想,他会不会跑?敢不敢跑?警察已经找到李志辉了,他跑了,李志辉就得承担这责任了。一这样想,二相就又觉得那人不会跑,李志辉也不会让他跑。但怎么会没有消息呢?那人会不会已经来了,甚至早就和事故处理中心的人在一起了呢?一想到这,二相刚踏实了一下的心就又悬了起来。如果是这样,二相倒希望那人还没来,这样只会惹怒事故处理中心的人。二相害怕的倒是那人已经来了,而且和事故处理中心的人在一起了,那意味着什么?他们可都是这儿的人,手胳膊还都是往里拐,要是人家还认识,还有关系,那会是什么结果?
二相有些不敢想下去。他整个的脑子已经被各种猜测搞得乱麻麻的了。
第二天早上,二相接到警察的通知后,到了事故处理中心。刚走进大门,二相就看到了那个现在看来多么熟悉的面孔,那就是那天送他回去拿钱的那个男人。男人正和一个身穿制服的人从办公楼下来。
警察一看到二相,就说,你来了,你看,撞到你妻子的人是不是他?
二相毫不犹豫地就坚定地说,是的,那天就是他送我回去拿钱的。
二相跟着男人和警察一起走进了一间办公室。警察说,事情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他也承认了,只是他说那天是你妻子违反了交通规则才发生那起交通事故的。
二相的心里突然地凉了一下。
警察说,不过,你妻子骑的是非机动车,他骑的是机动车,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要承担主要责任。
警察顿了顿又说,你们先私底下商量一下,看能不能私了。要是能,私了了算了。王二相,你想一下,看要他给你多少钱,你们相互商量商量。
警察说着就走出了办公室。
二相已经没有想过要要多少钱了。从昨天晚上起,二相就已经没在这上面花过一点儿心思了。他想不到现在警察竟然会叫他与肇事者商量私了,还问他要多少钱,这实在是出乎他的意料。
只是,要多少钱呢?二相开始犯难了。他应该要多少钱呢?二相曾听说过,像这种事要算什么精神损失费、护理费、住院费、生活补贴费、误工费什么的,但他不知道这些费用要怎么算。就连住院费要多少,他也还不知道。虽然医生要让他至少准备一万元,可是最终究竟要多少呢?光住院费就可能要一万元,要是再加上其它费用,那又要多少呢?一万元已经不少了,再加上其它的,那应该是多少?是两万?还是就一万?如果开口说两万或者就一万,那人家会不会以为他是乱弹琴,想趁这事来敲诈勒索人家?可是能说要四千五千吗?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承担主要责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责任?小米违反了交通规则,这又意味着什么?
二相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和男人商量,不知道该怎样私了。
男人说,你想一下,要多少钱,干脆点,我很忙。
二相说,人还住在医院里,我不知道要多少钱才能医好,现在我觉得不好私了。
男人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二相说,你应该拿出钱来,先把人医好了再说。
男人说,我怎么能先拿出钱来呢,说法都没有一个,我拿多少钱出来?
二相看了一眼男人。男人也看了二相一眼。
二相说,你怎么就不能先拿出钱来了,你撞了人怎么就不能先拿出钱来。二相说着把手指向了男人。
男人后退了一步,双手一摊,说,事实我承认了,该我负的责任我会负,我都听处理中心的。王警察叫我怎么赔我就怎么赔,你在这儿发火也没用。
二相和男人没说出个什么结果,警察也一直没回来,男人走出办公室后,二相也就跟着走了。
走出事故处理中心,二相说不出自己的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他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可这希望是那样的渺茫,那样的捉摸不定。王警察,那警察姓王吗?男人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他们已经很熟悉了吗?警察让他们私了,这是为什么?警察为什么不叫男人先拿出钱来医治小米?不应该吗?不可以吗?男人都说了,该他负的责任他会负,警察叫他怎么赔他就怎么赔,他为什么会这么自信?他该负的责任究竟是什么呢?警察会叫他怎么赔呢?
这天晚上,李志辉来医院找到了二相。二相以为是那个男人叫来跟他商量私了的。但不是。李志辉说,我今天来是要问你一件事。
二相说,什么事?
李志辉说,我的摩托车被事故处理中心的人扣了。
二相有些意外。
李志辉说,你知道为什么被扣的吗?
二相说,不知道。
李志辉说,那我告诉你,是因为你,你报了假案,说我骑车撞了你老婆。现在已弄清你老婆不是我撞的,我的车却被扣掉了,你看这事怎么办?你得给我一个结果。
二相说,我报假案,我报什么假案了?
李志辉说,那我问你,你妻子是我撞到的吗?
二相说,不是你撞的,但是是挂着你的车牌号的车撞的。要找,你也只能去找那个男人,是他,用你的车牌号挂在自己的车上骑着撞了我妻子,才让你的车子被扣的。
李志辉一下子跳了起来,抬起一只手指在二相的脑门上吼着说,不是我撞的就不是我撞的,什么挂着我的车牌号的车撞的,反正我不管,事故处理中心的人跟我说了,要两千块钱才能取出我的车来,你得赶快把这钱弄来给我,要不,我跟你没完。
二相被李志辉这一吼,吼得有些失魂落魄,吼得有些三魂出壳,七魂离体。二相还没回过神来,李志辉已气势汹汹地走了。
看着李志辉离去的背影,二相一片茫然。
怎么了?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现在怎么有理也说不清了呢?这能怪我吗?我报假案了吗?我这不是按照9787的牌照号找到的肇事者吗?
李志辉那手像是还在指在二相的脑门上样的,这让二相的心里一阵又一阵的毛骨悚然。
五
医院已经停止为小米用药了。二相跑到医务室问医生说,17床还没有输液。正在一个本子上记录着什么的一个女护士扭转头来说,输什么啊输,都催过多少次了叫交费,已经欠三千多了,你说我们拿什么来输?没赶你们走就是好的了。
二相说,我们的事情正在处理呢,一处理好我们就来补上,请你们先给治着啊。
另一个站在旁边的医生说,你别在这儿嚷嚷了,赶快去找钱来,能让你们欠着三千多已经算是开大恩了,以前你说那是交通事故,医了的费有人背着,可现在怎么肇事者还不来呢,你叫我们还怎么相信你!
二相的眼前朦胧了起来。是啊,人家都让自己欠着这么多的医疗费了,怎么还会让自己继续欠着呢。二相低着头离开了医务室。怎么办?难道就这样在医院里干住着吗?这样干住着,那还不如回家去。可是小米连床都还不能下,又怎么能出院回去呢?
回到病房,小米正无奈地看着别人的吊针发呆。二相觉得小米已经明白了什么。但二相还是不说,二相拿起打饭的口缸,说,想吃点什么,我去买来。
小米回过头来说,不想吃。
二相说,不行,一定要吃的,医生说了,吃下一勺饭去可要胜过一瓶液的,怎么能不吃呢?
小米说,我真的不想吃。
二相说,那就吃点稀的,吃碗稀饭吧。
小米没有说吃还是不吃,又把头转过去看着其他在输着液的病人去了。
二相提着口缸走出病房,泪眼朦胧地来到食堂,又晕头转向地回到了病房。坐在小米面前,要喂小米吃了,二相才发现自己打来的竟是一口缸米线。
二相说,来,吃点米线吧,米线滑,好吃。
小米又看了一眼输着液的病人才回过头来。
二相换了一双筷子,一根一根的挑着米线往小米嘴里送。
二相边喂小米吃边说,我问过医生了,说你今天不输液了。
小米像是在吃药样的。二相都把下一筷子米线喂到她嘴边了,先前的那一根还在她的嘴里拌过去拌过来,如食黄莲。
小米也就吃了四筷米线,就望着二相摇了摇头,说,我吃不下去了。
二相迟疑了一下,放下口缸说,那趁你不输液,我出去转转。
要走出病房的时候,二相回头看了一眼靠在病床上的小米,心如刀绞。二相不忍再看一眼。他转身离开了病房。住院部的整个过道里,都见缝插针地摆满了病床。看着那些睡在床上痛苦不堪的病人,二相觉得小米还能住在病房里,已经实在算是不容易了。只是看着过道上、楼梯间,来来往往的人大包小包的提着东西来来去去时,一种悲凉的感觉就涌上了二相的心头。
站在医院门外的一个十字路口上,望着行色匆匆的人们和疾驰而过的各种车辆,二相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格格不入。那些人和车,行走的方向都是那么明确,只有他自己,不知道要走向哪儿。
钱,在哪儿能找到钱?
二相穿过十字路口,信步走向了事故处理中心。
六
王警察办公室的门紧紧地关着。
二相不知道王警察去了哪儿。
二相想,等等吧,他肯定会回来的。
关门的越来越多了。要下班了。可王警察依然没来。
二相壮了壮胆,问了一个刚关了门要走的警察。这个警察说,这个案子不归我管,你得找王警察。二相说,可王警察不在呢。这个警察说,那你明天再来看吧。说着,也走了。
二相第二天又到了事故处理中心,但他依然没找到王警察。
二相第三天开始像一个在事故处理中心上班儿的同志一样,上下午按时地走进了事故处理中心。但他一连等了四天,还是连王警察的影子也没见上一个。
第七天的下午,二相没见到王警察,却见到了那个男人。
见到男人,二相像是见到了一根救命草。这哪儿是向他去要钱,分明就是去跟他叙旧。二相说,你也来这儿?
男人说,啊,我来找王警察有点儿事。
二相说,我们那事王警察怎么说了啊?
男人说,怎么说?要怎么说?
二相说,医院已经停药了,你得找些钱来先垫着把人医好啊。
男人说,不是说了吗,要等病人出院了才处理。
二相说,可现在人还没好,我们又没钱交进去,人家不治了。
男人说,那你是打算私了了?
二相停了停无奈地说,那也行。
男人二话没说,从兜里拿了一沓钱出来,说,那这是两千块钱,算是同情你,也算是把这件事给了结了,你要同意,就拿这两千块钱去,写个字据,以后互不相干。
二相一下愣在了那里。二相木桩样地站在门边,望着男人说,两千块?行吗?你说,我们在医院里已经交了五千了,现在都欠着三千多了,这两千,连还欠医院的都不够啊。
男人说,怎么?你还嫌不够啊,我倒是觉得你们老远的来这儿打工也不容易,发生了这事还挺同情你们的,才给你两千,你倒还嫌少了,那就等出院了来处理吧。
说着,男人已经扬长而去。
二相想追上男人,狠狠地揍上男人一顿,但二相挪动不了自己的脚步。望着男人的背影远去,直至消失,二相整个的懵了。两千元,这两千元拿来能做什么?连付医院的欠费都不够呢。还有那个李志辉,他还要两千元呢。二相傻了。二相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一边是连下床走路都还不能的小米,一边是钱。
怎么会这样呢?王警察到底去哪儿了?
二相走出事故处理中心,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钱把二相的脑袋都快挤炸了。两千元,也一直在他的脑子里旋转。他问自己,两千元,真的少了吗?如果少了,那应该要多少呢?如果最后连两千元都得不到,那又怎么办?
风,疾疾地刮在二相的脸上。二相打了一个寒战。二相抬起头看了一眼天空,才发现天空已是乌云密布。一道闪电划破天空的同时,一声惊雷也随之在天际间轰隆滚过。街边的门面里,以及那些住房里,都已亮起了炽白的灯光。街上的车辆,都在撕破喉咙地鸣叫着喇叭疾速行驶。那些骑自行车的,双脚踩在踏板上,站着个身子,没命地蹬着踏板。骑摩托车的也一律地弓着个背,低着个头,像穿着滑冰鞋样的在大街上飞翔般地行驶。走路的更是,像是家里着了火样的,抱头鼠窜。二相也想走快点。但他却不知道自己要走到哪儿去。虽然那医院是他现在必须去的,但他不知道自己怎样走进去。二相不知道怎样去面对小米。二相想先回到租住房里去,去认真地想想下面该怎么做。但现在已经到交房租的时候了,他还从来没有拖过房租,他不知道回去要是房主问起房租的事来怎么说。
一阵急促的雨点打在二相沮丧的脸上。一种冰凉的感觉浸进二相凄凉的心里。二相仰起头望着夜幕苍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下吧,大大的下一场吧。二相渴望狠狠地淋上一场大雨。走到医院门口了,二相又绕道继续往前走。
但二相最终也没能淋上他想象中的那一场雨。失望而又无奈的二相一脸沮丧的走回了医院。
进了住院部,刚转过一个过道上的弯,二相就一下子充满警惕的站住了,并随即往后退缩了几步。
二相看到了李志辉。李志辉正站在小米她们病房外的过道里。二相知道李志辉是来找自己的,二相也知道李志辉找自己的目的。二相害怕着李志辉。二相害怕碰上李志辉。二相退回到电梯旁的一个墙角里,在那儿探着个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李志辉。李志辉还是穿着那件红色背心,双手插在布满洞洞眼眼的牛仔裤的裤兜里,嘴里叼着一支烟,在那过道里走来走去。
时间过去了许久。二相的心里越来起急了。怎么还不走呢?他要等到什么时候?小米现在还没吃饭呢。小米现在说不定正在为自己担心着呢。他进去问过小米了吗?小米会怎么说呢?小米都不知道自己去了哪儿,她会怎么说呢?她是说自己要回来,还是不回来?李志辉有没有跟她说起他来的目的?他要挟了小米没有?
李志辉似乎也开始急躁起来了。他开始不停地往二相站的这边过道里张望。
李志辉走进病房去了。二相的心一下子紧了起来。他进去做什么,他没等到自己,会不会去对小米怎么样?二相想冲过去。就是不冲进去,二相觉得自己也得去站在门边听听里面的动静,以防万一。
没等二相冲过去,李志辉就出来了。二相刚探出去的身子又像被电击了样的缩了回来。
李志辉出来后,又点燃了一支烟,然后左望望右看看的,终于有些不舍地走了。
七
随着火车与铁轨撞击出的“哐啷哐啷”声,一个高楼林立的城市退出了二相的视线。接着是一座又一座浑圆的山影。二相怀抱着小米,一边不停地看着外面倒退的山影,一边又不停地观察着周围的人。车厢过道里偶尔走过的一个人,常常让二相心惊肉跳。特别是那些穿制服的人一走过来,二相就把整个的头埋在了小米的身上,埋得死死的。
二相背着小米走出了车站。一下子二相的周围就围上了很多人。叫坐车的,叫住店的。现在除了小米,二相便什么东西也没有了。他还坐什么车,住什么店?
二相不知道医院里现在有没有发现小米不在了,有没有追来?还有那房东家,有没有为自己这么长时间没回去而把他们住的那间屋子转租给别人?二相不知道自己这么一逃走,是幸还是不幸?
逃,二相这已是第二次逃跑了。第一次是在老家被那些债主逼得没办法了才逃的。这一次没有谁逼他,但他不逃又能怎样呢?医院里已欠了三千多,说不定已经更多了,李志辉还要两千,还有房租费,那个男人却只给两千,王警察又找不到。除了逃,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深夜的天空星星点点,二相不知道自己现在该怎么走,该走向哪儿?二相一片茫然。二相想到了回家,可二相知道自己是怎么出来的,现在那些债主们那种狰狞的面孔又魔鬼般地在他的脑子里晃荡。债还没还,田园早就荒芜,房屋或许都已经倒塌,自己怎么回去,回去怎么生活?就是要回,现在连回的车费也没了。二相只想等明天就近找个活做,挑灰浆也好,看工地也罢,无论做什么都行,只要有个活做着,就能让小米把病养好,就能让自己生存下来,甚至挣了把家里欠的债还完,把那房子翻修起来。
二相没有住旅馆。二相已住不起旅馆。二相背着小米又回到了候车室。一走进候车室,二相就觉得那是一种再也不能有的温暖了。二相让小米坐在了一个凳子上,自己紧挨着坐在了另一个凳子上。小米紧紧地靠着二相。是因为暖和,还是因为疲倦,大厅里寻人的、告别的、寒暄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并没有影响着二相,二相就那么抱着小米,在那儿摇摇欲坠地睡着了。
二相是被一个人摇醒的。二相正在做一个恶梦。他觉得自己的胳膊正在被一个穿制服的人死死地揪着。二相一左一右的挣扎着,使劲地甩着。这一挣扎一甩,二相就醒了。醒来的二相,额头上已沁出了一层毛毛汗。
二相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二相揉了揉眼,努力地看着他面前的这个人。
你是王二相吗?你咋会在这儿?还没等二相看个真酌,站在他面前的人已万分惊讶的看着他问起来了。
二相同样是惊讶。二相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在这儿遇上家乡的人。他已经看实在了,站在他面前的人是他们村的村委副主任李德宽。
背着小米跟李德宽走出候车室后,二相看到了更多的乡亲。男的,女的,都有。但都是年轻的。一个个年轻的面孔上都带着一种外出闯荡的憧憬和喜悦。看着他们,二相的泪水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如一道河堤的崩溃。
二相装了满腹的心酸,却又觉得无脸向李德宽,向他的乡亲们诉说。但在乡亲们的追问下,他最终还是说了,说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
李德宽说,他是送这一群人去打工的。是以村委会的名誉去的。村委会已跟广州的一个公司签了合同。村委会的领导也已跟着县乡的领导去公司作过了考察。那个公司的待遇很不错的。
李德宽还说,现在,他们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市级示范点,在市县乡的指导和帮助下,他们村除了从种植业、养殖业上发展外,还走一条“打工强村”的路子,现在去的这一批已经是他们送出去的第三批打工队伍了。
李德宽又说,现在你回去也一样不是一样的,也没日子过,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出去,哪儿跌下去哪儿爬起来,再出去一次,说不定一年或者两年的,你就好起来了。等安定下来,我们再找个律师什么的问问,看有没有办法让这事得到处理。
二相很想跟他们出去,他知道自己正像李德宽说的那样,回去也没日子过,况且还连回去都成问题,他现在身无分文不说,还有小米,现在还是这个样子,怎么坚持得下去?去了又不是一下子就能有钱来治的。
李德宽似乎看出了二相的担心,他说,要是你想去,就别担心什么,车费我们一个挤出点来,没问题的,就是小米,到了那儿后,我们也先凑钱给她医治。
八
次日,二相带着他带病的妻子,跟着李德宽带领的乡亲们,踏上了去广州的列车,又一次走上了打工路。
二相有了一种孤鸟归队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