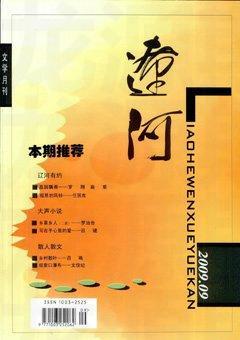摇晃的风铃
任国良
那个年轻男人从理发店前走过去,穿着黑色夹克衫,里边穿着灰色带暗格的衬衣,脸上棱角分明,面色红润。不到五分钟,他又折了回来,站在那里看那个牌子。牌子是用铁焊的,白漆做底,红色的字:王师傅理发店。时间久了,红色变得发白,漆有些脱落,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字来。在林立的色彩鲜艳的各种招牌里,显得很不合群。这是一条在高楼之间的小街,街两边有几十家美容美发店、小旅店、小吃部。每家店铺前都有一个拉客的小姑娘。王师傅理发店前面只有一块牌子。年轻男人甩开几个小姑娘的拉扯,犹豫着走了进来。
王师傅正在给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头儿理发。王师傅个子不高,头发梳得很整齐,穿着也是很朴素。王师傅注意年轻人好久了。他看出来这个小伙子不是来找小姐的,就有几分好感。他破例地说了一句话:“先坐一会儿。”年轻人点点头,坐在沙发上,点着一支烟。屋不大,前后两进,多是理发用具,三面墙都有镜子。在窗户那里挂了一串紫色的风铃。开门、关门、王师傅用电吹风,风铃都会摇晃并发出悦耳的声音。王师傅的电动推子不慌不忙地在老者的头上左一下右一下地推着。有时可能只剪去几根头发,推子在一个地方走好几次,但绝不一下子剪得过深。鬓角、脖根都仔细地做出个形状来。老者已经眯上了眼睛,发出均匀的呼吸。但王师傅却没有停下,那推子的作用此时更像是一种音乐或是一种抚摸。屋里没有其它声音。午后的阳光从高楼的缝隙中射过来。整个屋子明一块,暗一块。一个人睡着,一个人忙着,一个人手中的烟灰已有一寸长。
“咯咯——”一阵笑声从后边房间传来。那是女人的声音,小巧、细碎,有几分娇气。老者猛然醒来,坐直了身子。王师傅说:“刮刮脸吧。”老者笑了:“小王,你的手艺是越来越好了。我都做梦了。”王师傅笑了一下:“不好意思,给您惊醒了。”刮脸,洗头,再仔细检查一下。半个小时过去了。老者站在镜子前边,满意地说:“你小子一动手,我就年轻了二十岁,走了啊。”
年轻人坐在椅子上。王师傅开始动手理发。谁也没吱声。但是推子仿佛是最好的语言,刚开始时,两个人的陌生感体现在相互配合上,有些不协调。三分钟后,两个人仿佛已经是多年的好朋友。推子成了两个人的纽带。年轻人僵硬的身子变得柔软,配合着做着轻微的姿态的调整。王师傅顺手了,推子仿佛是在空中飞的自由的机器,没有一点儿障碍。年轻人也闭上了眼睛,仿佛从肩上卸下了重重的担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王师傅没有说话。他已经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别人说什么,他委婉地附和,却又清晰地表达着他的观点。别人不说,要么是个寡言的人,要么心情不好,那他也不愿意给客人增加压力。理发是一个手艺活,但在王师傅的感觉里,理发就是一门艺术。
洗头的时候,王师傅的膝盖不小心碰到了年轻人的腰,一个硬梆梆的东西让王师傅一惊,那是一只手枪。年轻人也感觉到了,嘴角咧了一下,说:“我是警察,我叫于文强。”王师傅知道这个人。在小城里,于文强不亚于市长的知名度。他大学毕业,功夫好,只身破了几件大案,三十出头,成了副局长。王师傅对职务不感兴趣。他只对头发感兴趣。洗完了,又重剪,按摩。收费五元。于文强觉得在这里理发真是一种享受。但是他又觉得不公平,师傅手艺这么好,顾客却并不多。
于文强刚走,又来了一位客人。王师傅熄灭刚点燃的一支烟,又开始了忙碌。
风铃是玻璃做的。王师傅偶然在朋友家看到,就喜欢上这种装饰品。他自嘲地想,老了,老了,还有这样的念头,好笑。但经不住风铃的诱惑。他到礼品店买了这个紫色的风铃。在盒子里,风铃是没有血肉的,但是悬挂起来,一有风,风铃就活了。它的悦耳的碰撞声仿佛人的脚步。但是风铃又是多么的脆弱,只一点点轻微的波动,它就会被奏响。它的情绪又是如此地不易平息,往往一阵风过后,所有的事物都停了,只有它还在颤动、摇晃。王师傅有时觉得风铃就是一种装饰品,一种玩具,有时又觉得风铃就是自己。
这一间店是王师傅的固定营业场所。但是王师傅还有自己的另外一个舞台。
上午,电话响了。一接,是老顾客赵粮食。其实赵粮食具体叫什么,王师傅并不知道。只知道在粮食部门工作。赵粮食在电话里说:“王师傅啊,我要办点儿事儿,你来给我理最后一次发吧。”王师傅明白了几分:“你这些日子住院了吗?”赵粮食明显笑了:“咳,咳,你小子不够意思,我都八十七了,没病。什么都好说。我叫儿子去接你。”王师傅也觉得不好意思。但这也是规矩,如果有传染病,他会带口罩,戴手套。对一些老顾客,他都会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来说一下自己做事的规矩。现在赵粮食说自己,王师傅也觉得应该。马上收拾好家什,一把老式推子,一个剪刀,一个刮脸用的刀。一辆的士停在门前。王师傅进了里间说:“别惹祸,我去干活,一会儿回来。”出门上锁,上车。赵粮食的家是一幢老楼,仍可看出当年也是上数的。王师傅坐下。赵粮食的儿子进屋,和一个老太太扶着赵粮食出来。赵粮食坐在椅子上,看着王师傅说:“我要走了,火车票都买好了。小王,你可得好好给我剪,剪好了,我得领你一块儿走。”王师傅笑了:“好哇,不行你先走一步,我这就到。”年轻人和老太太都转过脸去,王师傅看见他们的泪水。赵粮食坐不住了,他的头费力地挺着,但嘴上却一点儿不老实:“小王啊,你给我理发三四十年了,你说,你光卖我的头发能不能顶一头肥猪的钱?”王师傅说:“能顶三四头牛的钱。”赵粮食:“看样子,我这样的废物也有用。儿子,你记着,再理发你就到王师傅那,他看到你就想到我,想到我他就难受。我见马克思了,不能让这小子好受。他挣了我一辈子钱,我得报复他。”王师傅说:“是啊,人家小姑娘小媳妇扯你拉你,你都不去。出门学习三个月,非得要回来上我那儿去理发。”赵粮食叹口气:“人呐,怀旧。今天给你二百,行吧?”王师傅说:“有点儿多了。”赵粮食说:“不多,我走了,你得赶礼,活着没请到你,我走了的大烂菜你总得吃。”王师傅说:“好,好,我一定来。”那两人已经泣不成声。
临走,赵粮食握着王师傅的手,久久不放。
出了门,王师傅把用过的推子、剪刀、刀用白布裹了,一齐扔到垃圾箱里。花两元钱泡了个澡。想想,又到市场上买了二斤大虾。女人就爱吃这个。王师傅高兴就一定会买。
于文强第二次来,气色虽好,但是眉宇间有了一丝忧郁。他坐在沙发上吸烟,一支接一支。王师傅也没言语,仍细细地为顾客理发。像他这种店,大部分顾客都是四十岁以上的回头客。他做事就是这样,干就干得最好。半个多小时后,客人满意地走了。于文强坐到椅子上,掐灭了烟。王师傅边给他围巾子边说:“烟少吸点儿,人受不了。”于文强动了动脖子,苦笑一下:“没当领导时我不吸烟,当上领导了,不吸不行。也算缓解一下吧。”王师傅打开电源,推子响了起来,于文强突然说:“王师傅,这次理的时候,给我留一点棱角,短一点儿。”王师傅笑了:“好。”于文强问:“店里生意怎么样?”王师傅说:“老百姓活得简单,一家人吃得饱就行了。不像你们,也不容易。”于文强慢慢闭上了眼睛:“有时想想,还是老百姓好,面朝黄土背朝天,高兴了就干,不高兴就撂挑子。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王师傅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现在看来,我最适合理发。”于文强闭着的眼睛动了一下:“我看王师傅可不简单。”王师傅说:“你太高抬我了。我五十多岁了,站着干活也三十多年了,我干的这个活儿最枯燥,可我越来越觉得离不开这拨老朋友,这拨老朋友也离不开我。人呐,日久生情。”于文强轻声说:“现在许多事,只有利益。”王师傅端详着镜子里的头型,说:“年轻时我一表人才,能说会道,不知天高地厚,人家给我介绍对象,横挑鼻子竖挑眼,后来有了现在的媳妇,又不好好珍惜,报应啊。”
刮脸的时候,于文强说:“王师傅,这刀片在肉上走,感觉真舒服。”王师傅手上用力,嘴没闲着:“刮脸的刀最锋利,要不拿不下胡子。上岁数的人都愿意刮脸,人的皮肤很难接触到刀,刀对人的皮肤的刺激,对神经的刺激是最强的。”于文强仰起了脖子,王师傅捏住了他的上唇,刀剃胡子,剃鼻孔处的绒毛,又用剪子剪去鼻毛,之后又在脸上抹了一遍香粉。
于文强临走,碰了下风铃。风铃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
于文强羡慕地说:“你的心境真好。”王师傅说:“像我这个岁数,什么都无所谓了。”于文强回头说:“王师傅,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你尽管吱声。”王师傅笑了:“好。”
小街在火车站和客运站的对面,流动人口很多。所以各种牌子站在店铺前,仿佛摆了一桌子的好菜,只要你肯花钱,总能找到对口的卖家。那种繁华让人联想到影视里的老街。轮回,时光的轮回,人事的轮回,总有许多类似的事情在历史的某一天发生。
上午九点多钟,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民。农民在进店看到王师傅之后,眼睛就直了。王师傅在小街上干了几十年了,什么事儿都经过,但是像这么看人的事儿,还是第一次发生。屋子里就剩下王师傅和那个农民了。农民坐上椅子,很小心地说:“我姓江,叫江有财。”王师傅有些好笑,你叫什么关我什么事儿。见到王师傅没吱声,江有财又说:“我想问你点儿事儿,问错了你别见怪。”王师傅把白色的大巾子在那人领后叠好,塞进脖领,有些不耐烦:“有什么事,你就说吧。”江有财瞪着镜子里的王师傅,慢慢地说:“你继父姓王,你亲生父亲姓于,是古城于相沟的人。”王师傅的脸一下子变了颜色,原来有些笑意的脸一下子长了。王师傅说:“别说了,你说的对。”江有财说:“你也别怪你爸。”王师傅的脸红了:“我十岁,我,我妈,我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全部跪在他面前,他都不能改变主意。要不是我继父收留我们母子四口人,我们早死了。”江有财说:“你父亲看中的那个姑娘是长得俊。”王师傅苦笑:“长得俊就得把老婆孩子撇了?他有没有一点人性?”江有财盯着镜子里的王师傅:“你和你同父异母的妹妹长得太像了,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你有多少年没回于相沟了?”王师傅说:“我从离开就没想回去。”江有财说:“你亲爹岁数大了,经常叨咕你们娘们孩儿。人呐,可能会做错事儿,但做错了,改了,也就行了。血管里的血都是老于家的。你看你这面相,和你亲爹是一个模子里卡出来的。”王师傅眼里一热,想骂人,说出来却是:“我娘走了好几年了,从离开家,她没回去一趟。我那亲爹身体怎么样?”江有财故意问:“你想知道?”王师傅掸了一下巾子上的头发说:“当故事听吧。”江有财长叹一口气:“也死了,就前些日子死的。他妈的,你说,我怎么不早几个月来你这剪头?”王师傅的手明显一顿,又开始理发。
临走,江有财在门前转了好几圈,四外看得都非常仔细。王师傅看出来,他在记道儿。
晚上,王师傅破例喝了点酒。女人看他喝酒,就格外小心,像一只猫,一点声音都没有。喝得有点多,他晃晃荡荡从屋里出来,买了些冥币,找了个十字路口,跪在那里烧,一张一张卷,一张一张烧,嘴里却没闲着。嘟嘟囔囔的,一会儿爹,一会儿娘。
于文强有近一个月没来理发了。像这种回头客,什么时候该来,王师傅心里有数,前后差个三天五天的,正常。若超过时间太久,王师傅就有了几种判断,在这个人还在这个城市的前提下,一个是嫌他年老不时尚,不来这里了;再一个就是出事了。像于文强这种身份,这个年纪,不到他这里很正常,所以也没往心里去。
王师傅这儿是个信息中心,所以市里的那点儿事儿,也有耳闻。其中一个新闻就是,于文强被双规了,行贿受贿。所以于文强推开门,王师傅有些愣。看出来了,这一个多月,于文强没理发,没刮脸,所以头发很长,胡子也长起来了。王师傅急忙对在屋子里唠嗑的几个老友下了逐客令。于文强坐在椅子上。王师傅瞅了眼镜子里的人,感觉到一种距离。于文强闭着眼睛,慢慢地说:“听到不少传闻吧?”王师傅冷冷地说:“我只负责理发,别的事儿不管,也不听。”于文强说:“真好,我什么时候能过上你这种生活?”王师傅笑了:“也不是每个百姓都活得那么轻松。”于文强睁开眼睛望着镜子里的人说:“大叔,市面上的谣言,是有人要害我。请你相信我。”王师傅说:“我谁都相信。再说,我怎么看你,能有什么用呢?”于文强说:“谁都不相信我,我是清白的。你一定会知道结果的。”王师傅没再搭言,只细心地理发去了。
于文强上午来理的发,下午傍黑又来了。他坐到理发的椅子上。王师傅这个人有个特点,他总是能从刚理完的头发上看出来不妥之处,哪怕是他花费两个小时理出的头发,也能看出毛病来。所以于文强一坐下,王师傅就又忙上了。于文强躺在那里,长舒一口气,轻快地说:“总算有结果了。我被撤消了领导职务,现在是一名普通的警察了。王师傅,从今天开始,我就管你这片,有什么事儿 ,你尽管吱声。”王师傅说:“我一个剪头的,能有什么事?”于文强说:“我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了。”王师傅心中一凛,接口说:“好聚好散,两口子互相宽容一点。”于文强嘟囔着:“她为和我离婚,上纪检委告我为老人做寿大操大办,收礼,属实。解除领导职务,我一下想明白了,就签了字。谁可怜我呀?我用谁可怜?”说着眼皮渐渐地不动了。
于文强醒来,已是掌灯时分。
王师傅理发店的斜对过是个公共厕所。原先污水横流,现在改成收费厕所了,味道好了不少。王师傅从厕所出来,看到了江有财。江有财身边有个中年女人。只是背影,江有财把女人领到理发店前边就扭头走了。中年女人进屋,一看没人,往外走,和王师傅就碰对面了。
两个人都愣住了。
两个人的个头、体型、面貌太像了,王师傅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侧身进屋,说:“我不给女人美发。”中年女人似乎没想到王师傅这么说,略显沧桑的脸上涨起一片红晕。她拎着个新编的筐,筐的上面用新毛巾盖着。王师傅见过许多这样的乡下女人,拎着鸡蛋鸭蛋、野菜野果走街串巷。有时他就想,一筐蛋卖个三十五十的,去掉车费吃饭的钱,能剩几个钱?在家干什么不挣个三十五十的。他有些不屑。一次,一个卖野菜的女人中午到店里要水喝,王师傅给倒了杯热水,女人从筐里拿出个馒头啃起来。王师傅问:“你卖了钱了,去饭店吃一顿得了呗?”女人笑着说:“大哥,我一顿饭花三元五元,够俺孩子在学校吃两天,这一趟才卖四五十块钱,去掉车费剩三十,我可下不起饭店。”王师傅这才有点明白,原来有些人过日子,到了今天还是以元、角、分来算计的。
中年女人把那筐放下,说:“家里也没什么好东西,攒了一百个鸡蛋,给你和嫂子吃。”王师傅火又来了:“你拿走,我不认识你。”中年女人眼泪就下来了:“大哥,老人都不在了,是我妈的不对,我向你道歉。可我妈也背了一辈子的屎盆子。进土就进土了,我也不求你什么事,就是来看看。”女人说完扭头走了。王师傅追出去,一直看着那个身影消失。他进屋,把那筐鸡蛋放在沙发上,掀起毛巾,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
于文强来理发,竟穿着警服。王师傅很意外。于文强坐到椅子上,摘下警帽,笑呵呵地说:“以前出门哪敢穿警服?现在好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小片警。”王师傅端量了一下镜子里的并不长的头发,说:“咱们换个头型?”于文强说:“身份变了,但人没变,还要那个头型,我就这个作风。”王师傅随声说:“换个角度看生活,你说多有味道?咱们吧,有朋友、有亲人、有咱们牵挂的人、有牵挂咱们的人。有情有义的平凡生活。”于文强说:“领导难啊,他哪能有这种心态?工作要成绩,事业要高升。上哪找清福?看咱多好?”王师傅说:“什么时候当新郎,我免费给你理发。”于文强笑了:“王叔,你怎么这么寒碜我。我离婚才几个月,哪来的对象?”王师傅肯定地说:“现在五月份吧?我先放个屁搁这儿放着,不出一年你就能再婚。”于文强怀疑地说:“你上哪看去?”王师傅说:“你等着吧,别忘了请我吃喜糖。”于文强说:“行,你要说准了,我认你当老干爹。”王师傅叹口气:“我哪有那个福分。”
窗户开着,一阵微风,风铃晃动起来,那声音像什么呢?有瓷器碰撞的味道,有铁器与玻璃相击的感觉,有水珠从高处落入静潭的回味,甚至有一点短促的回声。此起彼伏的,好像声音被串成一串,忙不迭地被扔在地上。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一阵细小缓慢的歌声从里屋传出来。声音像少女一 样娇羞,似乎害怕惊动了什么,但又抑制不住激情。甜润、轻快、活泼。
于文强有些奇怪地瞅着镜子里的王师傅。王师傅似乎有些意外,所以把推子从头发上拿起来,怔在那里,只片刻,他就感觉到镜子里疑惑的眼神。他的脸一下子红了,五十多岁的人,从事室内的职业,显得很白,所以脸红得异常明显。王师傅颇不好意思地说:“我老婆,不好意思,打扰你休息了。”于文强笑着说:“师母的嗓子真好。”王师傅进了里屋,轻声说了几句什么。歌声停下来。
于文强又闭上眼睛。
里屋传来电视的声音,很小,小到几乎听不到说什么。在于文强的感觉里,只有坐在离电视不足一尺的地方听,或许能听到。这是里屋最正常的声音。于文强在这儿理发半年多了,每次来,里屋都是这种声音。而这种声音又告诉于文强,里屋有一个女人,从来不露面的女人。
于文强进屋的时候,王师傅看出了异常:于文强没穿警服。于文强坐到椅子上,一躺,长舒一口气,眼睛又闭上了。王师傅说:“你怎么长了这么多白头发?”于文强苦笑道:“快全白了。”王师傅瞅了瞅镜子里的那张憔悴的脸,于文强的眉头始终是紧锁的,仿佛是有意皱眉头。王师傅知道,那是紧张造成的。
于文强睡着了。王师傅先是轻手轻脚,后来干脆住手了。他走出店门,站在小街上晒太阳。
邻居是个女老板,约王师傅好多次。女老板说:“大哥,我这儿有干净姑娘,你不解解渴?”王师傅笑了,摇头。女老板说:“你买卖那么好,攒那么多钱干什么?两腿一蹬,你什么都没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王师傅说:“白费呀,我没那个能力呀。”女老板不明所以,忙说:“有药呀。”王师傅扭身就走。
现在,看着小巷里那些花枝招展的女孩子,王师傅习惯性地转过身。
他看见于文强在小店里睡得很香。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在他的脸上,那是一张多么有朝气的脸啊。
于文强醒来,很不好意思。临走,于文强面无表情地说:“我又高升了,我是这片儿警务局的局长。”王师傅说:“好好干吧。”于文强整理了一下衣服,走了出去。
王师傅看着那背影,有些陌生,又有些熟悉。
一天傍晚,要关门了。一个女人走进来。女人穿得很好,保养得也好,一看就是那种贵妇。王师傅边扫地边说:“对不起,我只给男士理发。你走错地方了。”女人站在那里没动。女人自言自语地说:“一点儿都没变。你不认识我了?”王师傅说:“不认识。”女人叹口气:“王一摸,我是小蝴蝶。”王师傅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我不是王一摸。”小蝴蝶笑了:“王一摸,二十多年前,叫响小城的王一摸,你死了我都认得你的骨头渣子。”王师傅毫无表情地说:“王一摸死了,二十多年前就死了。”小蝴蝶有些激动:“人可能死了,但是那一段岁月谁也不会忘记。嫂子现在还好吗?”王师傅说:“王一摸死了,她就过上平稳的生活了。”小蝴蝶环顾了一下小店,缓缓地说:“王一摸是专门给女士美发的。可惜他现在却只给男人理发。”王师傅叹口气说:“一切都是报应。”小蝴蝶盯着王师傅:“王一摸的手艺多好,小城有多少女人都希望能让他给美发,那是时尚、漂亮、个性的代名词。不就是摸一下吗。当着大伙的面从后面抱着摸一下乳房,放松神经又提高双方的兴奋性,多科学。如果是暗地里,那是不道德的,公开场合,那就是一种挑战,向世俗和道德挑战。有什么不好?”王师傅坐下,点燃一支烟:“是啊,最后还是王一摸承担一切。”小蝴蝶说:“这也不能怪王一摸,谁叫他媳妇疑神疑鬼。”王师傅吐了一口烟:“王一摸没福分。宽容和谅解是有限度的。”小蝴蝶说:“谁都有过青春年少。可能我也有责任。刚和男朋友分手,就想发泄一下。我真的没有什么恶意。”王师傅说:“王一摸也明白。可是他媳妇怎么想?自己的男人手里握着别的女人的乳房,在五六个人的笑声里激情长吻,她会怎么想?”小蝴蝶低下了头:“嫂子出事之后,我就离开了这个城市。我也无法原谅自己。我想对嫂子说声对不起。”王师傅说:“王一摸死了,他媳妇也开始了新生活。平静的日子多好。”
屋里传来女人的哭声。仿佛受了很大的委屈。而且声音越来越大。却又明显地抑制。小蝴蝶恳求说:“让我见见嫂子吧。”王师傅站起来:“如果你可怜王一摸的媳妇,就请你走吧。她受不了陌生女人的声音,对她来说这是一种刺激。”小蝴蝶流下眼泪:“王一摸还是值得去爱的。他能和一个几乎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的女人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他是一个好男人。”说完,小蝴蝶缓缓地走出了屋子。
王师傅冲到窗前,一个背影在夜色里模糊起来。
被撞到的风铃,叮叮当当地响起来。
王师傅关上门,扭身进了里屋。
北方小城冬天有雪。
雪天活儿少。几个老友坐在小店里神侃。一对男女捂得只露眼睛进了屋。男的脱下帽子,是于文强。于文强说:“理发。这是我的老干爹王师傅,这是我媳妇小雨。”屋里的人穿戴好都走了。小雨说:“王师傅,我家文强天天叨咕你。”王师傅笑了:“姑娘,你眼力不错呀。”于文强坐下:“王师傅,我有点事儿。我想辞职,还想去干片儿警。”王师傅刚要开口,小雨从沙发上站起来:“这事儿你怎么没跟我说?”于文强笑了:“现在说还晚吗?”小雨有些火:“于文强,你听好了,我可是二十几岁的大姑娘,比你小十岁,你还是二婚,要不是看在你是分局局长的份儿上,我还不干呢。你今天辞职,咱俩今天就分手。”
于文强看了眼镜子里的王师傅,王师傅也正在瞅他,有那么三秒钟。然后,于文强闭上了眼睛,慢慢地说:“我这不是逗你玩吗?”
一阵风吹来,窗户都跟着晃。风铃被震了一下,叮叮当当地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