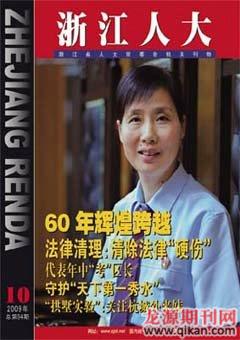突发事件问责的制度路径
单学刚 竹立家 陈 潭
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等对突发事件处置不当者的问责方式在规定中得以明确。如何科学理解这一新规定?如何将问责落到实处?当前的问责制度还存在哪些缺陷?有关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解读。
问责的制度化推进
□自从2003年非典疫情处置不力导致时任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等官员被免职以来,“问责制”逐渐走入了公众的视野,这次规定的出台可以说是将“问责”制度化。首先请嘉宾谈一谈这个规定出台的时机和意义。
■竹立家 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尤其是2008年我们国家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这标志着中国社会的转型速度在加快,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突发期开始出现。因此,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负有决策和领导责任的干部必须对党、国家、民族和人民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出台了《暂行规定》,它可以减少随意行政、人治行政和恶性行政。
□规定指出了7种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情形,其中有一条就是“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请问竹老师,这几年突发事件越来越多,而且涉及面越来越广,基本上各个民生领域,都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这是因为官员的责任心、素质越来越低了,还是公民的民主意识增强了,学会了维权?
■竹立家 两方面因素都有,一方面确实我们在选人用人方面,我们的机制不是很健全,所以从石首事件和瓮安事件看,确实存在一些官商勾结的问题,这表明我们的一些地方基层官员的素质不是很高;另一方面,随着信息的加快,我个人认为网民的素质越来越高,群众的参与意识越来越强,所以说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国人的参与意识民主意识越来越强,官确实越来越不好当。因此,只有那些素质高、品行好、愿意和敢于对人民和党负责任的人,具有公共精神的人,尊重群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人,才能当好官,才能当好人民满意的官。我曾经讲过,群体性事件破坏性升级不是老百姓的要求多了,而是官员的责任心少了。为什么官员的责任心少了?主要是由于某些官员的利益不是与老百姓联系在一起,而是与官场和商场联系在一起,看到这一点,就看到了中国群体性事件增多的原因,和产生群体性事件的症结所在。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加大对官员的素质品质教育;另一方面还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让老百姓、社会中介组织、政府共同治理社会,加速中国公共生活领域的民主化进程。
□有人说,我国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近期才千呼万唤始出来,很多人都认为姗姗来迟,充其量算是一份迟到的惊喜。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具备官员问责制度的前提下,为什么在今天却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才孕育出来。请您分析一下这方面的深层次原因。
■陈潭 一个国家的制度成长需要时间和过程,古代也有官员问责,那是对皇帝负责,那是一个家天下的问责制。同时也是一种选择性问责,皇帝不喜欢的就问责,喜欢的就不问责了,那是一种特权下的问责制和家族制下的问责,与现在制度下的问责不可同日而语。其实在共和国的60年历史当中,我们大大小小都有很多问责,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了,但是原有的问责并没有被制度化,因而存在不少的问题。基本上也是一种人治问责。今天的问责制度化姗姗来迟,我想也有以下原因:第一,现有的领导干部人事制度是一种刚性体制,缺乏弹性,官员没有形成一种能上能下的机制;第二,自己问责自己,毕竟还是有些难处;第三,整个政治生态比较单一化,只在官员内部讨论问责的问题,没有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参与到问责系统当中来。
问责的制度性缺陷
□不少人认为,目前我国的问责多少流于形式,存在“替罪羔羊”现象——需要问责时找个下面的小官员来免了就是。
■陈潭 问责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缺陷,表现为问责的主体方面就是同体问责,不是异体问责,用俗话说就是:自己问自己。第二个问题是问责的客体,我们到底“问”谁?现实中多问“政”,少问“党”,有些决策是党的一把手做出的,而要政府的一把手来承担责任。我们大多数时候只问责“打仗的”,很少问责“拿指挥刀的”。
第三个缺陷,问责的范围与层级。问责要问到哪一级得明确。科长出了事,处长要承担责任,处长出了问题,厅长要承担责任。在问责范围这一块,与群体事件发生的直接责任人都要受到问责,不能有的问了,有的没问,问责不能特权化。
第四个缺陷,问责的结果。民众普遍关心问责问得怎么样,不少人认为有些问责流于形式。比较多的问题官员的悄然复出,说明我们的问责制的执行力不够强。
□陈教授刚才提到缺陷中的同体问责,实质上也是我们现行很多好的制度难以收到实效的原因,既是球员又是裁判的现象屡见不鲜。请问出现这类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陈潭 “同体问责”这是体制上的原因,既是球员又是裁判,边裁和比赛监督也是自己人。模糊了一些“越位”,漏掉了“红黄牌”,出现了“黑哨”和“官哨”的现象。这也是中国社会的劣币现象。我觉得中国的政治问责体系当中,我们要区分两个系统,一个是公务员系统,一个是政治家系统。公务员更多的是考入和任命制度,主要是执行。政治家系统是选举产生的,他更多地行使决策的职能。我们的体制模糊了、混淆了公务员系统和政治家系统,都把他们看成是党政领导干部,这是有问题的。有时问责要更多地问到政治家系统,也就是决策者身上。
其实,我们今天的问责还存在一个“面子”和“人情”的现象,这是中国特有的官场文化问题。因为大家把国看成是家的放大,“家”里面的问题,兄弟姐妹可能以相互体谅的姿态来对待某个人的错误,家长的权威有时还起着关键作用。要想挑战家长的权威、改变兄弟姐妹的亲情关系是有难度的。
□有基层干部反映,当下一些被网络广泛关注的问题常被问责,没有被关注的则少被问责。毫无疑问,网络在过往的问责事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请嘉宾谈谈网络监督在问责时代的意义。
■竹立家 一般来说,问责有两种性质。一种就是体制内问责,包括我们纪检部门、组织部门及人大。另一方面,是体制外问责,就是新闻舆论和人民群众,通过各种形式对一些官员乱用公共权力和个人行为品质进行监督。所以说,我们首先要区分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问责形式。在国外对于政务官的问责,主要是通过舆论形式实现。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德国某一市长,由于违反政府规定,在坐公交车的时候没有给一位60多岁的老妇人让座,被社会公众问责。虽然这个人在电视台连续向全体市民道歉,但是最终在市民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下辞职。公众的意见是让这样一个没有爱心的人当市长,他很难为市民提供完善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也很难爱护公共利益,必须下台。所以,我个人认为,网络监督是我们实行和实现问责制的一种必要形式,应该肯定。
问责的制度路径
□请问,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后,从官员的角度出发,该如何处置才是最妥当的?
■竹立家 我曾经在哈佛做过访问学者,在哈佛的时候也学习到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和做法,我个人有些体会。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政府要在第一时间把事件的背景和过程向社会公布,做到公开透明,因为任何群体性事件都伴随着谣言,消除谣言的最主要办法就是公开透明。
□有人说一些重大的公共事件相关领导易被问责,而日常工作中违规失职造成损失就难被问责。我们看到在这个规定里,对日常“决策严重失误”等问题的问责也做了确定,但是,诸如“重大损失”、“恶劣影响”在执行过程中如何进行评判和监督呢?
■竹立家 这也是我所关心的问题。我建议我们在暂行规定出台以后,还应该有一个细则来进行一个界定,对各种事件要有一个基本的细致描述,我们的一些法律法规不少,但是往往执行不到位,所以必须出台一些细则,使我们的法律法规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
□对于这些被问责官员,特别是年轻官员,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恐怕“一棒子打死”也不是一个很科学的态度。是否应该再给他们“东山再起”的机会。
■竹立家 首先我想说明一个观点,什么是领导干部问责,问责不是纪律追究,也不是法律追究,问责主要是道德问责、政治问责和行政问责,换句话说,就是由于官员行为不当,对整个社会造成重要的道德影响、政治影响。问责的对象主要是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和主要领导责任,具有决策权的领导干部,这些人在西方叫政务官。问责的范围不是全体公务人员,而是公务员里的政务官这一部分。事务官属于执行层面的官僚,这些人在个人行为中出了问题,有纪律追究和法律追究。我们知道被问责下去的官员一般来说都负有重要的道德政治和行政责任,这就是说,这些人从个人品质来说,已经没有正确行使和运用公共权力的能力和素质,不适宜担任领导工作。
■陈潭 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复出要考虑官员的历时性政绩,不能因为一时一事,而全面否定一个人。往往想有一番作为的官员可能更容易绊脚,我们对问题官员也要区别对待。有些人不干事,他是个庸官,他肯定没问题,这种不作为的官员有可能比有问题的官员更没有责任感。所以我们要反对因为问责制的存在而不作为,实质上庸官更要问责。因此,问责制的推行,要与绩效考核挂起钩来。
(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公共行政理论等。陈 潭:中南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公共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