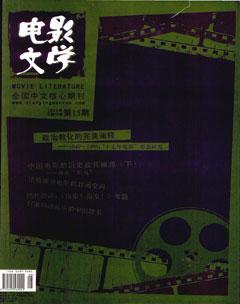底层写作的困境
金宏建
[摘要]新世纪以来,底层写作蔚然成风,贾平凹的长篇新作《高兴》就是其中之一。底层写作的困境在于:底层写作不等于艺术优势、底层写作如何理解个体权利的建立、底层写作如何避免类型化写作。本文试图在这几方面给以解析,以期使底层写作在新世纪茁壮成长。
[关键词]底层写作;艺术优势;底层表述;类型化写作
《高兴》是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于2007年9月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一出版即受到批评界的热烈称赞,认为该小说是对社会转型期间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探索的自觉担当,准确地呈现了精神嬗变的轨迹:写出了底层民众从生活自救到精神自救的乐观与顽强韧性:它以乡村精神和共鸣姿态,拓展了新的思想和艺术表现空间。从作品内容层面上来说,这些说法都是较到位的,但是,关注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精确呈现了时代精神嬗变的轨迹、具有乡村精神与共鸣姿态的作品就一定是好作品?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重新回到对文学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文学与现实(包括底层现实)关系如何?文学如何表达底层等问题的探讨之中。
一、底层写作与艺术优势
近几年来.随着底层写作思潮的兴起,有关底层苦难的叙事层出不穷,贾平凹的《高兴》就是底层写作的作品之一。贾平凹在《高兴》创作后记中这样谈到: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作者以知识分子对农民特有的关照心态.如“时代的记录者”一般忠实地记载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态,体现出作者对底层的关怀。但是作家除了呈现进城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体现出知识分子对底层的关怀外。还能告诉我们什么呢?而对这个“什么”的回答才牵涉到文学作品的艺术意味问题,作品的艺术魅力才能由此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写底层并不意味着一定是有艺术意味.底层写作不等于艺术优势。
《高兴》写的是以刘高兴、五富为代表的农民在城里无根飘荡的生存状态。是对当代进城民工日常生活的一次还原性呈现。作品的主角刘高兴和五富因为“清风镇就那么点耕地,20世纪90年代后修铁路呀修高速路呀,耕地面积日益减少”而进城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乡土为家园的刘高兴们,由于家园的日趋凋敝,在乡土中看不到希望,只好把目光转向城市,盲目地进入城市。在城市里,刘高兴们被动或主动地处处设法融入城市。但每一次试图和城里人的交流都以失败告终。刘高兴们精神上属于“乡土的世界”,城里的文化和人很难接受他们,甚至排斥他们,受人欺凌、摆布、愚弄的处境成了进城农民工的常态,刘高兴们陷入了巨大的时代旋涡中。农民被裹挟在“现代化”建设的人潮中,农民与“现代性”的生活纠缠在一起,究竟意味着什么?农民的精神上的乡村与身体的不得不融入城市的碎片化生活,又意味着什么?这些最能构成作家作品艺术意味的问题。作家在哀婉与感伤中感到茫然而惶惑,作品中农民工现实生活的碎片化就等于作家创作的碎片化。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是对现实的反映。不是文学等于现实。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必然给每个生活其中的人带来变化,而一个作家,特别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则应该突破我们时代大多数人对现实的感受和一般的文化性理解.建构起一个艺术世界。农民精神与现实生活的分裂状态,完全可以通过作家自己的独特理解,或显现现实的缺憾,或弥补现实的不足,给人以启示。“如果作者对主人公的生活持怀疑态度,那么,作者就可能成为纯艺术家;他将始终以超越性的完成化的价值与主人公的生活价值相对立,他将从完全不同于主人公从自己内部经历生活的角度来概括生活;叙述者的一言一行都将尽量利用观察上的根本优势,因为主人公需要超越性的确认.而作者的视角和积极性,也正是在主人公的生活面向自己外界的地方,才会对主人公的基本思想涵义界限做出本质性的把握和加工。”¨巴赫金对作者应有超越现实的思想能力和把握现实的能力的强调可谓掷地有声。当今农民工生活的碎片化是现实给予我们的事实,这事实只能是作为材料,参与到贾平凹艺术世界的建筑中去,发挥出不同于现实的意味。再真切如实的记录原生态生活.也只是呈现的现实而不是艺术。构筑艺术的材料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非现实的,关键在它必须有艺术意味。这就意味着,写底层内容与写非底层内容,对文学创造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关键在于作家对底层与非底层内容的理解,即建立起自己的“超越性的完成化价值”。
二、底层写作与个体权利的建立
当下写底层的文学作品多表现底层生活苦难、艰辛,并已成为底层写作的固定模式。底层的内涵主要是苦难、艰辛吗?从政治经济学与文化视野的角度,底层可以被界定为这样的特征:第一,政治学层面——处于权利阶梯的最下端,难以依靠尚不完善的体制性力量保护自己利益,缺乏行使权力的自觉性和有效途径。第二,经济层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匮乏.没有在市场体系中进行博弈的资本,只能维系最低限度的生存;第三、文化层面——既无充分的话语权,又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因而其欲求至少暂时需要他人代言。从这三个维度对底层的界定来看,写底层的苦难、艰辛,只能维系最低限度的生存的现状,体现底层普遍不具备完整表达自身的能力,因而其欲求至少暂时需要他人代言的状况。但是政治学层面的内容却被忽略了,这更切近问题的根本和出路,也更有分量的内容。缺乏这些内容的底层关注,造就底层的政治体制未被触及和改变,底层写作就会成为无理想和方向的写作。没有理想。苦难就不能变为改变的动力:没有方向,作家只能受制于现实。
贾平凹在《高兴》创作后记里这样记录了自己的创作经历:最先是想写出刘高兴们如何进城、如何安身生活、如何感受认知城市——让更多的人了解。觉得就满足了:然后用严重的农民意识,即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视城市的心态创作,没能完成写作;再次以刘高兴原型“得不到高兴仍高兴着”的精神状态,完成了“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的人物塑造.写完了作品;最后改用第一人称完成定稿。作者从构思到创作,最想突出的是代言身份、同情心以及人物盲目的“高兴”生活状态。仔细分析会发现,作家在为底层说话之时,已经假定在自己与底层之间存在等级差异,底层是不能发声的。只有代言底层才能发出声音,知识分子的某种优越感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底层无法发出声音的真正原因被这种优越感的知识分子遮蔽了。按理说刘高兴们有自己的趣味、生活理想、生活方式、话语,为什么面对社会却无法发出声音呢?是什么力量让他们不能发声呢?转型期的中国是把“我们”主体还原为“个体”主体的时期,当家作了主人的农民们的主体权利,如何在改革大潮中变为个体农民的主体权利,“我们”的权利如何落实到个体权利层面,是目前我国社会机制建设的薄弱点。正是在这一点上,农民工失语了,即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构成的社会机制制约着他们的表达。文学不
揭示和消解这种有缺陷的社会机制,作家的代言就会找不到方向,也无法指出底层获得救赎的前景。贾平凹给他作品中的人物设计的“让自己活得高兴些”的做法,不指向对社会机制缺陷的改革,只能成为无奈之下的软弱的自我安慰。“去不去韦达的公司,我也会呆在这个城里。”这是刘高兴在小说末尾发出的心声。如果刘高兴一如既往地没有个体权利意识的萌发和生长,刘高兴一辈子留在了城里,也只能是不能发声的沉默的底层,有希望的底层不会站立起来。
三、底层写作与类型化的表达方式
“内容形式化和形式内容化”是创作方法与文学的关系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文学作品的任何创作方法和技巧.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故事、情节和气氛,既不是独立的存在,也不能嫁接和模仿,而必须由作家对世界的独特理解“生长出来”。形式与内容在作品中是一个有机组合.无法分离,偏向任何一方都会因为有机性的被破坏,失去其审美性。《高兴》最为人称道的是用了第一人称手法、追求细节白描手法的精湛等等,而不是在作品整体意蕴上体现其艺术魅力,作品的艺术意味只能打折扣了。
《高兴》被称为是近几年底层写作中第一个以第一人称叙事的作品,其优点是直接呈现底层人物心态及其琐碎的日常生活,体现底层驳杂而丰富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增强了底层人物的在场感,知识分子替底层代言成为可能。同时消解了过去乡土表达的启蒙成分。这样理解人称使用的作用,太过笼统。用第一人称写作更能突出知识分子替底层代言这一倾向,是显在的事实。但是知识分子的关怀只是知识分子生存层面的状态,这一状态并不能证明作家创作出的作品的艺术成就。贾平凹写《高兴》时所作的大量生活调查、众多的素材积累乃至用第一人称叙事,都只是作者创作时所采取的创作方法。但是,作者最后要告诉我们的,除了底层的无根性飘荡状态、作者对苦难的焦虑和无奈,还能告诉我们什么?如果《高兴》所用创作方法达到的这些效果,同样是其他作家如罗伟章写底层的小说、胡学文写底层的小说等等都达到的效果、都体现的内容,那么,贾平凹用第一人称等创作方法达到的效果只能是类型化的写作。即表达内容一样,表达方式多样罢了。
贾平凹在《高兴》后记中这样说自己的创作:因为情节和人物极其简单,在写的过程中常常就乱了节奏而显得顺溜,就故意笨拙,让它发涩发滞,似乎毫无了技巧,似乎是江郎才尽的那种不会了写作的写作。这句话突出了作者细节上追求白描精湛的特点。在诸多精湛的细节白描中.刘高兴与孟夷纯谈恋爱,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他们的爱情描写不由自主让人想起传统“才子佳人”故事模式,刘高兴如落难的“才子”,妓女孟夷纯如“佳人”,同样生活在生活的最底层,危难中凸显爱情的浪漫意味。他们的爱情为什么不成功?这本来是个内涵与外延均可放大的细节,作者却用一般性的理由毫无新意地解释了不成功的原因:刘高兴的地位底下,担当不起孟夷纯的日常生活开销;孟夷纯的妓女身份,也不能保证爱情的纯洁性,他们之间的爱情只能是不成功。细节内涵上的类型化描写,显示出作者对既生机勃勃又浑浑噩噩的刘高兴们的生存状态的无以把握,更不要说给人人类性启示了。我们注意到谈鲁迅的作品,只谈“白描”或重点谈“白描”,都只能是对鲁迅文学作品的整体哲学意蕴的忽视.因为一部优秀的作品,其语言、技巧、人物、创作方法等都只能由作家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派生出来,一个作家专注于作品语言和细节上用力,而忽视用力的语言和用力的细节是为了体现自己怎样的对世界的理解,其语言与细节表现的内容只能是大同小异。
类型化的写作,只能意味着作者不能通过自己对现实的把握,建立起“超越性的完成化价值”,进而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给人以启示。“一个小说家能够用别人尚未试过的方式来讲故事,总是因为他已经想好了一个别人从没听过的故事。”贾平凹能给我们一个从没听过的故事吗?我们期待着。
[参考文献]
[1]冯德华.做时代的记录者[N].文艺报,2007一12-01:001.
[2]贾平凹.高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3]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王晚华.当代社会文学如何表述底层?[J].文艺争鸣。2006.
[5]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76.
[6]吴炫.什么是真正的好作品[J].文艺争鸣,2007(05).
[7]王晓明.“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A]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c].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5.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