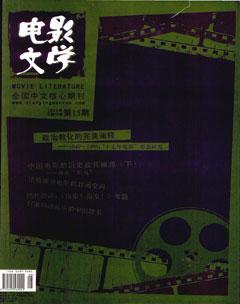中国电影的历史及其根源(下)
钟大丰
实用理性精神的实践体系
电影,一种极好的教育工具
尽管中国电影在其发展道路上曾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复杂影响,但电影毕竟是一门艺术,它的成长必然无法回避电影艺术规律的制约。电影虽然是在西方文化中诞生出来的一门新艺术,但它一旦在不同的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扎根之后,由于不同民族生存的文化环境和传统的不同。自然会使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电影被打上其本民族的深刻烙印,呈现出风貌迥异的形态来。电影一来到中国。便很快地与中国既存的民族的文化艺术和审美传统迅速地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电影思维和艺术方法的体系。中国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的审美心理传统的深刻影响。这有的是创作者有意追求的结果,但更多的是文化心理积淀的无意识流露,它们影响着中国电影民族风貌的形成。由于中国电影所处的历史环境,使大多数的中国影人对电影的认识和创作方法都受到戏剧经验的深刻影响,这使中国占主流地位的电影观带上了浓烈的戏剧化色彩,所以我们把这一体系称之为“影戏”。
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影戏”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于艺术和电影的思维方法。中国是一个注重实践的民族.这使得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带上了一种实用理性的精神。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并不致力于建立一套抽象的电影美学。而是发展起一种与流行的影片类型直接相关的实践体系。“影戏”观正是这样的一个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的实用美学。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的“文以载道”的思想传统,使得中国人进行电影创作时对电影的功能特别重视.成为一种有强烈伦理目的的论色彩的功能美学。同时,由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侧重于直观整体地把握事物,使得中国人对电影的认识也更注重影片的整体把握,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剧作和情节方面,而不是在镜头和影像的水平上。“影戏”作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电影观念体系。它几十年来随着中国电影的实践不断地发展演变着.但其核心内容又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决定着中国主流电影的艺术风貌。
“影戏”反映着中国电影工作者对电影的基本认识。中国影人对“电影是什么”这个历来被电影实践家和理论家都十分关心的问题所做出的回答。直接影响着电影创作的面貌。在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们看来,电影既不是对自然的简单摹写,也不是与内容无关的纯形式游戏.而是像戏剧一样的一种艺术。艺术,首先是一个意义的表达体系。中国人之所以重视“文以载道”,正是因为他们首先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艺术的。因此,中国人在把握电影的时候,从一开始就遵循着一条与西方影人相反的方向。它们不是从结构的角度出发,把电影看做一种与戏剧等其他艺术相比具有独特的艺术语言的“独立”的艺术;而是从功能的角度出发,看到电影具有与其他艺术一样的意义表达能力.因而才认定电影“也”是一门艺术。由于电影已经是一门公认的传统艺术。所以人们从电影与戏剧在意义表达的功能方面的共同特点来认识电影的艺术地位。戏剧是一门艺术,而电影与戏剧有在意义表达的功能方面的共同本质.所以电影也是艺术。这种从功能目的出发把握电影的方法.既是对中国“文以载道”的艺术传统的一种继承.也是中国人注重实践理性的思维传统的一种体现。对于中国的艺术家来说,拍电影从来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一种社会行为。他们把电影作为一种极好的教育工具.努力通过自己的创作达到“表现人生、批判人生、调和人生、美化人生”的目的。而且把这看做是电影能否在艺术的园地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关键。
当然。对电影功能的这种注重并不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意义上,而是与特定时代的具体社会条件和文化思潮紧密相关的。它具体地演化为对电影与时代、电影与社会、电影与人民、电影与政治等一系列的关注。尽管艺术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文化观点可以不同,但在有意识地追求某种社会功效这一点上却往往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多少可以归因于“影戏”以功能目的论为基本出发点的思维方式。这种电影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电影许多方面的艺术风貌的形成。
从自发的功能目的的期望
衍生出自己的本末观
在不少中国人看来,“影戏”作为艺术,与其说是由于其特殊的艺术手段,不如说是由于其所具有的表现功能。由于这个原因,加上电影作为一种商业性娱乐对市场的现实要求.以及早期中国电影队伍构成的历史渊源等因素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主流电影在艺术风格上的价值取向和追求。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还是作为一种娱乐产业,电影都必须努力赢得尽可能多的观众。而对于作为中国电影观众主体的城乡中下层平民来说,最适合他们在长期接触的戏曲和民间说唱艺术的文化传统的熏陶下形成的欣赏习惯的,莫过于那些具有强烈的戏剧性的影片了。而早期中国电影的创作队伍的主体也源于这同一个文化传统中所衍生出的“文明戏”。所以,“影戏”这种带有强烈的戏剧化色彩的电影能在中国影坛中赢得主流的地位.正是这双方面的共同需要的结果。“影戏”电影的主导地位一旦确立.它又反过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电影工作者和观众对电影的理解和需要。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电影的面貌在不断地改变,但这种出于社会功利的出发点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时有强化。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电影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的地位日益突出。尤其是在从1957年到1977年的20年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更是左右了电影艺术发展的方向。随着阶级斗争日益成为文艺作品的核心内容,“影戏”在艺术风格的把握和艺术手法的运用方面也越走越远。戏剧性冲突和矛盾成了表现阶级冲突、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直接工具.构图、光线、影调等电影的视听时空构成因素随之成了特定的政治话语和语言元素。这一切到了“文革”电影中被推向了极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突出”的所谓“创作原则”和“敌远我近、敌俯我仰、敌暗我明、敌冷我暖”的一套荒谬的公式,既是那荒诞时代畸形的政治生活的产物,同时又有其艺术思维方法方面的深刻渊源。由此可以看到“影戏”从其发自功能目的的期望衍生出自己的“本末”观。
“影戏”从内容表现的具体功能出发.而不是从影像和镜头等影片的具体构成因素出发把握电影。电影首先或主要是被看做一种戏剧性的叙事艺术。“影戏”一词的重点是在“戏”上。在“影戏”对电影的基本认识中,“戏”是电影之本.而“影”则只是完成“戏”的表现手段而已。人们对于电影本性的认识,是从把它看做是戏剧艺术的一种延伸开始的。上世纪20年代徐卓呆曾说过,“影戏虽是一种独立的兴行物,然而从表现的艺术看来,无论如何总是戏剧。戏之形式虽有不同,而戏剧之艺术则一。”把电影看做是戏剧。或认为电影与戏剧在基本艺术规律上是相同或至少是相通的.这可以说是中国最初建立起的电影观念的核心。“影戏”不单是一个简单的译名,它反映着人们对电影的认识。“影戏”一词是从戏剧引申出来的,这一点包
天笑和张石川等人都曾有过论述。同是20世纪刚刚诞生,由西方传入的电影和电视,在早年被人们取了两个极富象征意味的名字。当中国人刚刚知道有电视这么个东西时,就马上感受到了其作为一种建立在远距离传输声像信息基础上的新技术媒介特点,给它起了个音义结合、形神兼备的译名“睹影闻声”(Television)。而电影(Motion Picture)虽然最初也是作为一种使固定的影像活动起来的新技术来到世间的,但它来到中国虽曾有人称之为“活动影画”,可这个名字并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后来还是叫成了“影戏”。电影从开始就被看做是一种变相的演出活动,周剑云说:“影戏是不开口的戏,是有色有声的戏.是用摄影术照下来的戏。”到后来电影的声音和色彩都具备了,其“戏”的性质便更受重视。
中国人自己的电影制作从《定军山》开始,这本身就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现象。它从一开始就显露出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戏剧经验结合的端倪。由于初期中国电影创作队伍的艺术渊源,也由于这种观念的指导,“影戏”作为一种演出活动,从一开始就在创作实践中大量借鉴戏剧经验,在无声电影时期就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电影形态体系。在其后的几十年里,虽然人们对电影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文学进入了“本”的核心.人们从把对电影看做是以“戏”为中心的艺术,改变为将其作为一种为以形象的叙事表达为中心的艺术来看待。与此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声音进入电影,几十年来电影艺术本身的巨大进步以及艺术家们对电影艺术技巧掌握的日益全面和娴熟.也使“影”的因素在不断地丰富着。但是在许多中国电影工作者的眼中。电影与文学和戏剧等传统的叙事艺术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本同而末异”的。而且“文学的共同规律是本,是第一位的,电影的特殊规律是末,是第二位的。”由此可见。这种本末观从未发生本质变化,所不同的只是视野有所扩大罢了。
戏剧性的叙事本体论
包括性极强的超稳定结构
作为电影观的核心对于电影本体论的认识方面,中国影人采取了与西方人不同的思路,建立起的也是一种不同的电影本体论。这是一种以叙事表达为核心的电影本体论。人们认为对电影的基本结构和功能的把握应建立在“戏”的基础上。把与影片的叙事整体相联系,有利于直接明确地表现作品含义的“戏”看做是电影的本体,而把和具体镜头相联系的“影”的因素看做是完成“戏”的表现手段。基于这个原因,对于电影剧作的重视在中国电影的发展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其中对于戏剧性叙事的推崇和关注显得尤为突出。早期郑正秋、张石川等人“惟以剧情见胜”的成功秘诀.左翼文艺家从编剧人手改造中国电影的努力,解放后的电影题材规划,历久不衰的关于电影的戏剧性和文学性的讨论等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中国人的这种电影本体论。
中国人对本体论的理解。并不是从抽象思辨的意义上去探讨,而是以实用的态度去对待的。从以剧作叙事为核心的电影本体论出发,很自然地使中国人对电影叙事的应用规律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在对这一规律的探寻中。中国古代的小说及民间说唱艺术等通俗叙事艺术的经验为人们提供了不少帮助。故事的传奇性和情节的曲折性,在强烈的戏剧性冲突和跌宕起伏的情节进展中展现人物命运和心理历程,这些都成为影片艺术表现的最有力手段。在开始,戏剧的经验是中国人拍电影时最主要的借鉴对象。上世纪20年代候曜就说过电影的基本材料包括“危机”“冲突”和“障碍”。这实际上就是从戏剧剧作出发来认识电影要素的构成。以后文学的影响不断地扩大着,可是真正为中国的电影工作者所接受的主要是那些带有较明显的戏剧性因素的文学样式及其经验。几十年来.在好莱坞电影经验的影响、把电影作为政治工具的需要以及电影工业和科技发展水平的牵制等等诸多因素的推动下,这种倾向不断得到强化。当然,企图对这种戏剧化的傻事有所突破的尝试并不是没有出现过,中国电影历史上的许多优秀的传世之作大都可以被看做是这类尝试的结果。但是,这些往往是出自于一些初出茅庐的新人,多少带有某种创新实验的色彩。随着这些艺术家们对电影介入的加深。其中大多数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了初衷.在创作中增加了更多的戏剧性因素。这种现象,我们在中国许多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电影艺术家身上都可以明显地看到。早年曾以创造富有美术价值的优美银幕形象作为自己的基本艺术追求而被人们称作“唯美派”电影家的史东山,后来自觉地在创作中简化内心表现、放慢表演速度、努力使剧情情节简单而叙述周详,使其后期作品成为中国主流电影的典型代表。夏衍早年曾创作了带有浓厚生活流色彩的《春蚕》,朋友们批评他的改变缺乏戏剧性,但他不为所动,还主张詹姆斯·乔伊斯式的意识流素材是最适合电影叙事的材料。但到50年代,他却在融合了从李渔到好莱坞的各类经验,建立起了一整套带有明显戏剧性色彩的剧作理论体系。《祝福》中贺老立的故事和《林家铺子》最后的街头惨剧也多少反映出了他后期的电影叙事观。曾为奠定“第五代”鲜明的造型风格立下汗马功劳的张艺谋,又是同代人中最早重新尝试寻回经典叙事的一个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当中的原因当然是十分复杂的。但中国电影的创作环境的压力和对电影功能表现的需要所产生的影响无疑都起着很大的作用。当一种电影观念被普遍接受并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而且培养了一代代创作者、观众和电影评论家们之后,要想动摇它就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了。中国人的这种以戏剧性叙事为核心的电影本体论就是在几十年的发展道路中,经过几代艺术家创作实践的不断改造和丰富,逐渐形成了一个包容性极强的超稳定结构。它随着人们对电影艺术规律掌握的进步,不断地调整着自己,表现出了极顽强的生命力。
叙事和造型能力的不平衡
严重影响艺术发展的步伐
作为一种商业性大众媒介,电影需要有动人的故事和曲折的情节,这是艺术规律的要求,也是市场和观众的选择。这是无法否认的现实。新时期初期的不少探索者们,尤其是初出茅庐的“第五代”都曾企图尝试不再以戏剧性叙事为核心来结构影片,而以富于表现力的视听形象所传达的情绪或情感冲击力去震撼观众。尽管这样的确产生了相当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优秀影片,但它们毕竟与电影市场的需要和观众的欣赏习惯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在80年代后期电视兴起和商业大潮袭来的时候,这些所谓“探索电影”显得那样的不堪一击。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20年代后期一切武侠神怪片浪潮兴起时“长城”“神州”等所谓“新派”电影的命运。而且取代它们占领电影市场的影片也是那样的相似。这历史的重演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的,除了经济、社会和民众心态等复杂原因之外,电影艺术规律与观众欣赏要求之间的微妙关系也是每一个电影艺术家都无法回避的。面对着广大的电影市场和观众的欣赏需求,中国电影选择这条戏剧化的道路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然
而,这种方法一旦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就自然会极大地影响到人们对电影艺术规律的探寻。
当然,情节和戏剧性是电影的基本表达手段之一。这也是符合电影艺术规律的,至少在大多数常规电影中的确是如此。但问题在于它在整个电影观念体系中被赋予的位置。在这一点上.“影戏”与好莱坞电影也是有所不同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否一定要以戏剧式情节结构为电影的基本叙事形式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真正决定“影戏”的创作风貌的是“本末观”。近百年来,中国电影艺术家们广泛地吸收外国电影和中国传统叙事艺术的丰富经验.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影片。然而,从整体上中国电影表现出的叙事和造型能力的不平衡.无疑是严重影响中国电影艺术发展步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进入90年代之后,大陆电影市场受到港台电影的激烈冲击,几乎到了无法招架的地步。如何看待它们的成功,有不少经验可以引起我们的深思。除了极具号召力的大明星和有效的商业推销手段等外部因素,其创作思路方面与我们影片的差异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尤其是创造一种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视觉奇观和这种奇观与叙事进展的关系的处理方面,不少成功的港台影片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武侠片受到广泛的欢迎,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视听奇观的营造。给奇观以位置,就必须使叙事做出相应的调整。武打、赌博等在这些影片中,与好莱坞电影中的动作或奇观性段落相似,它们既是情节发展的有机部分。其本身又具有独特观赏性。这对叙事的整体结构和节奏掌握、情节起伏和分支的设置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叙事上的相对停顿甚至节外生枝都有可能由于奇观的出现而成为影片中极具魅力的精彩段落,这实际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我们视为极重要的叙事的严谨性。但由于奇观性段落的惊心动魄。使观众无暇注意情节存在跳跃,甚至会对某些情节或人物逻辑上不甚合理之处视而不见。这种现象我们在不少好莱坞电影中也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处理不应被理解为某种取巧的障眼法,它在更大的意义上体现的是好莱坞银幕剧作的基本原则——用画面讲故事。当然,当代港台电影同样从中国电影传统中吸收了大量有益的经验。但其视觉段落在整个作品中的位置和意义实际上与传统的中国电影叙事相比都已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在分析许多成功的商业片时,都会发现其叙事中实际存在着菜种漏洞,但观众却并不计较。这恐怕不能只看做是观众水平的低下.而应看到它们在完成叙事的同时还从其他方面满足了观众的期待。不断变换的刺激冲淡了观众对情节细节的关注,这当中似乎也反映着电影媒介的某种特殊规律。反观中国以往的大部分主流电影,虽然并不排斥视听奇观性的段落或场面,但其与叙事之间的联系和影片整体结构中的位置都有所不同。
中国电影中长期存在着一种现象,即往往以推动情节进展为首要任务的叙事性段落或场面与主要以视昕形象营造情绪或气氛的抒情性段落各自在形态和功能上都呈现出相当的独立性。这至少可以追溯到左翼电影运动刚刚兴起的30年代。从默片中春蚕结茧的优美视觉段落,到初期有声片中《大路歌》《毕业歌》《天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电影歌曲;从40年代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到“十七年”的“十面埋伏”“十八相送”“徐策跑城”等等的古为今用;直到80年代的“板车之歌”和圆明园断壁残垣前的感慨,甚至更新一代的“腰鼓阵”和“颠轿”等等。它们是那样优美动人。但在许多情况下,抒情和叙事是相对独立的。在抒情的时候,叙事往往出现停顿。近年某些商业片中的一些动作性场面也是如此。由于其与叙事进程的相对游离,不仅破坏了影片的节奏掌握.还容易使人产生在展览其中的暴力等刺激性内容的感觉。即使这些段落是在抒发一些健康优美的情感情绪,也容易使人感到冗长拖沓、难以人戏,影响观众的认同。在相当一批影片里.这些非叙事性段落还不是或不仅是抒情.而更多的是对某种意识形态观众的突出和强化。这样造成的与叙事进程的游离往往更显眼,也更令人出戏。这恐怕是中国电影如此重视叙事.却又常常使人感到叙事不够流畅的原因之一吧。
戏剧式电影的主流样式显示着
自身历久不衰的生命力
在中国电影的历史发展中。戏剧式电影作为主流样式在创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因此,人们对电影的艺术语言的认识也离不开对这一主导样式的创作探索。这涉及电影的叙事表达与时空表达的关系.演员的表演在时空体系中的位置、镜语体系的构成以及对电影真实观的理解等诸多方面。当这种认识与特定时代对电影的意识形态表达要求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往往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从而推动其向特定的方向发展。本文不拟对此展开论述,但中国电影中的许多现象都是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的。例如,就像在叙事层面里随阶级斗争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和对“无冲突论”的批判越来越强化着尖锐的外部戏剧冲突在中国电影叙事中的地位一样,电影中的“样板戏经验”里的许多创作成规也不仅仅是江青一个人的一时心血来潮.它同样是从人们对艺术规律的一种特定的理解中衍生和发展而来的。由于以演员表演完成主要叙事任务的段落场面作为中国传统电影里影片意义表达的核心部分.使得演员们在场景之中的相对关系成了电影时空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否与中国电影中常见的那种以全景为主,多以过肩镜头组成人物交流的镜头段落的境语方式有关呢。“两结合”的艺术方法与对电影真实观的理解有没有联系呢?徐鹏飞围着正襟危坐的江姐小丑般跳来跳去地进行审问的场面调度方式中.是否也隐含着意识形态和艺术技巧间的某种呼应与和谐呢?《乌鸦与麻雀》和《春苗》两片结尾处以楼梯为背景的高潮戏在艺术语言的运用和意识形态含义的表达上是否有些相通之处呢?《红旗谱》里朱老巩护钟的场面与“文革”电影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塔式构图”有没有内在联系呢?“敌远我近、敌俯我仰、敌暗我明、敌冷我暖”等一套公式是不是对光线、影调、构图等视觉因素的戏剧性应用的一种延伸呢?“文革”电影的荒谬公式首先是那个荒谬时代畸形的政治生活的产物。然而新时期的电影新潮之所以从反对戏剧化和宣传纪实美学开始其全面的艺术的思想革新.的确与人们深深感受到某些戏剧化的表现手段与前一个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切实存在的深刻联系是分不开的。
当然。艺术语言并不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什么直接的对应关系。但是当一种电影观建立在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目的为出发点的基础上来理解和认识媒介时.对艺术规律的把握就必然会受到其功能需求的制约。我们说“影戏”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长期立于中国电影的主导地位.与前50年民族危机、社会动荡.后30年政治风波叠起的社会环境有着深刻的联系:也与中国电影市场所面临的现实需要相联系。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新潮.企图冲破戏剧化作为开拓电影新路的突破口,试图以“电影本体论”代替“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论、以一种“影像”的美学代替“影戏”的美学。它们不仅在创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收获.也大大深化了对电影媒介本身的认识以及丰富着我国电影的艺术表现能力。然而中国电影赖以生存的土壤——市场、观众、社会需求并不是能够很快改变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发生急剧变化之后.这种艺术探索与市场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需求之间的差距更越来越明显的表露出来。在这种形势下,“影戏”主流电影的生命力再次显示出来。“影戏”的历久不衰也反映出它符合中国社会与被它近百年培养起的中国观众和电影市场的需求的一面。因此,在中国电影迫切需要寻回戏剧性表现经验的时候,我们就更需要对“影戏”传统的这种戏剧化倾向进行冷静的反思。
——以1907—1921年《东方杂志》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