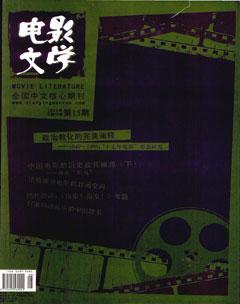“文革”前十七年文学状况
陈纯尘
[摘要]“文革”前十七年,随着中国文艺服务于政治的趋向日益明显,作家创作的主体力量,作家的地域特征、文化素养以及文学创作的题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试图阐述上述变化,以勾勒出“文革”前十七年文学状况。
[关键词]“文革”;十七年;文学状况
20世纪40年代末期,中国现代作家群发生了大规模的位置更替转移的情况,这是左翼文学力量对作家、文学派别进行类型划分,以确立“文艺新方向”的结果。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些重要作家迅速“边缘化”,一部分作家文学写作的“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比如沈从文、钱钟书、朱光潜、废名、李健吾、萧乾等;有的作家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观念、生活体验、艺术方法与新的文学规范的距离和冲突,或放弃继续写作的努力,或呼应“时代”的感召,以适应、追赶时势,企望跨上新的台阶,如茅盾撰写长篇的计划流产,巴金、老舍曾去朝鲜前线生活,前者的短篇小说《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与后者的长篇《无名高地有了名》都说不上成功,张天翼的儿童文学作品《宝葫芦的秘密》已不是之前的成熟的讽刺艺术,艾芜、沙汀的作品取材仍有延续,风格却难以为继;还有一些作家在50年代的政治、文学批判运动中受到攻击而被拒之文学界之外,如胡风、路翎、丁玲、萧军、傅雷等。
延续延安文学传统的作家,在这一时期成为创作的主要力量,居于中心位置。总体上看,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包括进人解放区和在解放区成长的两部分)和20世纪40~50年代之交开始写作的青年作家,是这一时期作家的主要构成,如赵树理、周立波、刘白羽、杨朔、柳青、欧阳山、杨沫、杜鹏程、吴强、梁斌、峻青、冯德英、李准、王汶石等,但并非这两部分的所有成员都能进入这一构成,艾青、丁玲、陈企霞、萧军、蔡其矫、秦兆阳、罗烽等“解放区作家”以及王蒙、刘宾雁、公刘、高晓声、陆文夫等青年作家就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文学方向与文学规范的“大辩论”中,被拒之文坛之外。
十七年文艺界作家的整体更迭可以看出文艺服务于政治.“新文艺方向”的指挥棒起着导向作用。从作家的出身地域、生活经验、作品取材等区域来看,出现了从东南沿海到西北、中原的转移。“五四”及以后的作家多“出身”于江浙、福建(鲁迅、周作人、冰心、叶圣陶、朱自清、郁达夫、茅盾、徐志摩等)和四川、湖南(郭沫若、巴金、丁玲、何其芳、沙汀等),五六十年代“中心作家”的出身以及他们写作前后的主要活动区域,大都集中于山西、陕西、河北、山东等一带,即在40年代被称为晋察冀、陕甘宁、晋冀鲁豫的地区。“地理”上的转移表现了文学观念从比较重视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的倾斜,从较多注意市民、知识分子到重视农民生活表现的变化。
这一时期作家的“文化素养”也与“五四”及以后的现代作家有着不同的侧重。后者中的许多人,经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传统私塾或新式学堂),许多人曾留学欧美日本,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学有较多的了解。不管他们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持何种态度,这种较为深厚的素养,提供了开拓体验的范围和深度以及在艺术上进行创造性综合的可能。五六十年代的“中心作家”则大多数学历不高,在文学写作上的准备普遍不足。他们的生活经验主要集中在农村、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方面,在以后的生活和写作过程中。也会通过不同方式对文化上的缺陷加以弥补,来保证其写作达到一定的水准。但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状况,一旦有限的生活素材与情感体验很快消耗之后,写作的持续发展便成为另一难题。此外,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心作家”中的多数人来说,文学写作与参加左翼革命活动,是同一事情的不同方面。文学被看做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一种独特的方式。他们对于文学自主、独立的观念会保持高度的警觉,不认为可以把政治活动、社会参与与文学写作加以区分。他们普遍认为凭借着“先进的世界观”,作家能够正确地认识、把握客观生活和人的生命过程的“本质”和“规律”,他们所实践的革命和文学,正是体现并阐释着这一发展规律的。他们对于文学的选择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契合,通过了“新文艺方向”这一标尺的筛选而进入了文艺界的“中心”…。
在五六十年代.文学“写什么”成了判定作家性质的政治标尺,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革命文学在题材上必须转移到对“新的世界,新的人物”的表现,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也指出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观察和说明,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像潮水一般涌进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创作中。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知识分子一般地作为整个人民解放事业中各方面的工作干部作为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的脑力劳动者被描写着。知识分子离开人民的斗争。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这样的主题就显得渺小与没有意义了”¨,在这里明确地划分了工农兵与知识分子形象在创作中的主次地位。将“民族的、阶级的斗争”“劳动生产”与“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作了明白的区别。1949年8月至11月,上海《文汇报》开展了“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涉及了小说(以及戏剧等)题材重点的问题。其中何其芳的文章对此进行比较全面稳妥且“带有结论性”表述:“在这个新的时代.在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新方向之下,中国的一般文艺作品必然要逐渐改变为以写工农兵及其干部为主。而且那种企图着重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主要斗争的史诗式的作品也必然要出现代表工农兵及其干部的人物,并以他们为主角或至少以他们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主角.而不可能只以小资产阶级的人物或其他非工农阶级的人物为主角。但是,这也并不等于在全部的文艺创作中就不可以有一些以小资产阶级的人物或其他非工农兵阶级的人物为主角的作品。”从这样拗口的加了许多形容词的表述中,不难发现叙述者对于这个问题紧张审慎的态度,此后围绕着题材所展开的争论,多年中持续不断,尽管作家批评家们对此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遵守一个法则:工农兵生活优于知识分子,非劳动人民生活.性质重大的斗争优于家务事、儿女情长,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写小资产阶级,写日常事务、内心情感,但在具体的创作中作家们都尽量规避此类的题材。我们在十七年的文学创作中就会发现农村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占有绝大的比重,只偶尔出现涉及知识分子内心改造的作品,如《我们夫妇之间》《红豆》《在悬崖上》《美丽》等等,就是这种偶尔出现的作品也如昙花一现,出现没多久就被打压,受到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1950年发表,1951年展开了对萧也牧等创作的批评,指责其作品是“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是“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歪
曲了嘲弄了工农兵”,“迎合了一群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它正被一些人当作旗帜,用来反对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胡风受到批判的主要错误之一,即所谓“五把刀子”理论中的一项就涉及了题材问题,“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值,‘忠于艺术就是否定‘忠于现实,这就使得作家变成了‘唯物论的被动机器,完全依靠题材,劳碌奔波地去找题材,找‘典型,因而,任何‘重要题材也不能成为题材,任何摆在地面上的典型也不能成其为‘典型了。而所谓‘重要题材,又一定是光明的东西,革命胜利了不能有新旧斗争,更不能死人,即使是胜利以前死的人和新旧斗争,革命胜利了不能有落后和黑暗,即使是经过斗争被克服了的落后和黑暗等等。这就使得作家什么也不敢写,写了的当然是通体‘光明的,也就是通体虚伪的东西,取消了尚待克服的落后和‘黑暗也就是取消了正在前进的光明,使作家完全脱离政治脱离人民为止……”,批判者将其此条“罪状”概括为“反对写重要题材,反对创造正面人物”。从胡风的表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文学创作题材的现状以及作家的尴尬,胡风的意见本是遵循文学自身规律所发的肺腑之言,但他犯了当时的大忌——企图修正“工农兵方向”,招致了那场轰轰烈烈、余波荡漾的政治运动。双百时期以及20世纪60年代初的文艺调整出现得《红豆》《小巷深处》《在悬崖上》等等,发表不久也都被视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而遭铲除,他们的作品在“文革”结束后才重新受到肯定,被收入在一个合集里,集子的名字叫做《重放的鲜花》。
20世纪50年代末讨论茹志鹃的小说创作时,其题材问题也是争论的重要方面,批评者认为“作家有责任通过作品反映生活中的矛盾,特别是当前现实中的主要矛盾。”“为什么不大胆追求这些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形象,而刻意雕镌所谓‘小人物呢”。《青春之歌》出版时认为林道静的塑造存在“较为严重的缺点”.“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以至于作者几次删改其稿。如此严苛的创作环境使得作家自觉不自觉地对此类题材退避三舍。不敢越“雷池”半步,导致了十七年文学创作题材单一的格局,此格局在“文革”时达到了极致。
题材的为工农兵服务,忽略人情人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个性的湮灭,群性的高昂,文学作品中塑造的高大全们,梁生宝们是一尊又一尊群性的雕像,是歌颂英雄的赞歌,这在诗歌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十七年的诗歌继续秉承了延安特殊时间空间里歌颂光明的主题,什么是光明,是延安,是革命,是共产党,是代表共产党的毛泽东,诗人首先不是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存在,而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诗歌成为革命事业有力的推动剂,诗人的情感代表了千千万万人民的情感,从1949年9月郭沫若《新华颂》开始,诗歌进入了“千秋万岁颂东风”的时代,不仅只颂一时,也不能只有一个颂者,“这是天山歌唱的时代,我们一起来歌颂”(田间《天山顶上放歌》),其后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柯仲平《我们的快马》、石方禹《和平的最强音》、艾青《国旗》、贺敬之《放声歌唱》、贺敬之《十年颂歌》等等诗作的不断涌现代表着规模浩大、持续长久的颂歌时代到来了。这是一个自我日渐消弭的时代,这是一个英雄日益高涨的年代,一个又一个“我们”从新中国的土地上矗立起来,一个又一个大写的“人”在消失.文学的本体性随着历史的车轮渐行渐远.最后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7—31.
[2]周扬.周扬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513—514.
[3]何其芳.何其芳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83.
[4]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J].人民日报,1951—06.
[5]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J].文艺报.1951—08.
[6]胡风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J].文艺报,1955.(01)(02)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