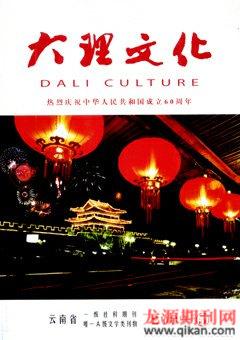味觉乡村
吴安臣
你知道吗,其实每个村子都会传给我们一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决不重复,这种气味流转在你的鼻腔里,甚至驻扎在你的胃里。也许你会在一个深夜归来,但是闻到那种特殊气味时,你的内心立刻就会充盈着一种温暖和激情,那时你也许会想着去拥抱这种来自虚空却又实实在在流转着的味道。
记得我小时在河南生活时,小村没有什么树木,但是唯一能在黑夜里引领我走进村子的是那些散发着甜香味道的刺槐花。每个人或许应该说凡是像我这样希望刺槐的花香包围的人,都会对刺槐产生一种无以名状的感情。记得刺槐花开的时节我和奶奶就会用一些长长的钩子把一嘟噜一嘟噜的刺槐花扭下来,然后把那些尚未开的花蕾摘下来,放在清水里漂洗一番,然后用面拌了放在蒸子上蒸熟,接下来放上点芝麻油和调制好的蒜泥,那种有着花香和油香的感觉似乎至今仍停留在唇齿间,也许那时的胃太好对付了。剩下的那些叶子给羊的话,它们也非常爱吃,因为叶子软而滑,羊也许更就喜欢那种温润的感觉。也可以在滚水里把花馇熟后晒干,这样的话保存的时间就会更长一些,但是味道自然赶不上新鲜的槐花了。有时这种花还可以用来做包子的馅,有一股干香之味。
每到槐花开的季节整个村子弥漫着一种甜香,这种味道会让第一次进入村子的你感到沉醉,甜香在月光皎洁的晚上浮在一片空明里,很多个那样的夜晚我庆幸自己能够在花香里入眠,那是一种笼罩着祥和之气的夜晚,那种静谧里的香味侵入灵魂,占据整个心胸。
我回云南生活后,刺槐很少见了,但是我仍然想念这种树。我总在自觉不自觉地寻找那种甜香,但是那种甜香回荡在中原大地上,我说给别人那是一种可吃可赏的花,没人相信,真的。虽然现在云南人也吃花,但是和我多年前在河南的那种吃法可谓大相径庭了,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胃要求特别高,佐料不齐的话也很难引人食欲的,善于美食的人们不好对付了。倒是有玫瑰不断地被晒干了拿来卖,但是玫瑰的价钱不菲,一般的人吃不起,不像槐花,想吃的话没人管你喜欢吃多少。那种味道把整个的小村笼罩在一片美好里,谁也夺不去。而我走过很多地方,就没有见过玫瑰能把整个村子笼罩起来的,也许那种味道太过华美,只适合在情人节或者一个个特殊时刻用来表达某种含义,一种贵族化的花始终无法走近乡村的贫瘠的土地,我常常如是想。
回到云南以后我对乡村传达出来的气息感受则更为深刻,真的,每个乡村的气息都是自我的。拿我们村来说吧,如果你是夜晚进去的,你会在夏天的某个晚上感受到村子也是悬浮在一种香气里的。记得那时的夜晚没有电视可看,但是可以目睹花在夜里开放,目睹那种开放的感觉如读一首诗一样的美丽,现在我想很少有人想静静地看一朵花开了,看一朵花开需要时间,需要心境。当时家里栽有一棵夜来香(不是平时人们说的夜香树),修长的嫩绿的杆,顶上托着如瓷似玉的花蕾,貌像水仙,但是身材更为修长,比水仙的香味更持久,更悠远。
在我年幼的感觉中,水仙的高洁赶不上夜来香。你想啊,一朵花不选择在白天开放,却独放在夜里,把幽香给那些心境平和的人们,不是具备了隐者之质吗?可以说她有婉约的丰姿,同时有一种清洁的高傲。也许那时的味觉更为迟钝吧,于是我对于这种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进入村子的任何一部分,我都能感觉到这种香味在追随着我的鼻子;也许花也有一种愿望,她也希望自己能在这片土地上永驻。但是花都是要凋零的,夜来香在白天到来时就凋谢了,但是那种香味却种植在记忆里,以至于我对于这种香味的回忆保持得十分恒久。其实我对于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的,但是夜来香却是个例外。
直到今天我还在寻找那种感觉,但是生活的喧嚣与浮躁让我越来越远离这种朴素的香味,我走在村子里,而今能常见到的是些兰花。据说兰花能卖好价钱,某些为官者也爱种些花草。那些生长在幽谷里的兰花,本来没有世俗气,没有一点烟火味,但是而今却有越来越多的铜臭附之其上。为一种花悲哀的同时我也发现味觉的乡土中,我寻找不到那种熟悉的气味了,不知是我脚下的乡土在麻木,还是人们的灵魂在麻木。总之乡村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留给花的位置越来越少了,真的。
我十二分地盼望再回河南吃上一顿拌有香油的槐花饭,把那份甜香裹进肚腹,把那种香味携着行走,在这个味觉失灵了的世界上,让我失灵的味觉恢复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