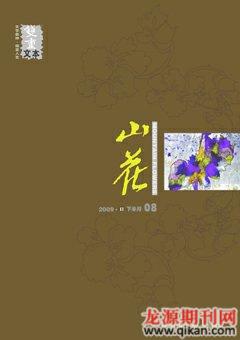情爱沉落的逻辑
马克思虽然关注妇女权益问题,但是“马克思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只是是过渡性的”,更多的是以社会学、经济学的方式提问并且加以处理,而未及伦理学的证明与批判。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为数不少的女权主义者看来,恩格斯的《起源》才是尝试理解和解释妇女从属地位的一本开创性著作,“代表正统马克思主义对‘妇女问题的立场。”
作为本文问题意识的切入点,“新时期”情爱题材创作的理论支撑即是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的理解,尤其是其关于“家庭”的论说。
突破情爱叙事禁忌,当首推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这一文本所具有的思想价值,正是提出了:“在革命者的生活中,爱情究竟有没有它的位置?应当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一追问,实际上暗含着对于阶级论意识形态的朦胧质疑,并无意识地开启了挑战全权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致思可能。
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也极具个案分析价值。小说中的母亲讲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爱情与贫穷无缘。
新时期从政治伦理的批判(主要是基于道德义愤的控诉),转向了情爱伦理的追问(欲使爱理念细腻化、丰满化)。其间引起最大争议的是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
笔者以为,这篇小说所要申张的,是具有思辨意味的、而且带有激进人道主义色彩,以抨击中国传统封建伦理的“爱的哲学”。虽然张洁对此并非自觉。
在作为陪衬性人物的珊珊看来:“虽说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可在这点上,倒也不妨象几千年来人们所做过的那样,把婚姻当成一种传宗接代的工具,一种交换,买卖,而婚姻和爱情也可以是分离着的。既然许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为什么我就偏偏不可以照这样过下去呢?”照此逻辑,就不会像作品所竭力张扬的母亲一样,成为“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
“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重温经典,居然有如此显豁的声言,在当时确乎振聋发聩。
在一个视离婚为离经叛道的时代,面对无爱的婚姻,主人公“尽管没有什么人间的法律和道义把他们拴在一起,尽管他们连一次手都没有握过,他们却完完全全地占有着对方。”叙事者珊珊因此发出这样的疑问:“到了共产主义,还会不会发生这种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事情呢?”
《北极光》(笔者以为与《爱,是不能忘记的》具有互文性)中的陆芩芩,离开了“家庭、工资、长相、人品……”各方面“条件”都好的的傅云祥。当然,走向自我中心的费渊,也自然不是芩芩要寻找的人,她遇到了有理想肯实干,与她爱好相似的曾储。
不妨说,爱理念的匮乏,本然就是汉语文化的致命伤。但这一问题意识的积累,尚需时日。
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 (与《爱情的位置》具有互文关系,即“孟小羽结婚以后怎样?”) ,塑造了一对逆境奋斗,并且自由恋爱结合的青年男女。通过男女主人公交替的内心独白,道出的是爱情与事业的“矛盾”。
不甘于做家庭主妇的“她”,有着这样的困惑 ——“两个人在家庭中的位置,象大自然中一物降一物的生态平衡,也有一种一开始就自然形成的状态。那时候,听一些女人夸耀,在家里都是她的丈夫做饭、洗衣服,我一点不羡慕,我不希望我的丈夫比我弱,捧着我,没有事业心。……为了给他调来北京、开辟事业上的道路创造条件,我放弃了去年最后一次报考普通大学的机会。”
情爱叙事,至此已暗示着女性主义的关注所在。
“他”和“她”终于调到一个城市。开始为事业奔波的“他”想:“当初那样地爱她,想她,究竟为什么呢?他们的结合,象是拼凑了一个两头怪蛇,身子捆在一处的两幅头脑。每一个都拼命地要爬向自己想去的地方,谁也不肯为对方牺牲自己的意志。她也许真能干出点什么,可做一个老婆,却是太糟了!”
两人有爱情有追求,两人也没有对错之分。“也许,恋爱的时候,双方都本能地急急忙忙地表达自己,生怕错过。而捆在一起了,自己或对方,以为在精神上互相依存了,反而使误认为一步可以走向任何默契。交谈的太少了!”
由此发现,关于情爱的奥秘已然被简化为有关“社会分工”所必然导致的人伦异化。
然而问题仍然在于,人们如何面对《起源》所表述的家庭-情爱论呢?换言之,恩格斯的言说,能否作为爱情永恒性的证明,能否确证家庭的伦理价值呢?
在“爱情至上”开始被人们宽容以至于认可的时代,“第三者”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东方女性》应运而生。
林清芬“不是封建时代的小脚女人,是个知识妇女”,面对丈夫出轨,条件反射般想到的就是离婚。“那根一米多长的枣木杖,是我外祖母的,外祖母活着时用它为外祖父擀面条儿,后来传给了我母亲,母亲活着时又用它为父亲擀面条儿,后来又轮到我了。我,现代的知识妇女,大学毕业生,妇产科主任,仍然在家里系上围裙给丈夫擀面条儿!我真象封建社会旧式妇女那样,是一堆软面团儿么?不是,绝对不是!”可离婚的社会影响,会断送“上进的孩子”未来的前途!
两位母亲的现身说法,让爱情至上的余小朵明白了——“爱情不只是两个人的感情扭结,或单纯是一种生理现象,而是感情、理智、生理要求和社会责任感的综合体。”。
……
统观这些小说,显见此类文本无不通过对比的修辞,来表达“社会主义爱情观”的语法。
这些作品虽然没有(似乎也绝无可能)正面给出社会主义情爱观的标准模式,却通过什么样的婚恋不是社会主义的婚恋,大体勾勒出社会主义婚恋的主要内容是男女双方具有高尚的理想、革命人生观,劳动、工作积极,志趣相投。当然,体魄、性格、仪表也是重要内容。
迄今为止,由于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或意识形态的滞后性使然,中国大陆学界情爱-家庭论仍以恩格斯的释读为据。这种教科书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认定“妻子”即是“工人”。恩格斯确信:“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恩格斯就此所给出的解决方案,即是这一著名的论断:“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
合乎逻辑的推论便是,假如妻子和丈夫同样具有了“工人”这一身份,假如二者同样进入了与“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相对应的“公共领域”,那么,夫妇双方便能够携手并肩地反对资本主义,丈夫自然而然地不再具有“资产者”的身份及其权力地位,以使妻子成为“异化劳动者”;妻子也顺理成章地以平等的身份与之相处,从而将公共事务管理的诸多要素纳入家庭,并且与丈夫分享权力。
质言之,千百年来由传统、习俗、文化所规定的“夫妇”,此时因其所形成的关系的意识形态属性而被命名为“同志”。
恩格斯的情爱-家庭论有一个逻辑假设:婚姻关系与市场关系同构同质。这一假设的思想底色,其实就是性别差异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无足轻重。问题正是在这里。“性别差异”并不纯然是一个自然选择的生物学问题,比一般经济学所讨论的“社会分工”有更为深远也更为深刻的人文主题:“女性”是被文化-社会共谋而成的一个陷阱(这正是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的主题)。
在此必须明确的是,家务劳动作为一项不证自明的事实(free labor),既是有别于异化劳动的自由劳动,也同样是无报偿劳动。
但是,这种“无报偿劳动”,由于“不公平”所导致的漠视,使得女性的成就感匮乏,“母亲”变成了“女性工作者”。因而,教科书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许有一个思维的死角:以一种资本分析的思想路径把“妻子”认定为是一种(无偿的)“工人”,对理解妻子的依附性以及将“女权”凸显出其政治哲学的意味,少有助益。
通过前述的文学现象的描述及其反思,归结至此,便不能不追问对《起源》或为意识形态化的解读、或为鄞书燕说的误读——其伦理后果会是怎样了。当《起源》以忽略了个体心性的宏大叙事这一写作姿态处理“情爱-家庭”论题,就必不可免地落入了习见的男权话语窠臼,也导致了后世对这一文本诠释的唯我论。一言以蔽之,诠释者将诠释对象诠释为自己。
因而,不难想象,“张洁们”苦心孤诣的理想主义追求,一旦强化为标语口号,或许只会现实化为——放逐情爱而追逐性爱:
“难道两个将要被撮合的青年人没有权利自由地支配他们自己、他们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器官吗?”“难道相爱者的这种权利不是高于父母、亲属以及其他传统的婚姻中介人和媒妁的权利吗?既然自由的、个人审定的权利已经无礼地侵入教会和宗教的领域,它怎么能在老一代支配下一代的身体、精神、财产、幸福和不幸这种无法容忍的要求面前停步呢?”
“情爱-家庭”的伦理价值,必须有一个信仰支撑。这意味着全称性的“爱理念”的确立,意味着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结构源自于感恩-自由,而这正是千百年来文学文本对于“母爱”的歌颂。母亲们对于日常生活自得其乐的热爱——因为自由,所以感恩;因为源自于家居生活的满足所领有的感恩,所以有不辞辛劳地引领全部家庭成员享受自由。
笔者的忧虑正在于此:由情爱而性爱的沉落,事实上将家庭的伦理价值一笔抹杀,也同时解构了其背后的信仰支撑。“张洁们”已然为”卫慧们”准备了理论前提,泼洗澡水的同时也丢弃了孩子。
参考文献:
[1]凯瑟琳·A·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佩吉?麦克拉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
[2]这里的“新时期”终结于1980年代末期.参谢冕.新时期文学的转型——关于“后新时期文学”[C].文学自由谈,1992.4.
[3]冯骥才.一个时代结束了[C].文学自由谈,1993.3.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曾镇南.爱的美感为什么幻灭[N].光明日报,1980.7.
[6]曾镇南.恩格斯与某些小说中的爱情理想主义[N].光明日报,1982.4.
[7]爱情、婚姻观念和当前文艺创作.新时期小说争鸣选[C].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7.
[8]怡琴.从〈北极光〉、〈方舟〉谈婚姻道德[N].解放日报,1982.6.27.
[9]爱情的位置[J].新时期小说争鸣选[C].十月,1978.1.
[10]张洁.转引自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3.
[11]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J].北京文艺,1979.11.
[12]在同一地平线上[J].收获,1981.6.
[13]公开的“内参”[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
[14]东方女性.新时期小说争鸣选[C].
作者简介;
郑丽丽(1975—),女,山东沂源人,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