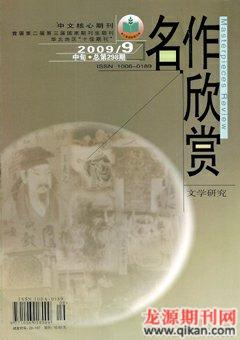人生边缘的行与思
罗 维
关键词:匪盗叙事 江湖人 原始生命力 抗争意识
摘 要:艾芜的《南行记》中刻画了一群生活在山峡深林中的江湖人,他们多从事非法或劫掠偷抢的勾当,这样的生存方式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凋敝、政治动荡的民国乡村十分普遍。然而他们并不是坏人,他们的人性人情甚至令具有道德优越感的叙述人——流浪知识者“我”也为之感动,这就使作者的情感和审美判断总是处于一种悖论的状态,从而造成了小说的叙事张力。《南行记》中所肯定的主要是个体生存的坚韧生命力量,这样狂暴而旺盛的生命力往往会逸出道德的约束和拘制,显示出一种自然状态。其生命的原力以及自由的形式与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互为和谐,时而呈现出一种与自然的狂暴阴郁相类似的野性和兽性。
一
现代文学史上的精品《南行记》的作者艾芜是四川新繁人,他天性浪漫,具有“不安分”的性格气质。据他交代,“读小学时,他就看过侠义小说如《七侠五义》《小五义》《七剑十三侠》等。这些侠义小说强化了他‘不安分的性格气质。它们与泼辣而具有‘叛逆品格的巴蜀文化一起,构成了艾芜在《南行记》中趋近和认同墨家、道家等传统文化中的非正统文化的潜在动因”①。青年时期他漂泊于中国西南边境和缅甸,在漂泊生涯中为了生计做过伙计、校对、编辑,历经磨难,饱尝世事辛酸。1933年他据此经历写了著名的自传体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其中反响最大的是1933年冬写的有关于山贼的小说《山峡中》。
《南行记》确实如一股扑面而来的清新明朗的风,让读者随文字去向往那个和庸常的单调生活不一样的忧郁奇丽的化外世界。即便今天,已经远离那个令人悲悯悒郁的苦难时代,读起来依然能够打动读者的心灵。那么它的魅力何在呢?
第一,它的主题和漂泊、流浪、游有关系。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化是以农耕文化所特有的对土地的眷恋为主的,虽然在传统文学中有很多关于宦游、离别的诗歌,抒情的主体却并非不系之舟,心总是牵挂在故园故土之上。但《南行记》里有着典型的五四式的与家庭的彻底割裂,主人公是个流浪知识人,一个人去闯世界,他的情感记忆里从来没有家的出现。而他笔下的人物全是社会中最特别最卑贱的,连种田耕地都没有份的流浪江湖人。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被不公平的世界给毁了,就是一个遥远的不可及的梦想。但他们在这个世界顽强地生存着,大多数对生活的态度是乐观的。他们从事强盗、偷马贼、私烟贩子、赶马人、轿夫、窃贼等劫掠偷抢的勾当,这样的生存方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凋敝、政治动荡的民国乡村十分普遍,“土匪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其中最常见的决定因素就是窘困的现实使任何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都变得行不通了。换句话说,贫穷永远是持久不断的土匪现象的潜在因素,饥饿则为为非作歹提供了有力的藉词”②。然而他们并不是坏人,他们的人性人情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像金子一样闪光,甚至令具有道德优越感的叙述人——流浪知识者“我”也为之感动。这就使作者的情感和审美判断总是处于一种悖论的状态,造成了小说的叙事张力。
第二,是小说集里展现的川滇之间的森林山岭中动人的原始风情。在现代文学中,很少有作家用这样流浪汉似的视角叙述一个城市与乡村之外的野蛮自然的世界。这个世界有芳香的鸦片、有白色的瘴气,有密实得不见阳光的林子,有崇山峻岭之中简陋而又孤独的客栈,有野猫子那样刚健而又野性的活泼女子。那种新鲜纯净而又朴实真切的文笔和所展现的这个化外世界真是天作之合。同时自然环境与自然的人性融合在一起,让人觉得这些江湖人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他们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其生命的原力以及自由的形式与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互为和谐。在《山峡中》中我们都会对那江水峡谷的险恶莽野不能忘怀,那可以作为山贼们的存在状态的一种喻写。“桥下凶恶的江水,在黑暗中奔腾着,咆哮着,发怒地冲打崖石,激起吓人的巨响”。当小黑牛被同伴扔下江中时,为了生存而不得已丢弃伤病的同伴这种残忍的兽行使我内心感到惊怖。“我轻轻地抬起头,朝破壁缝中望去,外面一片清朗的月色,已把山峰的姿影、崖石的面部和林木的参差,或浓或淡地画出来,更显着峡壁的阴森和凄郁,比黄昏时候看起来还要怕人些”。可是人性毕竟是渴望美好的。在小说中峡谷也有温暖而充满朝阳的时刻。“峰尖浸着粉红的朝阳。山半腰,抹着一两条淡淡的白雾。崖头苍翠的树丛,如同洗后一样鲜绿。峡里面,到处都流溢着清新的晨光。江水仍旧发着吼声,但没有夜来那样的怕人。”
第三,是作者特殊的叙述方式。“我”是这个小说集的叙述人,小说里的情节都是在“我”的游历生涯和“我”的所见所闻所想中展开,也就是说故事里充满了“我”的一种价值判断,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我”没有丝毫优越于他们的地方,但由于身份上的优越、由于“我”读了书,“我”不仅在自己和他们之间划了一条很清晰的分界线,并且在每一次对主人公们的评价中体现自己的道德优越感。比如,对于他们进行合法与不合法的质问,进行有关良心的探询,还有不时生发出来的高于这些底层人们的道德同情。这种从上而下的审视视角消解了不少主题的深度。当然在小说中,这个“我”的从书本里带来的价值观也遭到了同伴们的嘲笑和反驳,更重要的是连“我”自己也意识到面对不公平的世界,面对生存的困境,道德似乎不能作为准则来说明问题。
第四,是应该感谢艾芜先生让这样一群无法言说自我的下层流浪人进入文学史的视野。本来他们是不会为人所知的,而在艾芜的笔下他们却能作为生命个体进入历史言说。文本所写的草民之痛、草民之怒、草民之乐令人感动和惊异。比如《松岭上》里面那个年轻时因妻子被奸一怒之下杀了恶霸、杀了自己妻儿的、晚景凄凉的、卖杂货的老头;《七指人》里那个为自己的欲望所苦,自残三根手指的和尚。
二
从《南行记》当中,我们看到艾芜在漂泊的旅途中始终都在以一种启蒙主义的立场思考着社会底层的人们生存方式选择的问题。《南行记》中叙事的张力往往来自于为匪为贼的生存之道所带来的道德层面和生存层面的价值冲突。《月夜》中和我同行在山路上的小伙子吴大林,“我”是带着一种既厌恶反感又同情的心理看待他的。
我的旅伴吴大林,说他所以干了这么一种牵羊拔牛毛的职业,完全由于他从小到大,都过着挨打受骂的生活。起初在鞋匠那里,挨着鞋底板和巴掌,继后又在打铁店吃了拳头和脚腿,终于从裁缝铺子里逃了出来,手臂上带着烙铁烙伤的痕迹。从此在街上变成了流浪人,和扒手偷儿一道打堆,学会了牵羊拔牛毛的技术。生活对他,不再是压迫了,而是逸乐和嬉戏。他对他的同道,极抱好感,碰着无业的人,也能彼此相合,可以称兄道弟,其余的人便都成了他的眼中钉,总想设法使他们受点损害。他的快乐,便是建筑在他们的悔恨和气恼上面的。(《月夜》)
当“我”责备吴大林不该偷好心给他们吃饭的回族山里人家的鸦片时,吴大林大声骂道:“老子倒不管他妈的啥子回人汉人,在老子眼里看来,世间就只有老肥和穷光蛋。是老肥,老子就要拔他一根牛毛。走尽天下,我都要这样干的!”
匪性十足的吴大林,对于富人有着强烈的憎恨。他是一个四处漂泊的流浪汉,他的世界里全然是匪的观念:一方面世界非穷即富,所以富的就要被劫。但贫却未必济,连路上的小摊贩他都去骗偷欺负。吴大林对于自己的处世观没有丝毫负犯罪感,但叙述人“我”这个知识分子却以书本上所学到的道德廉耻代他承担着一分犯罪感,这种不安虽然苍白无力,却表明了知识分子面对江湖世界一种非常矛盾而又无奈的价值判断。“我”总是习惯性地用道德伦理范畴去考量他们生存方式的对错,可是又不得不在严酷的现实中开始理解这种错的和恶的生存选择。而那些底层的人们根本也不以为然叙述人的道德责备。显然在生存的层面,道德是无力的,更是无用的。
甚至在恶与错中,作者进而发现了这些流浪人所具有的金子般闪光的品质,那就是坚韧的生命力,活下去的顽强信念。这是艾芜的匪盗叙事具有的最深的主题意蕴。小说史家杨义对《南行记》有这样的评价:“以这样一种受社会拨弄、又不向社会屈服的顽强生命力去观照滇缅边地和异邦的化外人生,必然发现一个奇特的、令人惊慕又令人悲愤的世界。”③风险和不测没有使艾芜的这些江湖人畏惧止步,他们笑傲江湖,视凶险为常事,视痛苦为快乐。《荒山上》的那个强盗就宣称:“世间人倒有好些人总想古里古怪的过日子,愿意碰见许多料不到的事情,就是突然有人打背后来捏颈子,也比整天打哈欠活下去安逸些。”在他们看来,不幸和痛苦是人生的常态,作为一个人,不应逃避,不应唉声叹气,而是应该勇敢地面对,勇敢地承担,因为在这个江湖世界,“懦弱的人是不配活的”,“害怕吗?要活下去是怕不行的。”(《山峡中》)
“追求存在之为存在的不可动摇、无畏前行的力量,使艾芜的《南行记》中洋溢着一股不惜一切的赌徒式的激情。在与自然和他人搏斗抗争的过程中,每一瞬间的渴望、悲欢都化成了生命存在的趣味和快乐。这种在克服非存在的斗争中对存在‘所是的追求和肯定,是一种力,一种飞扬恣肆、热情动荡的生命力。④”所谓原始生命力是一种深邃的生命动力,它超越于善恶之上,既可以向善,也可以向恶的。原始生命力类似荣格所说的阴影,是一种强大的原形功能,是最好的东西和最坏的东西的发源地,是千百亿年来遗传而来的未经驯服的动物精神,是能够掌握人的命运的一种狂暴的自然力⑤。它是匪性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原始生命力的自然存在,就没有匪性意识的生成。
《南行记》中所肯定的主要是个体生存的坚韧生命力量,这样狂暴而旺盛的生命力往往会逸出道德的约束和拘制,显示出一种自然状态。这种对于自然的回归不是静态的天人合一的图景,而是动态的与自然和谐着,时而呈现出一种与自然的狂暴阴森相类似的野性和兽性。这些历史的边缘性人物们明知道是“在血盆里抓饭吃”(《私烟贩子》),在“刀上过日子”(《山峡中》),但仍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山峡中》当受了伤的小黑牛要被扔下江中的奔流时,面对夜白飞的哀求,魏大爷“发出钢铁一样的高声”:“天底下的人,谁可怜过我们?……小伙子,各个都对我们捏着拳头哪!要是心肠软一点,还活得到今天吗?”野性十足的野猫子则认为“我”不愿加入的态度是由于害怕,热情地建议“你得让爸爸好好地教导一下子!……往后再吃几个人血馒头就好了!”这是一群为了生存,在绝地中与苦难命运抗争的人们,和他们接触越多,了解越深,“我”便也越对他们顽强的生命力充满敬意。
在《我的旅途》一文中,作家表明了自己的终极价值确认:“他们身上禀赋有最好的东西”,“如同一个淘金的人一样,我留着他们性情中的纯金,作为我的财产,使我的精神生活,永远丰饶而又富裕。”在《偷马贼》中为了当偷马贼而被打伤的老三对这个世界发出诅咒:
妈的,这世道简直岩石一样,总是容不下你我干鸡子!……你想,我该怎么样呢?那还消说,只要裂出一条缝,我就要钻进去。
这种顽强的生命展现“使我蓦地感到这个弱小人物的高傲了。我蹲在他的身边,替他擦药,还对他有些同情。现在才觉得,在他身上升腾起了强烈的争生存的欢乐感情,是用不着任何人的怜悯的”。
同时,作者还从反面说明不抗争会是怎样的生存境况。《乌鸦之歌》的主题是围绕受压迫的人该忍受还是反抗的问题展开。小说用乌鸦敢于和吃了自己的小乌鸦的蛇搏斗作为对比,用间接叙述的手法,讲到“我”投宿的年青汉子的表弟发疯的故事。他们家一再受地主欺压,田给强占了去,牛给人家捉了去。表弟的父亲却一味忍让,最后受到勇敢的乌鸦刺激的表弟要拿刀报仇,却被父亲关在屋子里,日子一久就发疯了。“其实,乌鸦倒比我们这些人活得像样些!”听到这样的悲惨故事,和疯子乌鸦样凄厉的叫声,“我”不禁想起:
人类在最古的时候,一定像乌鸦一样,不晓得容忍的;如果一开始就会对仇敌容忍,那人类绝不能活到现在!
三
因此勇于抗争的精神是艾芜匪色想象中对于这些江湖人最为肯定的品质。在作者看来,与自然和他者的抗争、搏斗的过程中最为升华的是那些瞬间的渴望、激情、悲欢都化成了生命存在的趣味和快乐,变成了生命存在的最高的精神享受。大家“四海为家,银子钱,大把大把的,合着朋友使,日子过得比皇帝老哥儿还受用”(《在荒山上》),梁山水泊的乌托邦
情结中,凝结的已经是在现代意识下的艾芜对于江湖生活中自然人性的张扬。
所以在《南行记》的匪盗叙事中,还暗含着作者对于这种生命精神的肯定,对于江湖人生的亲近。多年后,艾芜还充满感情地说道:“如今一提到漂泊,却依然心神向往,觉得那是人生最销魂的事。”⑥显然让作者感到向往的不是苦难人生,而是那种自由而自然的人生形式。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罗维,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①④赵小琪:《艾芜早期小说的文化想象》,《文学评论》 2004.5。
② [美]菲尔·比林斯利:《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③ 杨义:《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478页。
⑤ 商磊:《英儿,爱与恨的两大本能》,《书屋》,2007.9。
⑥ 艾芜:《想到漂泊》,《艾芜文集》第10卷,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