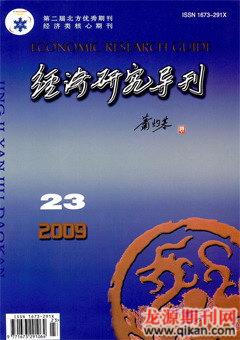关于《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若干认知
陶 铸
摘要:在摩尔的书中,关于结构、剥削、现代化等的论述是极为深刻的,对于比较的、历史的等研究方法的应用是极为精道的。摩尔以世界现代化的政治演进道路作为主轴展开了全书的基本架构,探讨了之所以主流的、“现代性”的几种政治制度得以形成的原因。但是,从方法论上来讲,这里似乎是摩尔的一点失误:在作史学推演的时候,恰恰在史学论述上显得不够;在强调历史重要性的同时,恰恰在很多地方忽视了历史的作用。
关键词:制度惯性;权力结构;暴力革命
中图分类号:G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3-0204-02
作为20世纪社会科学的三大名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以下简称《起源》)是一部思想价值极高的作品,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文化思想界的讨论长盛不衰。通过阅读《起源》,我们可以发现巴林顿·摩尔采用了迥异于他那个时代的叙述逻辑和分析框架。首先,摩尔在宏观的历史框架中探源索隐,区分出三种分布于不同时间序列和因果链条上的现代化道路: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道路,以及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次,摩尔提出了一反常规的结构理论——将现代化进程简单的归结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对比的结果,反将目光转向了地主贵族和农民间复杂的结构关系及其对未来历史产生的独特影响。其三,我们会发现,“暴力”在摩尔那里实现了身份的转变,由保守主义者 “抨击、批判和摒弃”的对象化身为“变革和创造”历史的必要步骤,历史的演进在“暴力”中找到了或失去了彼此衔接的线索。
在摩尔的书中,他关于结构、剥削、现代化等的论述是极为深刻的,对于比较的、历史的等研究方法的应用是极为精道的,对于这些我们后辈学人真的很难实现超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本文不想也无力对摩尔精深的思想进行全面的论述,只是选取几个引发了笔者深入思考的问题进行一点肤浅的解读。
一、制度惯性的力量
确切地说,《起源》一书是一本广阔的宏观史学论著,虽然书中有很多关于制度变迁、法律建构方面的论述,但是从方法论上来讲,这里似乎是摩尔的一点失误:在作史学推演的时候,恰恰在史学论述上显得不够;在强调历史重要性的同时,恰恰在很多地方忽视了历史的作用。
就历史而言,20世纪西方学界兴起的行为主义者普遍认为历史是无意义的。尤其针对当下的政策研究来说,历史研究和规范研究一样,提供的仅是事后的经验和教训,无法深刻地了解现实政治过程的运行情况和策略需求。而且传统政治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相较之以“科学、精确”著称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来说,多是冗长的、繁琐的、描述性的史料堆砌,不仅缺乏对一般性理论的抽象和模型的建构,在理论的精确性和说服力上也逊色不少。因而历史作为一种包袱被丢弃了,并不处于他们的研究视域之中。摩尔则不然。在否定行为主义过于简化的“偏好——行为”解释逻辑和演绎模型之时,对历史作了审慎的处理。在行为主义泛滥之际,他致力于国别史的研究。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革命起源”还是“亚洲迈向现代世界的三条道路”,摩尔皆以历史作为叙述的起点。
摩尔首先认为,一国历史本身制约着该国的现代化的路径和时间选择,因为“各种政治模式的历史前提是大相径庭的”[1]。对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存在诸种路径,有一种错误的“决定论”倾向,这从清末现代化过程中对西方立宪制度的文化误读和发展中国家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失败中可以窥见一斑。在很多时候,我们在肯定异质文化中的某一制度的功效时,往往忽视了该制度得以实现其效能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前提和条件,仅仅抽象地关注制度功效与选择该制度之间的需求性关联而非逻辑上先于此的可能性关联。制度的变迁和移植都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还涉及到制度的再生问题,因为制度安排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开放的生存系统。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摩尔对待历史的态度和青木昌彦所言的“制度起源的意外耦合”[2]说法甚为一致。对于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不是某一因素就能决定的了,而是诸种因素并存、融合、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历史的结果并不总是有效度的,很多时候都会超越人们预期范围。
然而,我们从摩尔的文章中也还能读到,他有一种很强的“历史无效性”的倾向。传统的史学研究普遍认为,历史是理性的、进步的、有效率的。譬如,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推出了“历史是前进的、上升的”结论,基本上都还是一种“长时段、深层次、总体史”研究。有点类似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的前后连贯的纲领,再作进一步的研究。然而,摩尔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历史无效性”,他在整个叙述的过程中,对于法西斯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较之西方民主道路在时间上的滞后性和曲折性充分透露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某一历史事件在时间选择上的延迟导致了那一时点上历史的无效,同时,也隐藏着对后来历史的或正或负的影响。
虽然摩尔的上述观点具有不连贯、不一致的地方是在不同的语境下阐释的,但我们也不难看出,他是在这两种倾向之间摇摆的,这种思想的摇摆有时候对于历史的理解有所助益,但作为历史观,这种摇摆的状态是不敢恭维的。笔者认为,历史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代表着一种文化的积淀,文化的恒久性决定了它的影响力是持久的,这也就是说,一种文化因为长久的存在,自然的就内化了,而是形成了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包括外在的一些规定,更包括在人们的思想、行动等之中体现出来的潜意识中的一种认同,这便是一种制度惯性。
二、权力结构决定论辨析
摩尔在文中提到了一个重要观点:在一个国家中,影响民主进程的重要因素不是经济发展水平,也不是文化因素,而是权力结构的变化。在他看来,经济的发展不能自然而然生成民主,可能走向以对外侵略和对内压迫为特征的法西斯道路。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可以再造文化。这个观点是有些石破天惊的,因为在传统理论中,影响一个国家民主进程的,有主张和经济发展挂钩,有主张文化素质决定的,但是却没有两者都否定的。
关于经济和民主的关系,我想起了另一位政治学大师,李普塞特。李普赛特的治学方法和摩尔相似,也是视野宏大,喜欢做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他的代表作《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是一部以论述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为主旨的政治社会学的经典著作,这本书中,李普赛特着重论述了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书中,李普赛特先提到韦伯和熊彼特民主的定义:民主是一种政治系统中,系统为定期更换政府官员提供合乎宪法的机会,民主是一种选举的程序。那么,这种民主的存在需要一定的社会土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的发展。李普塞特作出了一个理论上的假设:民主关系到经济发展的状况。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李普塞特以欧洲国家和英语系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国家作为对比的参照系展开了论述,最后得出了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并非正相关的结论。而在摩尔的书中的第一部分,他讲到,在英国和美国的早期,经济并不是很发达,但是,他们却建立起了议会民主制,民主制也真正的实现了广大人民的民主,这充分显示了在摩尔看来,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从摩尔的书中,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只有经济上的有效性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树立和巩固政权合法性和正当性,这就应该拓宽民众的政治参与渠道,建立顺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实现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三、暴力革命的反思
摩尔高度评价了暴力革命在西方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英国革命战胜了君主专制制度,使带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大地主腾出手来,在18、19世纪一举消灭了农民阶级。法国革命打破了尚未进入商品经济领域的土地贵族的权力,但在一定阶段上,又反过来开始要求新的强制力量,以约束和控制自己的劳动力,在这层意义上法国革命建立了另一条路线,开创了一个逐渐趋向民主的社会。美国内战消灭了种植园主的力量,这种理论量一度作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兴起,到这时却成为民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2]345-346摩尔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对民主制度建立的重要作用还可以通过德国、日本和印度的反面经验体现出来。在他看来,德国、日本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没有经过革命实现了现代化,但却由此形成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它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远远超出暴力革命的代价;印度没有选择革命道路,也没有形成法西斯主义,但它在现代化道路上却始终步履蹒跚,徘徊不前,这可能是没有经历暴力革命所付出的代价。
1996年以来,摩尔的观点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关于暴力革命这一点是遭到的批评最激烈的。在以现代化为目标归依的模式下,暴力革命在摩尔的论域中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点摩尔的论述也是非常充分的。然而问题也就在这里,无论我们的政治建构,还是学术研究,出发点到底应该是什么。首先,“现代化”作为目标模式就值得反思,更兼现代化是一个内涵极为宽阔的词,太多相反的价值也都可以统合到现代化之中;其次,就算在最狭义的意义上来使用现代化,现代化就是和很多价值冲突的,比如民主,比如自由等等。所以,从根本上说,摩尔犯的一个方法论上的错误,那就是在现代化这个价值之上还有更重要的价值,比如自由、健康、生命等等。所以,他哪怕在特定的意义上相信暴力革命的作用,那也很容易让人们产生误解,进而对他提出尖锐的批评。
一部好的作品,如果只是得到长久的称赞而得不到任何的批评,那么它并不是一部好作品,因为它没有给人们留有产生思想激荡的机会,那么它的影响也很难是持久的、长盛不衰的。幸运的是,摩尔这部《起源》在让人们惊叹的同时,留给了人们许许多多进一步思考的空间,让人们从之中不断地汲取营养。
参考文献:
[1][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