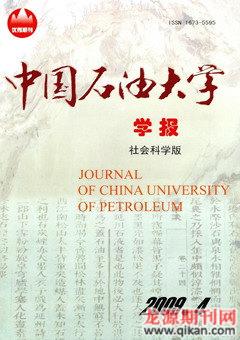有意的高扬与无意的颠覆
王瑜瑜
[摘要]明代剧作家许自昌《水浒记》传奇,是水浒戏的杰出代表之一。作者在改编水浒故事的过程中,一方面以先入为主的姿态有意高扬忠义,通过智劫生辰纲、私放晁天王、坐楼杀息(惜)①、火并王伦、闹江州、反上梁山等小说原有情节塑造宋江、晁盖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又大量铺排儿女风情,充分展开宋江、阎婆息和张三之间的情感纠葛,客观上颠覆了《水浒传》中对女性形象一味贬低的状况,具有了更为复杂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水浒记》;《水浒传》;矛盾;高扬;颠覆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9)04-0082-(05)
《水浒记》传奇,明代许自昌撰。自昌,字玄祐,筑梅花墅,因以为号,别署梅花墅,梅花主人,自号高阳生,长洲(今江苏苏州)人。②水浒故事萌芽于宋,元代已初具规模,至明代许氏创作《水浒记》时,水浒故事流播已十分广泛,这从余氏双峰堂刊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容与堂本《水浒传》的刊行可见一斑。而《大宋宣和遗事》一书较早、较完整地勾勒了《水浒记》的主要情节(包括智劫生辰纲、怒杀阎婆惜),此后,水浒故事在不同的版本中经历了更多的艺术加工,日趋成熟完善,《水浒记》的创作是在水浒小说丰厚积累的基础上展开的。③
一、无处不在的矛盾与先入为主的高扬
在《水浒传》这样一部世代累积成书的通俗小说中,人们会发现无处不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广泛存在于“忠”与“义”二字之中。李贽《〈忠义水浒传〉序》、天海藏《题水浒传叙》用大量篇幅执着于“忠义”之辨,而后来的评点者也往往难以回避,足见此二字对于《水浒传》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忠义”二字就是这部小说的主题,穿插其间的英雄传奇史与忠奸斗争史对“忠义”之间无处不在的矛盾做了最佳诠释。
首先,《水浒传》中宋江等人口口声声强调的“忠”主要指向“忠君”,即维护赵宋统治集团的利益。但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实力派(来源于封建中下层官僚、地主、知识分子的卢俊义、吴用、呼延灼、花荣、秦明、柴进等人)“忠君”的目的并不单纯,他们要赢得赵宋王朝给予个人的高官厚禄(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功业成就)和“忠君报国”的显赫名声,从根本上讲,这源于封建文人修齐治平的思想情结和与此交织的功名欲望。正是这批实力派人物决定着梁山的走向,而真正坚决与朝廷对抗的鲁智深、李逵、武松等人显然不具备掌握梁山核心权力的可能性。因此,笔者以为,与其说《水浒传》反映了农民起义,倒不如说反映了封建统治没落期,利益得不到保障的统治阶级下层“清醒人士”用极端方式试图重新获得权力分配却最终自我灭亡的艰难历程。功利性不可避免地掺杂导致了《水浒传》“忠”本身深含的矛盾:一方面,它要求百姓对赵宋王朝忠心不二,因此宋江无论落草之时还是掌握实权之后都念念不忘“招安”,要做大宋王朝的忠臣顺民,此时的“忠”,发自肺腑,信誓旦旦,是宋江心中正统封建道德观念的外化。但另一方面,这些“忠义之士”在醉酒之后竟然可以大题反诗,没有内心深处的叛逆基因,狂悖叛逆之语恐怕不会轻易出于笔下;接受招安时,他们要打得官军们“怕了”,多捞些招安的资本;他们还可以循私枉法,私放重犯,甚至路劫降香钦差。这些举动绝非大宋忠臣当为,因为它们无一不是在赤裸裸地挑战封建皇权的绝对权威。
其次,笔者认为《水浒传》中的“义”至少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如天海藏所说:“事宜在济民谓之义”,这是一种大义,即非为小集团或帮派利益两肋插刀,而是对百姓负责,即主动承担保护下层受苦受难大众的职责,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对抗更为强大的丑恶势力,乃至整个上层统治。其二,是为小集团利益或帮派利益付出一切,不顾是非,而将兄弟义气、同生共死置于首位,这是一种小义。梁山英雄们的“义”往往就是这两者的纠结与斗争,而他们更多从小义出发,因此常常流于狭隘,走向极端,直至葬送事业,毁灭自身,李逵之死可谓明证。
当水浒英雄们身处“忠”“义”之间,面临坚守与放弃的严肃抉择时,人们便能窥见他们内心激烈的斗争和难以摆脱的彷徨。他们究竟应该选择为民请命、抗争到底的大义,还是选择与赵宋王朝腐朽统治同流合污的愚忠?他们究竟应该选择闹东京、劫法场、杀官屠吏、保全兄弟的“义气”,还是维护朝廷的绝对权威,牺牲聚义之情,手足之义?他们究竟应该选择为济世救民而亡命四方,还是用弱者的血泪换取头上的“顶戴花翎”,以此博得“封妻荫子”?他们究竟应该为了百姓利益与昔日的聚义兄弟分道扬镳,还是与接受招安的兄弟们同生共死?种种抉择,势同水火,条条道路,进退维谷。《水浒传》的出色之处,正是将以宋江为代表的主人公们置于这样的环境中,把他们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斗争,痛苦与徘徊的精神状态,执着与无奈的生命抉择,现实生活中的左右为难展示给千万读者。④这些矛盾纠葛成就了小说独有的艺术魅力,作为世代累积型文学作品,《水浒传》得益于无数作者、读者、文人、百姓、艺人的合力创造和长久的精心锤炼,得益于不同思想观念和艺术技巧的继承、碰撞、交流和融合。
与小说不同,《水浒记》作为文人的独立创作,经过作者对本事的剪裁增饰,在思想主旨和艺术风格方面十分统一,尤其突出地表现为用先入为主的、一元化的忠义观念统摄整部剧作。作者通过精心设计的戏曲结构和绮丽流畅的唱词,对主要人物宋江、晁盖进行正面塑造,大大消除了文本的多义性(不同于小说),将一元的“忠义”观大力高扬并推向极致。同时,作者还或多或少渗入了封建正统的“节烈”观,使这部作品成为作者一厢情愿的寄托。明代剧论家祁彪佳《远山堂曲品》把这部传奇列为“能品”,他认为这部作品“记宋江事,畅所欲言,且得裁剪之法。曲虽多穉弱句,而宾白却甚当行”,可称“场上善曲”[1]。许自昌对水浒故事进行的“裁剪”主要有如下表现。
一方面,作者为突出“乱自上作”的混乱年代中水浒英雄的“忠义”,首先选取了“忠义”的化身——宋江作为剧作的主人公,保留原作私放晁盖、怒杀婆息、江州题反诗等具有高度艺术性的精彩情节。但这并非作者目的,对这些部分对立面的描写(即宋江是如何恪守封建道德的)才是作者用力最深之处。作者依次设置了《论心》、《发难》、《周急》、《慕义》、《约婚》、《效款》、《博执》《党援》、《聚义》各出,从不同角度对以宋江、晁盖为代表的“忠义”之士进行正面赞扬。第二出《论心》中,作者别出心裁设置了宋江与晁盖相会,意气相投,英雄相惜,相逢伊始便开门见山、直抒胸臆、表白一片忠君重义之心:
(宋江)[喜迁莺]晏婴身短只自笑,区区质赋优旃,盖世忠肝,包身义胆,然诺重似丘山,酬死士万金立散,答君恩一剑时悬,且雌伏自功曹,有日名垂鼎铉。
如果说《周急》、《约婚》两出通过具体事例对宋江慷慨好义、扶贫济困正面渲染,那么《发难》、《慕义》、《效款》三出则属侧面烘托,通过刘唐“宋公明扶危济困隐功曹,晁保正疏财将义好”和梁山王伦“及时雨名震皇都,是当今大丈夫”的钦佩之词对宋江等人进行赞扬。在《效款》一出中,作者精心设计了宋江劝降梁山喽啰的情节,他认为这些人“抛离家业,啸聚山林,既犯不赦之条,更为无籍之辈”,应当“弃去山寨,归就耕耘”,作者不但试图说明宋江好“义”,更试图说明宋江即使反上梁山,也自始至终服从封建道德规范,胸怀强烈的招安欲望。
身处顺境之中的宋江如此忠义,那么遭受苦难时的宋江又如何呢?作者通过《博执》、《党援》、《聚义》中宋江的表现再次从正面升华了他始终不改的赤胆忠义心。《博执》一出中,宋江装疯,一吐胸中块垒:
[一盆花]可惜乾坤浩荡,看天翻地覆……牛马冠裳……看此际玉皇下降,鉴别忠良,任吾主张,任吾放旷。
在遭到残酷刑罚磨折,身陷囹圄,依旧渴求自己的“忠良之心”被人体谅,怎不令人动容?
《党援》一出,作者对小说所作的改变更明确地体现了作者先入为主的创作倾向,晁盖“结党梁山,行道替天佐汉,看建帜忠义堂前”的表白与小说中晁盖新夺梁山后仍名“聚义厅”,宋江上山后更名“忠义堂”的事实不完全相符。⑤许自昌在这句唱词中直接使用了“忠义堂”,显然是将晁盖亦定位为既“忠”且“义”的好汉,与一般巨盗叛贼要有所区别。紧接着《党援》中晁盖表明心迹,《聚义》一出结尾,作者通过梁山众好汉之口完成了对忠义之士光辉群像的塑造:“锄强诛暴军威壮,扶危济困恩波旷。恁强梁,能如山寨,水浒有余光,”作者还为他们指明出路:“替天行道旌旗漾,看忠义堂颜高敞,管指日招安达帝乡。”这无疑是作者心目中宋江等人作为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忠义之士”所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和必然、唯一、正确的归宿。这些正面渲染和高扬大大淡化了宋江作为造反者的形象,能够激起读者对宋江忠义之心的由衷钦佩,而这种高扬完全基于作者个人对宋江等人的道德评价,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作者事先的定性似乎给读者一种无可辩驳的合理性。在《水浒记》中,这一强势的话语有效压倒了其他声音,远不同于小说《水浒传》中多种话语的喧哗与嘈杂。
另一方面,同样出于塑造“忠义”形象的目的,作者从梁山英雄好汉的对立面着力,对丑恶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揭露,揭示了政治的极度腐败和社会的极端不合理,千方百计为宋江等人破坏封建统治秩序的行为提供理由,让“忠义之士”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处处碰壁,壮志难酬,蒙羞受屈,痛苦压抑,令读者为他们一掬同情之泪,从而在心理上认可他们反上梁山的行为。与小说比较而言,作者在暴露封建统治黑暗方面更为集中,批判上更为直接、有力。
在第二出《论心》中,宋江之妻一针见血指出当时社会的黑暗本质:“外寇不宁,内乱交作,那些腰金佩玉的,又只管肥家润身,不顾民害,似你这等挺生豪杰,却又婆娑胥吏,困踬簿书。”而晁盖则有更为敏锐的眼光,他认为“奸臣弄主权,墨吏酿民怨”一定会导致“田横倡义咸思变,陈涉冯陵遂揭竿”,并且立下了诛杀酿乱谄佞的雄心。这一段无疑是作者为晁盖等人最终落草梁山埋下伏笔,并且为他们造反的原因作了第一次有力的诠释。围绕生辰纲展开的一系列矛盾冲突是忠奸斗争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大小官吏狼狈为奸,鱼肉百姓,“那权臣忒煞也势甚骄,惯纵着心腹贪饕,那生辰纲载珍和宝,逐件件是民间剥下脂膏,只见那搜刮价把民财耗,又见那输运价把民力扰。”另一方面,这些恶行当然会激起社会动荡,忠义之士的愤怒和反抗在作者看来就势在难免了。忠义之士铤而走险在作者看来是正义的,因为他们反贪官,而没有反对封建皇权。《约婚》一出,洞房花烛前夕,宋江依然念念不忘忧国忧民:“不为一家愁绝,只因万姓心伤,奸佞盈朝,豺狼当道,不思为民为国,但要自利自私……那生辰纲一事,既要差民转运,又要委兵提防……因他一个生辰纲,惊动多少地方,刻剥多少小民,”愤怒之情溢于言表,而“人人思乱,家家动摇”的现实又击碎了宋江“太平景象”的梦境,这些愤怒与失落的终极指向就是采取极端的武力反抗手段,作者预设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允许宋江这样不愿逃避现实的忠义之士有其他选择。
许自昌在剧作中试图以一种强势话语掩盖小说《水浒传》中的嘈杂之声,但从根本上来讲,它无法改变作品主人公自身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这些矛盾由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主人公思想行为的局限决定,只要这些原本充满矛盾的现实、思想和行为没有任何改变,剧作者的努力就一定会大打折扣。具体到《水浒记》,对“忠义”之士先入为主式的高扬,并没能从根本上抹去他们思想和行动中无处不在的矛盾,剧作家褒扬忠义的创作初衷和保留小说主要故事情节的创作方法,在创作动机和创作实践上显然有所抵触,矛盾不可避免。
二、儿女情,英雄气,孰长孰短
众所周知,《水浒传》是血气方刚的梁山好汉的一曲英雄赞歌,整部作品读来令人热血沸腾,英雄气概贯穿于字里行间,而其对儿女之情的描写却少之又少,为数不多的几个女性不是淫妇便是泼妇(如潘金莲、潘巧云等),对女性贬多褒少,这个现象很早就有学者关注,的确值得深思。《水浒记》中,张三(小说中名张文远)有一句话可作为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的起点:“人常说道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宋公明为人到是反这两句话的。”这句话指出宋江“儿女情短,英雄气长”的特点,推而广之,梁山好汉似乎全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禁欲主义者,似乎“红颜祸水”的铁律是专为梁山英雄而设,林冲、宋江、扬雄、武松、卢俊义等都是因为女人才被逼上梁山,所以真正的好汉在宋江、晁盖等人看来应该是不近女色的,反之就像王英“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而像晁盖“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像宋江“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的行为才是好汉所为。这些近似道学家的观点与其说是宋江等人的看法,不如说是《水浒传》的作者落后的女性观在作怪。正因为这样,“英雄气长、儿女情短”的《水浒传》在女性描写上尽管有些滑稽失真,却也正中某些道学家的下怀。许自昌则把一部单纯的英雄传奇演变为一部融汇英雄传奇与儿女风情的剧作,姑且撇开作者创作的主观意愿不论,仅就创作结果而言,笔者以为他在儿女风情部分的处理和创作上,成就远远超过了英雄传奇部分。学者们一般把宋、阎、张三人的感情戏当作败笔⑥,笔者试图从另一方面关注儿女风情戏对于小说的创新意义,以及对整部剧作的积极影响。
要了解这部剧作中儿女风情戏的艺术魅力,不妨试举一例,《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水浒记”条著录:“《借茶》、《刘唐》、《拾巾》、《前诱》、《后诱》、《杀惜》、《活捉》等出不仅流行于昆曲舞台上,亦为京剧及地方戏所移植。”[2]由这条材料可知这些场次的受欢迎程度,与其他渲染忠义的场次比较,显然这些场次的艺术魅力更大、更为持久。日本著名学者青木正儿说:“以是后来行于歌场者……概为关于阎婆息之诸出,阎婆息事与潘金莲事并为《水浒传》中最妖艳之好关目,此记之所以与《义侠记》相并,盛行于歌场中者,亦非偶然也。”[3]265笔者以为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关目妖艳”并非决定性原因,作者将小说改编为“英雄气长,儿女情亦长”作品的艺术技巧和创作实绩至关重要。
在《水浒记》三十二出的篇幅中,集中展示三人情感纠葛者占去十二出,依次为:第三出《邂逅》、第六出《周急》、第十一出《约婚》、第十二出《目成》、第十五出《联姻》、第十八出《渔色》、第二十一出《野合》、第二十二出《闺晤》、第二十三出《感愤》、第二十四出《鼠牙》、第二十五出《分飞》、第三十一出《冥感》。作者何以对感情纠葛描写如此着力?笔者以为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明代中后期社会主情思潮和传奇作品的强烈抒情特征使然。郭英德先生在《独白与对话——明清传奇戏曲的抒情特性》一文中,对传奇作品的抒情特性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他认为戏曲语言“善达性情”,宣泄感情更为直接、酣畅,可以自由变化,适应性很强,更契合个体情感的自由本性,具有表情达意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他认为,明中后期思想领域“心学”和言情思潮兴起,传奇创作中“以情为本”的主体精神和感性色彩更为突出。⑦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综合作用促使许自昌在《水浒记》中大量使用绮丽之语描摹男女私情,花费了大量笔墨。事实也证明他在这方面的努力的确成功塑造出了阎婆息这个复杂多情的人物形象。
第二,儿女风情戏的大量掺入是“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综合作用的结果。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云:“《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4]219具体到《水浒记》的创作,可以说是“以戏曲语言”运“水浒故事”,从这个层面来讲,忠实于小说原著这一点许自昌做得很好。他的难能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因文生事”,在戏曲创作过程中,“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大胆添加了借茶、活捉两个重要关目,结合小说原有故事情节,一气贯通,塑造出了不与小说雷同的阎婆息形象,由小说中性格的单一化、平面化变得复杂、立体,富于韵味。这一创作过程使作者无意之间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自身的价值判断,表现出对阎婆惜的复杂心态,与其对节烈观的渲染形成了一对矛盾,这对矛盾恰是构成颠覆的原因。
《大宋宣和遗事》对宋江、阎婆惜的描写相当简单:“宋江接了金钗,不合把与那娼妓阎婆惜收了;争奈机事不密,被阎婆惜得知来历……宋江……却见故人阎婆惜又与吴伟打暖,更不采着。宋江一见了吴伟两个,正在依偎,便一条忿气,怒发冲冠,将起一柄刀,把阎婆惜、吴伟两个杀了;就在壁上写了四句诗。……诗曰:“杀了阎婆惜,寰中显姓名。要捉凶身者,梁山泺上寻。”[4]36|37
从这段描写中可推知吴伟大概相当于张三的角色,而阎婆惜不过是一个娼妓,与宋江并没有婚姻关系,不过具备了妓女唯利是图、水性杨花的平面特征。而到了《水浒传》中,阎婆惜具备了娼妓、泼妇的双重性格特征,不仅唯利是图、水性杨花,而且蛮横无理、泼辣狠毒、忘恩负义,没有一丝值得同情之处,令人生厌。《水浒记》则花费了大量笔墨对阎婆息形象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在她身上添加了令人怜惜同情的成分,塑造出一个血肉丰满的女性形象。作者对小说中阎婆惜形象的改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阎、张私情起源上,小说中阎婆惜:“一见张三,心里便喜,到有意看上他。”而《水浒记》《邂逅》一出则突出了张三的主动勾引,虽然婆息亦有意,但相对处于被动地位。其二,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阎、张私情的逐步发展,描写了《联姻》一出中宋江新婚之夜对婆息的冷遇,使这次冷遇成为《渔色》一出阎、张私情最终确定的催化剂,客观上肯定了女性正当的感情需求,让读者感受到阎婆息背叛宋江不仅因为自身的水性杨花,更由于宋江“英雄气长,儿女情短,”不能满足她的基本情感需求。此外,在多个涉及阎婆息的场次中,作者详细描写了她作为女性多情善感、婚姻不幸、慨叹青春空逝的悲凉与无奈心境,使读者对她有更多同情,进一步为她私情的产生与存在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性。其三,最为难能可贵之处是作者设计了《冥感》一出,将婆息一片痴情写到极致,不管她所寻找的归属——张三是否可靠,张三是她唯一的感情寄托是不争的事实,婆息这种死去也无法忘情的挚诚足令人们感动。
但是,不可否认,作者根本的道德判断没有丝毫松动,情感上的某种倾斜,并不足以对抗作者基于封建道德观念对女性的看法。作者在塑造阎婆息的同时塑造了宋江之妻孟氏的形象,这是一个许自昌心中完全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女子:讲究三从四德,对丈夫毕恭毕敬,意气相投;是丈夫的贤内助,更可贵的是丈夫娶妾后不但不妒,反而欣慰;与丈夫同甘共苦;丈夫不在时死守贞节,大义凛然。宋江之妻孟氏与阎婆息构成了鲜明对比,前者是封建社会中的“贤妻”,却没有太多的情感追求;后者是不为封建道德所容的“荡妇”,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情之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创作实践的偏离对其坚守封建道德的初衷和创作原则构成了无意的颠覆。“无意”是指这种颠覆并非作者主观意愿使然,而极有可能是创作实践过程中奔腾的情感诉求无意中冲破道德底线的结果,一旦坚固的道德防线建构起来,便不再会出现如此矛盾却又如此人性化的情节。
此外,还应该充分肯定儿女风情戏调剂剧场气氛、丰富思想主题、开拓小说意境方面的功能。首先,儿女风情戏与英雄传奇戏的一柔一刚,相得益彰,改变了单调的演出气氛,细腻入微的情感交流和粗犷豪放的忠奸斗争给人截然相反的两种审美感受,有利于现实演出中让观众产生丰富的审美体验。其次,在“忠义”主题中掺入了情感主题,并且渗透了包括“节烈”观在内的多种观念,使剧作思想更为复杂,可阐释空间更大。再次,剧作明显拓展了小说原有意境,无论是在叙事规模还是细节描写的深刻细腻程度方面,与小说相比各有千秋,在某些场面的描写上营造出了比小说更丰富的意境。至于该剧作的缺陷,前辈学者多有精到的见解:结构上因“描写晁盖等事过多,遂呈分两头而为二家门之观”成为第一大缺陷;曲词“好用骈绮之语,与杀伐之水浒剧不相称,曲词无论矣,即茶店老媪,时述四六骈体之白,又如梁山泊军士叙梁山泊形胜,近三页余之独白,宛如一篇长赋,难免不伦之讥”[3]265是为第二缺陷,曲词过于雅化不但不符合人物身份和性格特征,而且会让听众茫然无所适从,难称场上当行之曲。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水浒传》中无处不在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忠义”观念的复杂性之上,《水浒记》力图通过先入为主的正面高扬对这一状况加以改变,但结果仍无法跳出矛盾的怪圈;《水浒传》有“英雄气长,儿女情短”的突出特征,而《水浒记》则通过创作努力形成了“英雄气长,儿女情亦长”的艺术效果,而且无意中对压抑女性正常诉求的封建道德观念有所颠覆,但是这种颠覆最终只能无奈地回归原点。
[参考文献]
[1]祁彪佳.远山堂曲品[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6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59.
[2]邓绍基,等.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667.
[3]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4.
[4]朱一玄,等.水浒传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注释:
①小说诸版本中均作“阎婆惜”,《水浒记》作“阎婆息”,二者实为一人。
②学界对该剧作者有其他看法,本文采用许自昌为其作者的观点。
③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和李修生《古本戏曲剧目提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二书均著录《水浒记》尚有万历十八年(1890)金陵世德堂刊本,然均未见原书,或非许自昌所撰,兹不录。本文小说以施耐庵、罗贯中撰《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排印容与堂本为底本,戏曲以毛晋《六十种曲》(中华书局,1958年版)排印本为底本。文中凡引用上述两书不再一一注出。
④郭英德《论宋江形象的人格内蕴》(《昌吉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认为《水浒传》中的宋江的身份本不单纯。在经济上是小地主,政治上是刀笔吏,文化上是知书识礼的文人,行为上又是行侠仗义的侠士,集诸种身份为一身。他的绰号也显示了他性格构成的复杂性:“及时雨”说的是仗义疏财,济弱扶贫;“呼群保义”,说的是有号召力和组织能力,能够把天下的英雄豪杰凝聚成一个坚强的集体;“孝义黑三郎”,则说的是他在心底里又想恪守传统的伦理道德,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忠臣孝子。
⑤相关论述可见罗尔纲《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第四章所论。
⑥郭英德主编《中外古典名剧鉴赏辞典》(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认为《水浒记》“由于用过多的场次来描写阎婆息与张三郎通奸的事,结构不免有松散之嫌。”邓绍基等编《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水浒记”条同样认为此剧:“偏重描绘宋江、阎婆惜、张文远之间的纠葛,又过多穿插晁盖等人的情节,致使剧情分呈两头,主线不够突出。”笔者认为这两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些情节的插入有其积极意义。
⑦详见郭英德《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四章相关论述。
[责任编辑:夏畅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