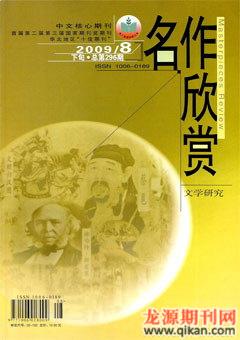有意味的形式
关键词:叙述人 叙述分层 传统叙事
摘 要:在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中,叙事的形式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总与叙事性质结合为一体,最恰当地表现出后者。本文采用叙述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文本细读,揭示小说所运用的叙事策略中的叙述分层的手法。透过叙述分层,莫言完成了对传统叙事方式的叛逆,也使得自己的叙述方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自由境界。
莫言的《红高粱》①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有关当代人生存境遇的寓言,其主题可概括为“一个当代人对平庸、弱化、压抑充满恐惧,渴望摆脱以到达自由的理想境界,却又不知如何摆脱,如何到达,只有借赞美祖先野性不羁的生存状态,发泄郁闷,叛逆现实”。这一悲剧性主题主要是通过“我”对祖辈的英雄过往的描述表现的。《红高粱》在文本叙事的探索方面所呈现的经典意义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如果将文本所要表达的最深层次的东西称之为理念,将文本的外在表象称之为形式,在阅读与分析小说《红高粱》的过程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二者完美的结合,它使作品以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读者面前发生。
任何叙事文学作品都必须具备两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即一个故事和一个故事的叙述者。二者的关系在作品中是一种最本质的关系。讲述一个故事有许多种方式,每一种讲述方式都会在读者身上唤起独特的阅读反应和情感效果。如何讲述直接决定这种效果能否实现。对于形式的琢磨,使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阅读作者的思想,而这种阅读,有时会比作者的夫子自道来得更为真实。
从总体上看,小说的第二部分与众不同。无论内容还是结构都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这部分叙述的是,“为了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我曾经跑回高密东北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调查的重点就是我父亲参加过的、在墨水河边打死鬼子少将的著名战斗。”为此,“我”查阅了县志并走访了村中当年幸存的老人。这种调查方式是常规的。叙事方式也是常规的。“我”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人,恪守一切叙述规则。这里涉及到的事件在其他部分中被充分展开描述。为了说明的方便,我们将第二部分称为序列A,其余则称为序列B。
很显然,这里出现了叙述分层,即“一层叙述中的人物变成另一层叙述的叙述者,也就是一个层次向另一个层次提供叙述者。”②这种形式上的安排为读者呈现了序列A与序列B的关系:前者是原始素材,是提纲;后者在此基础上创作而成。前者真实,后者虚构。即所谓感情是真实的,故事是虚构的。这里有如给我们展示了创作过程的一个环节,有着非常鲜明的元小说的味道。
其实这种结构方式我们并不陌生,它与古典名著《红楼梦》几近相同。“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后面又有一首偈云: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书云:……” 故事随即展开。于是读者看到了现在的《红楼梦》。
也就是从文本的层面说,《红楼梦》的故事蓝本就刻在石头上,石头就是叙述人;而后来的加工者是曹雪芹。这里显然也出现了叙述分层,我们姑且把石头上的故事成为序列1,曹雪芹增删之后的故事称为序列2,二者与《红高粱》的序列A,序列B的结构功能显然性质类似甚至相同。
我们再回到《红高粱》,会发现,虽然结构类似,但写法已完全不同。
首先,序列1与序列A不同。《红楼梦》中序列1只说这是故事的出处,并无实体内容;序列A则不然,有实体内容。序列A中“我”回乡调查家族史,调查的对象是一些年迈的乡亲,还查阅了县志。一是口头,一是书本。我们对历史的追踪也只能靠二者了。序列A涉及的事件有:作为小说主体情节的伏击战;中秋节大屠杀;修筑胶平公路,日本鬼子抓拉骡,罗汉大爷铲骡腿,被活剐,及其与“我”家的关系;奶奶的风流事。
其次,序列2与序列B更加不同。
第一,《红楼梦》中读者看到的只是增删之后的故事,我们无从知晓增删的依据或曰动机;《红高粱》中我们看到,序列A中的事件在序列B中被展开叙述,不过展开之中另有奥妙。举一例说明——罗汉大爷与奶奶的关系。序列A中“关于他与我奶奶之间是否有染,现已无法查清,诚然,从心里说,我不愿承认这是事实。”序列B中,罗汉大爷推开了喝醉了酒的奶奶,晃晃荡荡走进骡棚,给骡子拌料去了”,两人之间清清白白。这一细节,成就了“我”的心愿。这就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即序列B是按照“我”的心意构建而成的,“我”操纵着一切。也就是说,序列B是序列A中的“我”讲述的一个有关父辈的,掺杂着强烈主观倾向的虚构的故事。
第二,序列2中故事展开之后,无论是石头,还是曹雪芹,皆隐身不见,读者完全被带入故事的情境之中。在序列B中则不然。
按照常规,“我”虽然是实质上的叙述人,但必须如石头和曹雪芹一样隐身不见,因为,作为一个现代人,“我”当然无法亲临历史的现场,“我”只能依照序列A尽力去做让读者愿意相信的历史的还原。但莫言显然不愿如此。故事展开之后,“我”全番披挂上阵,唯恐读者将“我”忽略,表现出对传统叙事的刻意背离。
这里从作品中最令人难忘的混合人称“我父亲”入手分析。当“我父亲”看着余司令射向任副官的“子弹在低空悠闲地飞翔”,明显是叙述人“我”和父亲一起在看,形成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混合的视角。这种混合视点成为新时期文学史上的一个小小的奇观。不过,其实这种混合视点本身并不稀奇,即便是限制叙事,叙述主体从定义上说仍然完全知道故事有关的全部细节。在现代小说中,叙述者经常采用以一个人物视角选择材料,也就是说,只选择某个人物的意识“过滤”整个叙述。但叙述者身份地位还没有变化,叙述的材料由人物意识筛选,但叙述者依然控制所有的语言,文本的字字句句依然由他而出,他只是用一个人物的感知范围来限制自己的叙述范围。
因此,当我们讨论某种叙述方式时,我们谈的是叙述者身份与某种特殊“人物视角”的结合方式。叙述者可以做的,只能是尽量减弱自己的声音而已,消除就不可能。不过在传统文本中这一点被极力隐藏,就如《红楼梦》中的处理方法。在《红高粱》中,叙述人“我”则公然出现于事物的叙述过程之中,并以“我父亲、我爷爷、我奶奶”的人称方式使之尽力张扬。这种人为的有意暴露同时也直接把叙述人“我”推向前台。从情感上说,这种“我父亲、我爷爷、我奶奶”的人称方式也使得无限景仰英雄先辈的“我”直接在形式上与之表现出一种亲密关系,从而得以分享一份荣光。借由这种人称方式,叙述人“我”直观地出现在读者的视线中。
混合人称已经立场鲜明地向读者表明这呈现出的历史镜头中有“我”的目光,叙述人显然觉得还是不够,于是,“我”随意现身对故事中的人物做出自己的评论,要读者知道“我”的所思所想。在读者好不容易抛开人称带来的龃龉进入故事情境时,“我”随时发出现在的声音,惊人好梦。那间或出现的现代语言,现代生活观念的调侃插入,摇曳多姿,其灵动跳脱,扣人心弦。这里面有今人看历史的姿态,其实更有蕴含其中的因景仰而自卑而企图超越什么的欲望。同时,小说也确立了前所未见的一种叙事格局,即第一人称全知叙事,这使叙述人得以进入几乎毫无羁绊的叙述世界。从叙述学的角度讲,第一人称叙事所表现的一切都与叙述者有一种生命本体上的联系,因此这种叙述便具备有一种性格化的意义,使叙述人更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个性的张扬。
那血色天光的种种传奇,大开大阖的人物情节,不断将读者拉入作品情境。而“我爷爷、我奶奶、我想”之类的字眼不断出现,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到处处都有叙述人“我”的插入造作,将读者从故事及作品的情境中拉出来。“我”一方面讲着惊心动魄的故事,细数人物的情感历程;另一方面纵身而出评说事件的当代意义,使读者感觉好像正在注视舞台上故事的演出,从而不时将注意力从故事本身投注于对人之生存状态的更为深入的思考之中。读者极易与叙述人沟通。因为二者与被叙述对象有着相同的时间距离——都站在今天反观历史——即便带有虚构性的历史事件。这令读者回想起这个故事时很难将叙述人与这个故事分开。二者已经血脉相连。
就这样,与传统叙述方式中叙述人的刻意隐身不同,在此,叙述人在读者的视线中成了一个角色,一个与其所叙述的故事中的人物处于同等地被审视的地位,这个被审视的角色通过对事件的叙述及评说,通过诸种叙事策略的运用,向读者展开了他的心灵世界。“我”成了与其所讲述人物同样生动的人物,因而是一个被戏剧化了的全知叙述者。借由这个叙述人,莫言完成了他在叙述方式上的探险与叛逆。
在文本层面,序列A是现实世界,序列B是非现实的创作世界。我们看到,在现实世界中,“我”规规矩矩,不越雷池半步;在创作的想象世界中,“我”冲破一切,任意驰骋。序列B是一个如许自由的世界。也就是说,只有在想象中才有这样毫无羁绊的自由。这其实才是最深刻的悲哀,是这种形式安排的最动人心处,只因它如此真实地描述了我们的生存状态。从而在小说结构安排上达到了与现实生活的异质同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压抑已久的心灵在寻求突破,寻找希望,这时《红高粱》横空出世,几乎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安慰。我至今还记得当年读大学时我的文学概论老师在课堂上激情澎湃地宣讲《红高粱》,并在新年联欢会上要我们跟着他大喊“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情景。
在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中,叙事的形式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总与叙事性质结合为一体,最恰当地表现出后者,即令作品以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在读者面前发生。
对于莫言来说,始终萦绕于心的现实关怀和挥之不去的个人经验调动总是在寻找突破口,而二者的双重表现则往往需要分层。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叙事策略不仅仅是传达个人观念所借重的手段,而且是一种与个人观念水乳交融的东西。
在一本长篇小说的后记中,莫言认为“诉说就是一切”,并以惯有的语气写道:“所有在生活中没有得到满足的,都可以在诉说中得到满足。这也是写作者的自我救赎之道。”③这是莫言的“创作哲学”,《红高粱》则堪称阐述这一创作哲学的经典文本。
(责任编辑:范晶晶)
作者简介:夏环举,青岛酒店管理学院教师,汉语写作专业硕士,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②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第117页。
③莫言:《诉说就是一切——后记》,《四十一炮》,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