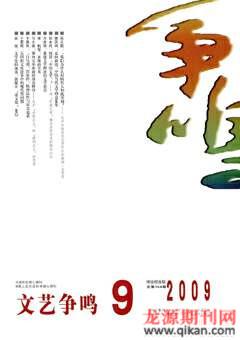以父权为核心的家庭伦理思考
孟春蕊
李安对电影的实践是从关注家庭伦理开始的,因其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复杂性,家庭伦理的东西方内涵就成为解读他影片的必须关注的一个方面。
一、家庭伦理的东西方内涵
家庭是人类社会共同生活中的最小单位,对于家庭问题,既可以从以个人为基础的角度来考虑,又可以从个人与他人关系(共性)的角度来考虑。人类是一种生命体,所以在家庭伦理的基础之中,就存在以下两项与生命体有关的自然事实:第一个是“性”的问题。家庭是在男女两性身心结合这个自然事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在这里表示肉体方面的“性”和表示精神方面的“爱”这二者的关系具有基本的重要性。虽然“性”与“爱”的关系是伦理问题,但是在其基础上,存在着个体中的身心关系(即身心的互相关系)这个生理、心理上的自然事实。在李安的电影创作中,两方面的矛盾都是他关注的重点,从《卧虎藏龙》中的每个个体都面临的身心困惑问题,到《断臂山》里两个人之间的性爱,李安都对这一命题的思考做了尝试。第二是以家长与子女的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的传宗接代的问题。家庭的成立是预料作为家庭成立的自然结果会生儿育女来延长生命这一点的,并且以此为前提。如果在实践上延长这种家长与子女的关系,就会成为祖先与子孙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人的生死这另一个自然事实。换言之,在祖先与子孙关系基础上的家庭的传宗接代,是与人类下述愿望相联系的问题,那就是超越个人死亡的永生。因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就是家庭伦理中的核心问题,李安早期的电影创作就把思考集中到这一话题,“身为人子比你是谁来得重要”,这是很多人认可的中国式命题。家庭这一共同体是在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条件——“生与死”和“身心关系”和这两个自然事实的基础之上成立的(前者与时间性关联,后者则与人类存在的空间性有关联)。关于家庭伦理的问题,开始于人们如何理解、解释并且处理这两个自然事实。
西方传统中是以个人为出发点来考虑共同体应有的存在方式。这种个人主义的态度,本来不是在家庭中而是在政治上伴随着社会契约说和民主权利的要求而产生的,但是后来,这种态度也被应用到家庭生活之中,于是那种认为结婚是平等的个人之间的双边契约的观念逐渐发展起来。而在东方的传统中,是把共同体放在优先地位来考虑的。儒家向孔子所讲的“仁”寻求伦理的根本。因此,人们认为在共同体中应重视人际关系,根据个人在共同体中所处的不同地位,遵守必要的道德规范。社会性共同体从最小单位的家庭,经由家族,以至国家、天下,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与共同体的各个层次相适应,都存在着负担一定工作的个人必须遵守的道德。
在这里可以看出,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东西方的传统在理解、解释存在于伦理基础的自然事实时是有差别的。但在文化表达上情感却存在着相通之处,无论是传宗接代的天伦之爱,还是身心相悦的两性之爱,都有世俗普泛的理解。身受两种文化浸染的李安在他的电影实践中将这种差别很好地表现出来,并尝试做了契合。
中国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对家庭和家庭伦理关系的表现就是常见的主题,主要的电影艺术家和经典的电影作品也有许多是表现家庭及家庭伦理问题的,如郑正秋、蔡楚生、谢晋的影片。(2)而好莱坞的通俗家庭剧,不仅构成了其一大电影群落,而且在电影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不乏可圈点之作。李安对这两方面的成就均有吸纳,并在自己的影片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中对“父权”的思考,就是其中主要的方面之一。
二、对父权伦理的影像表达和诘问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父权姓氏定于一尊为基础的伦理体系,无论君臣还是父子关系,都是非常男性的。几千年来,中国农业文明就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而凝聚家族的力量就是孝道和社会等级。“孝,礼之始也”,(3)百行孝为先,孝是最高也是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因此,当这种伦理模式遇上多元社会多元文化的挑战时,该何以自处是很多家庭都面临的问题。在台湾出版的他的自述《十年一觉电影梦》中,李安谈起过中国的“伦理”:我成长在一个保守士大夫家庭,个性也不算太叛逆,所以最能牵动我内心的还是伦理。面对不能尽孝,以及传统与现实间的种种矛盾,我有话想说。”
李安的父亲是台南一所中学的校长,士大夫观念非常严重,古风治家,教子甚为严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逢年节家中甚至要行跪拜礼。“读书做官”、“金榜题名”是他对李安这个长子唯一的期望。1973年李安在两次连考落榜后报考台湾国立艺专戏剧电影系,让他大为恼火,他始终认为这不是正业,甚至多年后在李安扬名国际影坛,捧着奥斯卡回家时,他仍然把李安叫到身边问他想不想教书。在这样浓厚传统氛围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李安,家庭带给他的不仅仅是文化的浸染,父权家庭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压力,更是他成年后也难以抹去的阴影及情结,这一切恰恰成为他影片最近距离的原始素材。
被称为“父亲三部曲”的《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就是李安在蛰伏期后对家庭伦理中的父子关系的一次集中思考。在《推手》、《喜宴》中,文化差异只是引发矛盾的背景,李安真正表达的仍然是亲情面临压力下的困惑。
《推手》的故事情节非常简洁:父亲老朱是一位太极拳大师,退休后被儿子朱晓生接到了美国,他的到来干扰了儿子儿媳的正常生活,引发了一系列家庭矛盾,到最后父亲自己选择了离开,搬到老人公寓。
影片中的父亲是强势的,一出场就给人以压力:一身内敛沉着的太极推手功夫,花白的头发,凌厉的眼神,整洁的习惯,当这样一个强势的人物面临老无所养的困境时,影片的张力立刻就出来了。矛盾冲突以老朱的几次离家为主线展开。
第一次老朱的走失是无意的,与玛莎的言语不通、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以及玛莎的冷淡观望都让他倍感孤单,他的迷路是无心之失,却引发了家庭矛盾的第一次爆发:温文的晓生在他走失后斥责妻子的照顾不周,并把厨房砸得一塌糊涂,老朱被警察送回,儿子醉酒归家。在这场冲突中李安把父子的心理刻画的细腻微妙:晓生的焦急烦躁,儿媳的愧疚委屈,老朱的歉意茫然,家庭隐藏的危机在这里一一展开,而晓生在接过儿子递过来一块纱布后的一句台词:杰米比爷爷和妈妈更会照顾爸爸,更是道尽了晓生的委屈和抱怨。这个时候父亲是懵懂的,他隐约知道有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知道自己的走失给儿子添了麻烦,但他绝对想不到自己是儿子儿媳冷战的原因。因此当玛莎胃病发作时他还是主动地给玛莎医治。玛莎的不信任和防范让他觉得受到了伤害,但并没有影响他的强势心理:他一开始就是淡化处理和儿媳的关系的,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父子间的沟通才是解决家事的关键。
老朱的第二次离家是在知道儿子布局撮合自己和陈太太之后。儿子的有心最初老朱是受用的,他对陈太太的好感也很直接,直到爬山时被儿女有意甩开后,陈太太的气急败坏才让他意识到儿子撮合背后的隐衷,这对他而言是无法接受的打击,儿子的真正用意竟然是希望老父亲有了自己的生活后,能离开自己的家,不再成为他和玛莎生活的干扰。父亲的尊严受到了伤害,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事实,老朱的伤感可想而知。他留了一封信离家出走,也把内疚留给了晓生。
老朱离开家后的困境是双重的,在生活和情感上都孤立无援,本是为着天伦之乐而来,可到头来竟然以七十多岁的年龄流落在餐馆洗碗,这种困境对任何一个老人都是残忍的,更何况是这样一个身怀绝技的老人,陋室内老人练气功的画面给人英雄末路的感觉,可后面还设置了更大的困境——被老板解雇。被斥令离开的老朱忍无可忍,在厨房内大显神威,使出推手功夫,将老板招徕的地痞一一震开,一头白发凌乱而尊贵,他的坚持不走里有太多悲凉的东西,胜得心酸。最后老板动用了警察,老朱被带到警局,闻讯赶来的晓生跪下放声大哭,父子相对无言。
最后儿子的新家里给老人留了一间房,但老朱却选择了独居。这种放弃里有太多复杂的成全:父亲引发了儿子一家的困境,到头来解决困境的仍然是父亲。导演对父子关系的处理是肯定的:在父亲的面前,子辈的挣扎和犹豫都是无力无能的,影片结束时老朱与陈太太相遇在纽约忙乱的街头,身后是耸立的摩天大厦,两个人都从儿女家中搬离,在这个西方价值充斥的纽约放弃了传统意义上应该安享的天伦,无奈中仍保持了老人的尊严。
《推手》里的人物关系是体贴的,每个人的为难都有合理性,父亲的离开在李安的表达里是一种无奈的自尊,也是对儿子的成全。晓生说到底是惭愧的,父亲成全了他的小家,也成全了他的不孝。片中虽然没有指责,但导演的视角是沉重的。到了《喜宴》(1993),虽然同样是父子矛盾,李安的处理要轻松得多。人物关系的设置也多了几分戏剧性和喜剧性。
《喜宴》中的父亲是一位戎马一生的将军,是典型的父权形象的代表,虽然不再强壮,但仍是儿子想都不想与之对抗的人。
来自台湾的伟同是一名同性恋,他和美国男友赛门已经同居五年了。随着父母年事己高,二老施加给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为了敷衍父母,男友帮他选择了需要一个合法的美国身份的大陆女孩威威假结婚,没想到父母亲自飞来美国参加婚礼,并举行了传统的“喜宴”,各色人等在这场貌似完美的“喜宴”中尽情地表演:众人逼新郎新娘钻进被窝,然后将衣服一件件扔到被子外,李安本人也跳出来面对镜头说:“那是中国人五千年的性压抑”。——其实,正如李安所说:“《喜宴》是部李安的电影。我的教养、背景都反映在里面。”(4)可以找得到李安后来作品的所有主题:文化冲击下的身份困惑、人在自由意志与责任义务之间的矛盾挣扎。
在这场“喜宴”过后,五个人组成了一个奇怪的临时家庭里,三个年轻人小心翼翼,惟恐骗局被老人识破,但没想到的是伟同和威威在争执中的假戏真做竟让威威怀孕了。三个年轻人用英文大吵了一架,第二天,父亲住进了医院,伟同向母亲坦白了同性恋身份。到这里,局面开始发生变化,母亲开始和三个年轻人一道隐瞒父亲。几个人之间形成了 “我知道你不知道,你知道他不知道”等滑稽而又令人辛酸的局面。直到赛门过生日时父亲给了赛门一份大礼,观众才明白原来父亲的心中早就知道了真相。伟同的母亲暗地里落了许多的泪,倔强的父亲问她哭什么,她说是高兴的,父亲说“我也高兴”。
威威不忍心,留下了孩子,二老回台,留在纽约的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奇怪家庭。结局令人感动,走过机场的安检通道,为接受检查,戎马一生的父亲举起了双手,却仿佛是向下一辈投降的标志。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在这部片子里样样不落,李安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境遇描绘得淋漓尽致,“传宗接代”的家族思想,在被西化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之间苦苦挣扎,最后大家达成的默契,似乎找到了平衡。《喜宴》是一部对文化背景感兴趣的电影,但毫无疑问的是这部电影剧情的主线不是高伟同与赛门的同性之恋,吸引我们的是高伟同如何对父亲表白他的同性恋身份,父权的长期压制造成的压力和对父亲的深厚感情之间,存在着太多复杂的细节,最令人深有感触的情节是父亲晨练回来后坐在椅子上瘫睡,伟同上楼叫父亲早餐,把手伸到父亲鼻子下试探他的呼吸,试过后伟同松了一口气。父亲的老迈让儿子解除了原有的压力,但另一种伤感也随之而来。母亲可以在他成年后仍抓着他的手臂咬,但父子之间的这种情感表达往往更含蓄微妙。
整部电影里我们看到的是对父亲权威的熟悉和顺从,导演在表达时让观众不自觉的合理化这种对父权结构的认同。因此尽管伟同对自己的同性恋抱持着健康自然的态度,但是并不愿意去挑战异性恋以及传宗接代,他的能躲就躲,能骗就骗,能瞒就瞒里有太多传统的阴影,《喜宴》的重心最后落到父子亲情,但导演的意图很明确:儿子不应当挑战父亲的权威,影片最后亲情的的维护、父权的保障和家庭的和谐延续最终都凭借它得以实现。
1994年李安创作了《饮食男女》,父子矛盾转化为父女矛盾,这使得冲突的表达更为微妙。仍旧是郎雄饰演父亲,仍旧是“老朱”,仍旧是老人问题,但可以比较出,李安在这部影片中表现的更加成熟。人物比《推手》多了很多,情节也远比《推手》复杂。影片中的父亲老朱是台湾国菜的大厨师,和三个女儿住在一所老宅子里,每逢周末他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做一桌丰盛无比的菜肴和孩子联络感情,但每次似乎都不顺利,都有意外:二女儿家倩要搬出去住,三女儿家宁要生孩子,大女儿突然结婚。三个女儿从老处女到情窦初开的都有,鳏夫爸爸束手无策,十分尴尬。
影片中穿着两条线:“饮食”和“男女”,暗合着“食色,性也”。按照编剧王惠铃的讲法:吃、饮食是台面上的东西,欲望男女则是台面下的东西。台面下的东西永远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讨论,尽管性是家庭的根源,家庭营造了合法的性关系,但在中国家庭里,性是一个禁忌,父母从来不和孩子讨论,父亲和女儿更加难以启齿。这就构成了影片中爸爸和女儿一系列荒谬行径的由来。影片有多处性爱荒谬矛盾的描写:如仍是学生的家宁怀孕了,要和男孩结婚;家珍把暗恋的对象想象成辜负她的初恋的男人,在传统、保守的外表下,其实充满了对爱情的期待与渴望;看来似乎是最杰出理性的家倩,和分手的情人维持着“十分松散的亲密关系”,不是爱人反而能自在相处;以及老朱和锦荣出人意外的老少配。种种意外造成观众一波一波的惊讶,暗含着传统的禁忌被打破后,西方价值观充斥的都市中男女之间因为孤独所以渴求,因为可以无所顾忌所以速成的情感趋向。李安运用种种暗讽并略带喜剧的手法,提醒观众们某些社会现象的既存。借着种种荒谬却合理的剧情,让观众去重新思考在这个都市生活所必须面临的问题:没有人能判定别人的对或错,父亲没能干涉女儿们的生活选择,女儿也没能改变父亲的心意。在饮食上,口味无争辩,生活也一样。
和《推手》中远赴美国的老朱相比,这个老朱是在自己的本土上接受自己父权失败的,而这个父权的失败更是从家庭内部开始解体的。李安自己也难以说清对于这个颓倒的父权的微妙感受,是老一辈旧时代结束的凄凉惆怅,还是年轻一辈新时代开始的兴奋彷徨,都被李安的中庸平和一包而容。整部影片,平和之中透着紧张,而最后父女两人的伤感惆怅却显得温馨感人。
在这三部作品中,每一个父亲的身上都有传统文化的符号,太极、书法、美食,“父亲是压力、责任感及自尊、荣誉的来源,是过去封建父系社会的一个文化代表。”从父辈身上,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台湾、在年轻人身上的变化。一方面,年轻人以自我实现与之抗逆,另一方面,又因未能传承而深觉愧疚,这种矛盾的心情不仅是儿子对父亲的感受,也是导演对传统文化在台湾产生质变的感受。”(5)越往后拍,父亲的形象就越弱。《推手》中的父亲最强势,每次出现都带给观众压力,到了《喜宴》,求子心切的师长就多了些运筹帷幄,但他经常打瞌睡,甚至被送到医院急救。及至《饮食男女》,家中没有了儿子,血脉传承的意味越来越淡,父亲的选择更让人意外,借由年轻漂亮的妻子得以过一种现代的生活,最后还恢复了味觉。李安凭借着这三部影片将生活中父亲带给他的压力和阴影一一化解,突出表现了这个各种文化杂糅的时代社会基本单位——社会文化和家庭伦理观念上的变化。虽然中庸却很现实,其表现手法也同样质朴自然,继承了台湾电影生活味道浓厚的传统。
三、对家庭伦理问题的拓展
“父亲三部曲”后,李安开始进行西方题材的尝试。《理性与感性》《冰风暴》都是他对家庭伦理问题的进一步拓展。如果说《理性与感性》只是将思考换了一个时空,西方的“绅士”与东方的“君子”在文化表达上情理相通的话,李安在《冰风暴》中的思考要复杂得多。
在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的西方文化冲击,一次在上个世纪初的五四,一次是在上个世纪末的80年代后期,两次都是在经历了太久的封闭后,随着国门打开,西方文化排山倒海般一涌而入。在台湾,因为没有文革的人为破坏,后一次的冲击在时间上要比大陆来得更早,这也正是“父亲三部曲”中旧的伦理秩序受到挑战的由来。李安在对《冰风暴》中的思考正是基于对这种文化冲击上的互相作用与影响。
《冰风暴》的背景是1973的美国,“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背叛的氛围”。那是一个父权坍塌的年代,美国第一次经历石油危机;尼克松的水门听政会,总统第一次在电视上公开承认说谎;越战停战,世界第一大国仓皇从中南半岛撤军;美国、国家、元首这些父权形象突然幻灭,一向充满活力、不虞匮乏的美国人不知所措。如果说以前李安的家庭伦理讲的都是家庭对个人的约束、解构和改变。这一次李安反其道而行之,将个人置于极度的自我空间:当社会的道德维系崩溃,个人彻底解放时会有怎样的状况发生?李安抓着“家庭”这个还没尽兴的主题,试着从反面切入。
《冰风暴》的家庭是个典型的核心家庭,本·胡德及吉米·卡佛两家人面临各自的尴尬,两代人同样无所适从:中年人的背叛、荒唐、换妻派对,少年人对“性”的好奇和试探……一切都没有边界,没有约束,也没有正确答案。自由状态带给人的不是幸福感,反而是更多的不知所措。在《理性与感性》中,社会制约,每个人都想越轨,追求自我;而《冰风暴》里,社会开放,你被鼓励叛逆,任性而为,每个人反倒处于本性中的保守良善,重新思辨常轨。“冰风暴过后,一个青春的生命被吞噬”李安选择这样一个结局,以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他者”身份观察西方这段历史,在细节血肉上周到地考察了那一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社会时期美国的文化特质。在那里,李安找到了《推手》、《喜宴》、《饮食男女》等影片中文化冲突的根源,其本意是在探询伦理困惑的社会根源:他一直致力描绘的东方式家庭就是从那里走向崩溃的、父权就是从那里走向衰落的。
至此,李安对成长过程中父权引发的压抑作了一次整合思考,从东方的亲情伦理到西方的文化冲击,再到这一系列冲击变化的的社会根源,李安完成了他自己成长中由“父亲”带来的问题。正如李安自己后来的表述: “处理父亲形象十分有助于我的生活与创作,有着净化与救赎的功能”(6)。在这之后,李安开始把思考的目光转向自我——个体的压抑与欲望。
注释:
(1)(4)(5)(6)张克荣编著:《华人纵横天下——李安》第,现代出版社(北京),122页,第94页,第120页。
(2)侯耀:《影戏剧本作法》,见罗艺军:《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上册,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
(3)《左传·文公》。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省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