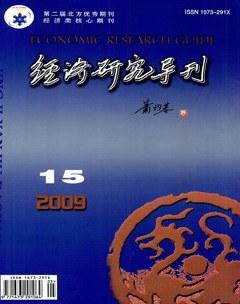企业规模扩张的经济增长含义
赵 祥
摘要:首先简单梳理了关于企业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用中国工业发展的经验数据证明了,企业规模扩大和企业数量增加共同推动了中国工业产出的增长,指出产业组织的发展体现了规模经济性和分工(专业化)经济性的统一,正是二者的统一推动了长期经济增长。
关键词:企业规模;交易费用;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7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5-0028-03
产业组织的发展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由于新的市场机会出现和分工的发展导致一个产业内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二是行业内现有企业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生产要素的进一步集中,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对于产业组织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现有的文献中存在着两条相对明确的研究路向:(1)新古典的规模经济和递增报酬范式,自马歇尔(Marshall,1890)以来,新古典范式主要讨论在既定的分工结构下如何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在解释经济增长的来源和机制时,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规模经济和递增报酬的作用,企业会随着规模的扩张而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这种规模经济效应则是经济发展的动力(Marshall,1890;Samuelson and Nordhaws,1992;Krugman and Obstfeld,1997)。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狄克西特(Dixit,A)、诺曼(Norman,V)、兰开斯特(Lancastes,K)、艾瑟尔(Ethier,W)及克鲁格曼(Krugman)等发展起来的新贸易理论,尤其重视规模经济的思想,基于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他们建立了内生的经济增长模型。与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的思路不同,他们更加强调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企业规模的扩大促进了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成本降低,并最终导致长期经济增长。(2)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传统,他们遵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主要从分工演进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增长,并结合了交易费用概念,形成了“分工—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亚当·斯密最早指出促进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要解释经济增长问题,首先必须说明决定分工水平的因素。斯密由此发展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阿林·杨(Yang,A,1928)进一步发挥了斯密的分工学说,认为市场容量又是由分工水平决定的,因而分工水平最终决定了分工的动态演进,因此,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就归结为对经济系统中分工演进的研究。继承这一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鲍姆加勒(Baumgarden.J)、基姆(Kim.S)、洛凯(Locay.L)、杨小凯、博兰德(Borland.J)以及贝克尔和墨菲等人,相继提出了一条基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经济的内生增长思路,形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用专业化表征生产条件,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思想。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廖伯伟发现1970年以后厂商平均规模逐步下降,而同期这些国家的总产出和人均收入都在不断增长,企业规模变化和产出增长不一致。张永生(2003)用企业雇佣的劳动力数量来衡量企业规模,在分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时间序列数据的基础上,揭示了这种意义上的企业规模和经济增长的负相关关系,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厂商规模无关论”,指出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厂商平均规模越来越小,总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厂商规模无关论”将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分析结合起来,并且为了便于进行这种分析,用企业雇佣的劳动力人数来表示企业规模。在此条件下,企业规模的变化取决于分工在企业内还是在企业间发生,而这又取决于劳动和中间产品各自交易效率的高低。如果劳动的交易效率较高则分工在企业内发生,企业就会多雇佣劳动生产中间产品,企业规模会随之扩大;反之,则分工在企业间进行,企业就会选择外购中间产品,减少雇佣劳动,企业规模减小,企业数量增加。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市场交易效率越来越高,交易费用越来越低,企业规模越来越小,主流经济理论中的规模经济效应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不起作用。一些新的商业实践如外包(Contracting out)、特许经营(Franchising)、外购中间产品和服务(Outsourcing)及贴牌生产(OEM)等为这种观点提供了部分事实上的支持。
1.企业的横向规模。主流经济学所使用的企业规模概念实际上是指企业的横向规模,企业被看成一个投入产出装置,其最主要的功能是从事生产,企业规模就是企业的均衡产量,它由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来决定。
古典经济学通过规模经济(生产)来解释企业扩张的机理。有关企业存在与扩张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斯密(Smith)和马克思(Marx)。他们主要是从分工深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来规模效应的角度来解释企业的存在和扩张的。斯密以制针厂的例子说明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报酬递增现象,技术进步引起劳动分工的深化,由于分工所形成的一些工序、工种是密不可分的,必须在同一组织中进行,因此企业规模随着分工的深化而扩大。他还指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而分工深化的边界就是企业规模的边界。马克思也认为协作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协作的经济效果大于单个生产者的经济效果之和,协作的不可分性决定了协作的规模,这就是企业的最小规模。
在利润最大化的假设下,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的横向边界主要是由生产中的技术因素决定的。当企业依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去组织生产时,它所选择的生产规模是最佳的,规模报酬递增空间的消失与否成为判断企业最佳规模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已经认识到, 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中, 确定企业边界时所需考虑的因素是不同的。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同一行业内部存在着众多的生产同质产品的厂商,每家厂商是既定的市场价格接受者(price taker)。从长期来看,由于资源在各行业间可以自由转移,因而每家厂商最终只能获取正常利润,在产品价格等于最低平均成本处进行生产,对单个厂商而言,企业的最佳规模是由其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来确定的。完全竞争模型的中企业规模定义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根据完全竞争理论,当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为传统的U型时, 企业尚可在市场竞争中选择最佳规模;而当厂商的长期平均成本线为水平线或向右下方倾斜时(即始终存在着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增现象),企业就无法确定其最优规模了,因为这时它无限地扩大生产,始终会使平均成本等于或低于产品的价格,是有利可图的。针对上述问题,经济学家们开始放弃了完全竞争的假设,在其他市场结构中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斯拉法(1920)指出,企业之所以停止进一步的扩张,不是因为这将使产品的平均成本上升而超过既定的产品价格,而是因为这将使产品的市场价格下降而低于企业的生产成本,现实中的企业并非完全竞争意义上的价格接受者,在非均衡状态下, 企业产品面临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使市场是竞争性的,但由于差别产品的存在,企业产品面临的需求曲线也将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市场竞争仍会使厂商按照价格等于平均成本的原则组织生产,但需求曲线与平均成本曲线的切点,不在平均成本线的最低点上,而是在其左侧的某一点上。可见在垄断竞争模型中,企业在确定边界时,不仅要考虑自己的产品成本,同时还要研究市场需求因素。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市场需求的增加,可以导致企业规模扩大,当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为水平线或向右下方倾斜时,市场需求的大小制约着企业的横向规模。
2.企业的纵向规模。企业的纵向规模揭示了企业内部所包含的生产环节的多寡,它由企业所涉及的交易费用决定。自科斯(1937)以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将企业看成是有别于市场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一种经济交易的治理机制,企业的存在体现了对市场交易费用的节约。科斯以前的经济学把企业的存在本身作为一个前提,而科斯的贡献在于对这个前提进行了重新论证。他认为,企业的产生是为了节约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企业组织可以内化市场运行的成本,但同时企业代替市场也是有成本的,即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只有当企业节约的市场交易成本大于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时,企业才有利可图,规模才会扩大,企业会包含更多的生产环节。企业的最大规模为“企业将倾向于扩张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者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科斯,1994)。”张五常认为,由于市场交易的对象是商品,“企业交易”的对象是要素,因此,企业代替市场是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由于要素市场的合同和产品市场的合同都是私有产权借以让渡的工具,两者没有本质区别。当劳动要素的交易费用低于产品市场的交易费用时,企业规模就会扩大,企业就会增加雇佣劳动的数量,直到二者的边际交易费用相等时为止。
在使用不同企业规模概念的基础上,他们分别强调了企业的规模经济性和分工经济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事实上,无论是经验证据和理论分析都说明了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规模经济性导致了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性,分工所引起的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间歇时间的减少和物质资料的节约都可概括为规模经济性(盛洪,1994)。不同经济学家分别将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古典经济学家将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性作为自己分析的起点,而作为回应,新古典之集大成者萨缪尔森认为,规模经济性很大程度上来自合理的专业化和分工。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引进交易费用概念揭示了企业和市场是现实中资源配置的两种替代机制,企业的出现是为了节约市场的交易费用。在现实中,专业化的生产者个体之所以不通过市场买卖他们生产的专业化产品—中间产品和服务,而选择聚集在一个企业内,是因为市场的交易成本超过了在企业内组织生产的成本,企业一旦形成便具有超过单个生产者的规模,因而在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看来,由于交易费用的节约而出现了一定规模的企业。因此,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一定的情况下,规模经济就是对交易费用的节约;而当我们考虑了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规模经济实质上就是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对生产费用的节约。企业的全部成本表现为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的总和,因而规模经济(分工专业化经济)实际上表现为企业总成本的降低。
我们在现实中可以看到企业规模的扩大及企业数量的增加和区域经济增长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下面我们就用中国工业发展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来探讨企业组织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体来说,我们用工业企业数量的变化来表明行业的分工水平,用企业规模的变化来表示行业的规模经济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来具体分析企业数量、企业规模变动与工业产出增长的关系。
由于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严格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没有保障私人产权确定和实施的法律制度,更没有自由的价格机制,因此在这种经济制度条件下,企业的投资权完全由政府实施控制,企业规模和数量的变化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工业产出的变化同样也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他们都依赖于国家计划的实施,这一时期的数据不适合我们的分析。为此,我们选择了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后的数据进行分析,时间跨度从1978—1997年。
为了计算1978—1997年间工业企业数量增加和平均规模扩张对中国工业GDP的贡献率,我们设定了一个简单的回归方程:
LogGdp=C+B■LogSi+B■LogNi+ε
其中,Gdp表示工业GDP的增长,Si表示企业平均规模的增长,Ni表示企业数量的增长,ε表示残差项,下面是对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
logGdp=-14.082+2.818logNi+1.218logSi+ε
(-16.96) (13.15)(8.47)
R2=0.97 F=305.706
我们可以看到方程的拟合优度较好,表明了中国工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和规模扩张与GDP显著正相关,二者的变化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根据回归结果,我们分别计算了1978—1997年间工业企业数量增加和平均规模扩张对工业产出的贡献率。在1978—1997年间工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对工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53%,工业企业平均规模扩张的贡献率为46.49%。
企业纵向规模理论上的逻辑起点源自于亚当·斯密的古典分工学说,并结合了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决定企业纵向规模的最终因素是劳动和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各种变量的交易效率的不同组合会导致不同的分工水平和经济绩效,分工水平内生地决定了企业制度。杨小凯、黄有光(Yang and Ng,1993)的间接定价理论将张五常(1983)的“企业用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的企业理论形式化了,赋予企业理论以经济增长的意义。当劳动的交易费用小于中间产品的交易费用时,企业就从分工中内生出来;在给定的企业制度出现后,如果中间产品的交易费用下降得比劳动的交易费用快,则企业会在市场上外购中间产品,减少雇佣劳动进行生产的数量,企业规模会随之变小,分工主要在企业间发生,单个企业越来越专业化。反之,企业规模会扩大,分工主要在企业内部发生,企业更多地是自制所需的中间产品而不是通过市场向外部购买。
“分工—交易成本”分析框架对于企业的一体化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却不能解释企业横向规模的确定问题。现实中的企业的确具有交易和管理职能,企业进行市场交易和内部交易(即管理)都是要花费成本的。企业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与市场相比较, 企业具有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交易成本的大小决定了企业的均衡。但企业在本质上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不仅仅是一个交易单位,仅用交易成本去解释企业的边界是不够的。实际上,企业作为一系列契约的集合,是加入契约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集合,是各生产要素交易契约的履行过程, 这一过程融交易功能与生产功能于一体(谢德仁,2001)。交易费用分析仅仅抓住了企业组织的“交易性”一面,而忽视了企业的“生产性”。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认为,市场的交易和企业内交易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企业组织与市场的最大差别在于其生产功能,企业组织通过联合生产(队生产)创造出更大的经济剩余,生产的联合效果和团队监督与激励的同时存在导致了资本主义古典企业的形成。因此,无论在企业进行生产活动内部化之前或之后,企业的最优规模都是建立在包括生产成本计算在内的利润最大化基础之上的。新古典范式与经济现实的脱节为交易成本理论的产生预留了空间,但“分工—交易成本”框架并不能完全取代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企业均衡的分析,生产成本仍然是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的决定因素。企业内部各个生产要素的结合导致生产成本内生于专业化分工的收益,而为了结合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和销售,企业在不完备的信息世界中必须付出搜寻、谈判、签约和契约实施等交易成本,这种交易成本又内生于生产要素的结合(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是内在统一的,二者统一于企业的产出,二者的结合才最终决定了企业规模的纵向和横向均衡。在这种企业均衡的意义上,企业规模的变动包含了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变化的因素,分工经济性和规模经济性才能真正统一起来。正是二者的统一使我们在现实中看到,企业数量的增加和企业规模的扩张共同推动了长期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North,D.,“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M].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
[2]Dixit.A and Stiglitz.J.E.(1977),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7,No.3,pp.297-308.
[3]Xiaokai Yang and Borland.J.(1991),“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of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99,
No.3,pp.460-482.
[4]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5]张永生.厂商规模无关论——理论和经验证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7]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M].高鸿业,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8]哈罗德·德姆塞茨.企业经济学[M].梁小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9]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王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