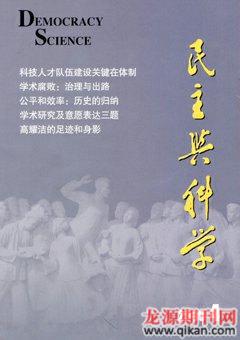鲁迅:体味启蒙之痛
丁国强
鲁迅处在“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过渡时代,在沉闷而苍茫的精神氛围里,启蒙者难以逃脱“中间物”的尴尬处境,这决定其精神角色的多重性。鲁迅的伟大首先来自其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鲁迅的声音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依附性。鲁迅不是中国第一个启蒙者,却是启蒙思想表达得最充分的现代思想家,他对中国人麻木、愚昧的品性有着最痛切的描述。人们把鲁迅当作认识自我、剖析自我的一面镜子,通过不同的视角审视鲁迅的精神世界,其中不乏“同情之理解”,也有不少世俗成见。作为话题的鲁迅是不拒绝任何当代化的阐释的,鲁迅似乎与任何一个庸俗卑鄙的时代针锋相对,这恰恰是鲁迅的魅力所在。鲁迅所展示给世人的是“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人生,然而,人们却出于各自的目的给鲁迅戴上了五花八门的面具。鲁迅的力量在于真实,这种真实源自生命内在的抗拒,抗拒“中国向来的老例”,抗拒“西崽相”,抗拒帮忙和帮闲,抗拒麻木的看客心态。
从赴南京学开矿,到日本学医,以及弃医从文,青年周树人走异地,寻出路,在漂泊中苦苦求索。仙台成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起点。“幻灯片事件”已经成为我们理解鲁迅的一个不可忽略的精神事件。在日本求学的周树人的精神基调是压抑和苦闷的。这种痛苦是超前的,先觉的。因为更多的留学生是在过一种自以为是、自欺欺人的快乐生活。“幻灯片事件”对于浑浊的眼睛和麻木的心灵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而对于青年鲁迅而言,则是一道无法挥去的精神伤痛。青年鲁迅的思想是与当时新兴的社会思潮相合拍的,诸如推崇科学,相信进化论,反对清朝共和革命等等,但是,鲁迅并没有停留在新潮的观点上面,他的《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文章提出了“立人”这一深刻的思想命题。正是这一深刻的思考和真切的关怀使得他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平均化”状态。
鲁迅1912年至1926年在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担任公务员。在机关里办公、在官场上沉浮的鲁迅扮演着为五斗米折腰的角色。鲁迅在教育部的职业生涯是考察其心路历程的独特视角。与同代人相比,鲁迅的深刻和凝重来自他的坎坷的人生经历,家庭的败落、兄弟的纷争、生存的艰难都让他充满焦虑和痛苦,所谓“心事浩茫连广宇”。鲁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以骂人为职业,虽然在性情上他是地道的文人,但是,为了谋生,他就职于教育部,从事着繁琐而无聊的公务。鲁迅在1925年3月31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经历了希望破灭的过程,鲁迅所获得更多的是容忍、静观和沉思。正是由于近距离地观察了腐化怪异的官僚丑态,鲁迅才对旧势力有着刻骨的憎恨与愤怒。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却要忍受着庸俗的官场事务和乌烟瘴气的官场风气的折磨,这种磨练对于鲁迅的思想和写作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虽然身在官场,但是,鲁迅显然没有学会和适应“潜规则”下的官场生存,鲁迅的公务员生涯是一直不顺利的,他是一个蹩脚的公务员,无论是在南京还是在北平,他都常常因得罪上司而险遭除名。他的内心与官场相去甚远。职业不过是人的生存外皮而已,并不能控制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反戈一击是鲁迅的性格中坚硬的一面,而那些故意作态的人则往往无法掩饰其媚俗的一面,正如鲁迅所言:“中国的隐士和官僚最接近的。”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其实是一直与官场保持相当一段心灵距离的。这种 “营垒中的反抗”是与鲁迅的坚韧性格有着内在的关联。鲁迅是官场上的异数、另类,他无法更改自己的文人习气,虽然也有 “枯坐终日,极无聊赖”的时候,但是,他更多的是把时间放在了读书思考和整理古籍以及到北大、北师大兼课上,这是一种靠容忍所获得的自由。这是鲁迅的生存智慧。在体制内生存虽是无奈的选择,却也不失为近距离观察人生的一种手段。不少学者在进行鲁迅与卡夫卡的比较研究时,都十分强调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职员经历,也许正是有了官场那种异化生存的体验,才会有“吃人”与“变形”的发现与自觉。
一生傲然独立的鲁迅从不姑息黑暗,决不“将纵恶当作宽容”,用“最坏的恶意”和入木三分的骂来表白着自己的毫不留情和“不识时务”。在专制和残暴的政治空间中,鲁迅对那些暴发户的革命新贵和靠杀人起家的政治流氓,冷眼相看,恨之入骨。不愿当“暴君的臣民”的他对统治者所炫耀的“治绩”自然是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对政治的绝望实质上就是对现实的清醒。政府在压制言论,草菅人命,它所造成的许多血和许多泪令鲁迅无话可说。鲁迅对残暴政客的种种恶行是无比愤怒的,所以,他“论时事不留面子”。鲁迅的“不满”不仅仅是对“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独裁政府的反抗,也是理性精神和公共关怀的体现。鲁迅在断言中国不存在俄国那样的“智识阶级”的同时,也在竭力担当着精神界战士的职责。没有鲁迅这样不停地与黑暗捣乱的思想者,当权者会更加肆无忌惮,而奴才们则睡得更加香甜。鲁迅是一个全方位的不合时宜的人,是一个永远的“异端”。
鲁迅的呐喊大都是内在的,决不是空洞的口号和空虚的喊叫,即使是激烈的谩骂,也透着一股沉郁、冷峻的气息。鲁迅戳穿了许多演戏者的鬼把戏,制止了他们向权势转化的进程。鲁迅的伟大在于他不是用一种话语霸权来取代另一种话语霸权,他甘当失败的英雄,单身鏖战的武人,抚哭叛徒的吊客。他在同论敌的争执中是坦荡的,没有预谋,也没有圈套,甚至连自我保护都没有。他在来自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中夯实着自己的精神根基。丰富着自己的精神血肉。
坚守独立性的鲁迅是一个坚硬的存在。他自称是“无所属”。他排斥主义、派别、山头和堡垒。在那个“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的变幻时代,鲁迅执著地选择了孤独。他用这种近乎自我折磨的方式对抗着传统的习惯、惰性和压力。他所运用的批判尺度来自自我的价值确认。鲁迅的价值关怀超越于时代,超越于个体,是对人的价值的关怀,对生命自由的呼唤。鲁迅先生的“大怒”是深刻的,是爱与憎交织的激情的迸发。鲁迅先生对我们民族的灵魂有切肤的体察,他最大的敌人是腐朽的传统文化,是“一级一级驮伏着不能动弹”的黑暗社会,他对我们民族文化中积淀下来的奴性是极为敏感的。而这种奴性根深蒂固,像污浊的空气,虽然看不见却时时刻刻缠绕着人们,无法摆脱。而一般人对此是全然不察的,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并且乐意充当“看客”,甚至参与“人血馒头”的交易。这正是鲁迅先生常常感到孤立无援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近现代的启蒙运动时常夭折的症结之所在。所以,鲁迅先生感觉到自己处于“无物之阵”当中,亲自感受到“软刀子割人不觉痛”的惨烈。
鲁迅身上洋溢着一种无以言传的革命气质。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始终是浮在时代表层的革命喧嚣和投机式的革命假象的反抗者、揭露者和消解者。革命如果不是出于人的内心自觉,就会异化为一种戕害心灵的权力,就会成为“做戏的虚无党”的花招。革命是一个不断被误读和改写的词汇。怀着不同心思的人,按照自己的意图对革命进行着“过度解释”,演绎或扭曲着革命的本意。革命文本成为心灵真实的对立面。那些声嘶力竭叫喊革命的人,大多是形形色色革命话语的替代品,是语言暴力的牺牲品。他们既是革命的宣告者,同时又是革命的囚徒。而鲁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清醒地看到了革命的多义性和被利用和歪曲的可能,从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没有成为革命的派生物。鲁迅对革命悖论的认识是深刻的。革命在解放人的同时,也会造成另外一重束缚。革命不可能包治百病,更关键的问题是革命本身也会成为一种病。革命者所忽略的恰恰正是鲁迅所关注的。他始终担心革命的无节制会演化为一种流氓行为。正如李长之所言,“鲁迅永远对受压迫者同情,永远与强暴者作战”,所以他总担心那些起来造反的奴才做了主子之后的状况,可见,鲁迅的忧思是何等深远。历史证明,革命不仅是崇高者的墓志铭,也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鲁迅是怀着“对庸众宣战”的心态投入革命的,这造成了鲁迅式的孤独和悲凉。鲁迅从来就不想“超出时代”,革命对于鲁迅来说,是执著于现实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