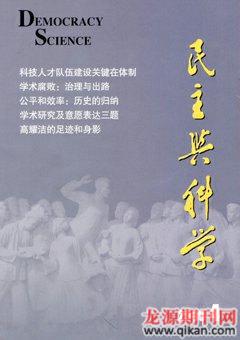序《中国医史》再版
韩启德
王吉民、伍连德两位先生撰写的《中国医史》是第一部用英文全面阐述中国医学历史成就的光辉巨著。此次上海辞书出版社要将其影印出版,我感到十分欣慰。出版社的同仁希望我写几句话,我就将自己近年来的一些思考,进行简单梳理,权作引玉之砖。
其实对医学史,我也是初窥其径。虽然从读书到工作,几十年间我都没有离开过医学领域,然而真正关注医学史,却是晚近之事。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我开始研究传染病的历史,之后对医学史兴趣日浓。通过研究医学史,我对医学的本质以及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深刻地感受到当前医学与人文日益脱离的趋势,这就更让我坚定了医学应当回归人文的理念。
古往今来,各类史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传世的医学史却寥若晨星。这大概是由于医学史的特殊性造成的,医学史难写,因为它不仅仅是医学科学和技术的历史,更是对生命、生、死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生问题的认识史;它不仅是经验的、逻辑的,同时也应是哲学的、审美的、人文的。回溯医学史,就是对医学价值的精神回归。
我始终认为,医学之目的原本是解救疾病苦难之中的人,这包括生理上的治愈和精神上的慰藉。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当人类已经能够将视角深入到细胞、分子乃至更微观的层面,征服越来越多疾病的同时,医学正与它最初的目标渐行渐远,技术的飞跃让医学拥有了独立的价值,并使这种价值不断强化,人的存在却被不断地忽略和解构。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的诘责令人振聋发聩:“人类精神方面的不健全已给社会进步造成障碍,因此也给技术进步带来障碍”,“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同样地,技术至上、忽视人文也会让现代医学进入死胡同。当冷漠取代温情,当交流变得奢侈,当诊疗成为流水线上机械的重复,医学也就蜕化成被药物和仪器所役使的工具,医患关系也随之由亲密转为紧张。
在如今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医疗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则是比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更为复杂和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如何让迷失在技术丛林中的现代医学回归人文,如何让人性和关怀重新成为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桥梁,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从医者去思索、去探究,而学习和研究医学史则是必须要做的功课,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医学的真谛,找回尘封了的对病人的爱,唤醒最初选择医生这个职业时的崇高的心灵。
对于中国医学界来说,关注医学史不能仅仅关心现代医学史,而同时应该回到祖国传统医学的源头去寻找我们的根。中华民族得以数千年繁衍昌盛,以中医为主流的传统医药功不可没。然而,有着辉煌成就的中国医药学因封建帝国与世界政治、文化的隔绝而鲜为世界医学界所了解,也因此失去了与现代医学相互促进和融合的机会。上世纪30年代,王吉民、伍连德两位前辈著述《中国医史》的初衷正是深感于中国医学在世界医学史界的缺位,而立志于向世界介绍。今天,当我们有机会重新阅读和审视这部著作时,除了慨叹前人筚路蓝缕开创的光荣,还要承担起历史交给我们的责任,那就是更深刻地了解祖国传统医学并向世界介绍,以及在当今现代化进程中,寻求中医突围、发展的方向和途径,创立新医学。
自从西医传入中国以来,关于中西医的种种辩争就不绝于耳,各方对此莫衷一是。其实,争论焦点就是对中医价值的认识。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中医,如果没有对祖国传统医学的深刻体悟,就难言扬弃。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的原理和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宇宙观、生命观、人生观一脉相承。我觉得,除了几千年积累下的医药经验和知识外,中医的价值还重要地体现在对生命的认知和医学的根本见解上。
在中医看来,生命是宇宙的一部分,生命运动和宇宙的运转遵循同样的法则。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医的理论基础,它并不意味着人被抽象和渺小化了,恰恰相反,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被扩大和提升了。生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疾病是生命自身运动的过程,而非生命的敌对方,古人有云:“生老病死,时至则行”(《因话录》卷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站在时代的潮头重估中医,我们可以看到,祖先们把医学并不当做简单的治病,而是通过对生命体的调节,使其实现平衡,达到生命状态与自然状态的协调统一,保持生命过程的和谐。这种和谐表现为人体各部分之间的和谐、人体与精神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它反映出中国人在把握人与自然关系上的高度智慧,也让医学超越于一般的经验科学,而具有了博大宽广的宇宙关怀。
中医是以人为本的。它强调医生与病人的沟通,望闻问切就是医生与病人的真诚交流和情感对话,它在诊治中也特别注意人的心理活动,关切人的内心感受,而这又与中医仁爱救人的准则始终相随。在古代中国,医术被称为“仁术”,仁者为爱人,因此,在中国传统中,尊重生命、关爱病人是医生的基本道德。最好的医生并不一定是诊疗技术最高明的,但必然具备高度的仁爱精神和高尚的道德人格。大医之道在精诚,孙思邈“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警语,就是对医生境界的精辟阐释。
不可否认的是,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两股浪潮的激荡之下,今天的中国传统医学面临着比王、伍两位先生著书时更为窘迫的境地。中国传统医学在当今医学系统中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应该沿着什么方向和途径发展,中国传统医学是在抱残守缺中沉沦,还是在融合创新中涅槃?这是《中国医史》对我们的拷问。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是善于传承和发展自己优秀的主流传统文化的。对于中医,我们应该深入地去了解它,应该对它怀有温情与敬意。我们要清楚,西医和中医的区别不是简单的新旧之别,更不是先进和落后能一言以蔽之的,它们是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差别。发展中医,并不是医学的一个流派对另一个流派的反抗和复辟,而是使相异的医学传统在交流中共同推动整个人类医学的进步。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中国医史》,上海辞书出版社影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