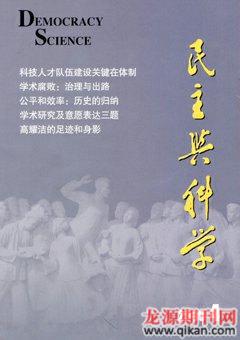思想与饭碗
杨 涛
1969年9月16日,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先生在贫困交加之中,因胃癌复发病逝于台大医院,此时,离台湾开放党禁还有18年,离台湾第一次实行政党轮换还有31年。
殷海光身后留有遗嘱一封,表达了自己心中的遗憾和对家人的愧疚,他在遗嘱中写到:对于个人生死并不足惜,否则这五年以来也不会是这个样子。所憾我有四件事:第一,我觉得很不对起我的太太,她是很好的家族出身的,她的身世和相貌,大可不必和我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我历经穷困,有时连买菜的钱都没有,我脾气又大,十几年来经历这么多艰险,受过那么多人的攻击构陷,她受尽委曲,但从无半句怨言。第二对不起孩子,不能给她更好的教育和适当的环境……
殷海光先生在遗憾中留下对家人的愧疚,事出有因。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殷海光先生可谓是贫穷潦倒,生计都难以维持,他的胃癌就是在那种穷困的生活中患上的。殷先生在给弟子张灏的信中写到:“那时我的父亲要我学医,我硬是要读哲学。父亲愤怒地说:‘你要读哲学,将来饿死了可不要怪我,现在回想起这话,差一点说中……我如今,头发如霜,现实里的一切,什么也不属于我,连基本的生存也成问题,还要学生朋友来支持,并且还要向那陌生的‘学术市场出售自己。我的心情,在某些方面,颇似晚年的陈独秀,或流亡于墨西哥的托洛茨基。”
在1949年就担任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主笔,兼《民族报》总主笔,之后在台湾大学一直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的殷海光先生,可谓才华横溢。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殷海光先生与雷震先生站在了一起,以《自由中国》杂志为阵地,评论时政,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名满全岛。如此一位学有成就的学者,晚年为何如此困窘?一切均是殷海光先生坚持自由立场,坚决捍卫自由,主张实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坚持民主与法治,要求国民党尽快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这一切显得处处与国民党作对,激起了国民党棍的极端仇视。都说鲁迅先生的骨头是最硬的,其实作为自由思想者的殷海光先生骨头同样是最硬的。1960年9月,国民党以涉嫌叛乱罪将雷震先生逮捕,《自由中国》杂志被关闭。殷海光先生挺身而出,与夏道夫、宋文明一起共同署名《〈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发表于《联合报》、《公论报》上,斥责国民党的恐怖行径,接着又发表了《我看雷震和新党》、《法律不会说话——因雷震而想起的》,为雷震先生进行辩护。自此,殷海光先生厄运不断。出版的书籍不断被查封,出门被特务盯梢,就连与世界著名学者哈耶克的见面也被阻止。
这种对殷海光先生的压迫到了殷先生晚年的时候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66年,国民党政客张其昀在中常委会上指责“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将国家长期科学委员会办得一团糟,三民主义的学者总是请不着补助金,像殷海光这样专门攻击政府的人却年年请到”。结果使得殷海光先生失去每月六十美元的“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补助金”,失去了其最低生活费的一半。紧接着,便是国民党的“教育部”来函强行要将殷先生调离台大,聘任为“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要将其收买,殷海光先生坚决拒绝这种所谓的调动,特务到其家三番五次的威胁,无奈之下,殷海光先生只好辞去了在台大的教职。至此,殷海光先生完全失去固定的生活来源,生活主要靠亲朋好友和弟子的接济。3年后,一代自由思想家,以极为凄凉的方式告别人世。
殷海光先生特别注重思想自由和思想方法的训练,著有《思想与方法》文集。殷海光先生指出自由思想要反对绝对主义、权威主义、教条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指出思想者要讲究逻辑,注重经验。殷海光先生对思想方法的注重,使他从党化教育的蒙味中解脱出来,获取了同时代思想者所不具有的远见,并具有了不断地自我否定的勇气与动力。然而,思想的方法却无法解决殷先生现实生活中穷困潦倒的问题,无法解决殷先生饭碗的问题,也就无法解决他的思想和学术生命等延续的问题。对于扼制思想者来说,最有效的方法不是组织言论来攻击、造谣,不是封杀言论,甚至还不在于搞恐怖活动在肉体上消灭,而是打碎思想者的饭碗。
如果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还是一种独裁统治,威权统治,那时他们对付思想者和异议者的主要方法还主要在于搞报刊新闻检查,用开“天窗”方法对付鲁迅先生,用特务暗杀形式对付闻一多先生。那么国民党迁台以后,统治力量进一步加强,其独裁统治在技术上开始不断“改进”,多少有向右倾极权专制转变的痕迹。在大陆统治时期,国民党要求学校开除或者交出左倾学生或者教授,学校往往予以抵制,有时国民党也无可奈何。但迁台以后,在小小岛屿,国民党对社会的控制触角开始深入方方面面,以往“教授治校”“学术独立”的传统开始被破坏,国民党更深入地控制学校的事务,安排校长的人选和插手教授的任命,对于教授的职业,独裁者开始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因此,对于思想者的控制,他们逐步延伸及思想者饭碗,打碎思想者的饭碗,殷海光先生遭遇便是一例。
不过,独霸的国民党毕竟还没有做到事无巨细地掌握岛内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分配,没有搞国家管制经济、计划经济,没有将每一个人的饭碗死死地掌握地自己手中,国民党可以打碎思想者的饭碗,但没有做到安排每一个人的饭碗,控制每一个人的饭碗。早在18世纪,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在《联邦党人文集》就写道“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而托洛茨基对于极权控制思想揭露的更为深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将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替代”。
国民党仅仅是打碎了殷先生和其他思想者的饭碗,就造成岛内万马齐喑的黑暗,那么在一个所有思想者的饭碗都被统治者控制的极权地方,思想者还有什么尊严与理想,思想还有什么火花与光芒?分配饭碗和控制饭碗远比打碎饭碗的能力恐怖。希特勒极权控制下的纳粹德国,思想者逃亡的逃亡,死亡的死亡,连海德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为保住自己的饭碗,向其东家希特勒示好,为纳粹唱赞歌,为极权张目。
思想者不怕思想被遮蔽,不怕言论受到压制,甚至对于一个思想者群体来说,可以打碎他们饭碗乃至于可以集体地分配和控制他们的饭碗,比单个思想者遭受生命的威胁更可怕。毕竟单个思想受到威胁,消灭不了其他思想者的火焰,激发其他思想者的抗议和更强烈的反抗;但是可以打碎饭碗乃至于可以集体地分配和控制他们的饭碗,思想者集体就遭到阉割,直到鸦雀无声,因为没有任何一个集体可以离开食物。一个开放的社会和市场自由的社会,即使是思想者不依附在权力身上,他仍然可以依靠写稿、讲学、从事律师行业等等自由职业来养活自己。没有饭碗的担忧,思想者才可以给那些灰暗的时代贡献光和热,而不会像殷海光先生一样,在那个孤岛上,由于贫困交加,生命之光连同思想事业一起沉寂于无边的黑暗之中。
(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