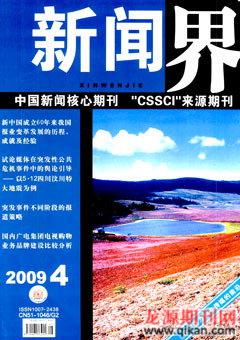论李普曼新闻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影响
胡正强
摘要本文对李普曼新闻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沃尔特·李普曼新闻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沃尔特·李普曼(1889 9.23—1974.12.14)是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政论家,也是新闻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大陆对李普曼新闻思想的了解是从1982年施拉姆的推介之后才开始的。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准确。李普曼对中国新闻学术界产生影响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新闻学术界即对李普曼有关新闻理论多有称引,且称引范围也不以《公众舆论》(《Puplic Opinion》)为限(注:1989年出版的由林珊翻译的《Puplic Opinion》中文书名为《舆论学》)。笔者现对掌握的一些资料略作排比,以初步勾稽李普曼新闻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与影响的面貌。
一
《公众舆论》是李普曼的代表性新闻理论著作。该书第一次对公众舆论做了全景式的描述,对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梳理。李普曼在书中提出的“拟态环境”与“刻板成见”的两个重要概念,比较早地论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1982年,美国传播学教授韦尔伯·施拉姆来华讲授新闻传播学时,曾把李普曼奉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并把《公众舆论》列为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作品,当年罗纳德·斯蒂尔的《李普曼传》即由于滨等人翻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
中国新闻界对李普曼的最早接触和了解确实是从《公众舆论》开始的,但时间却可上溯到20世纪20年代。1929年,汪英宾《中国报业应有之觉悟》一文中,就称引了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中“刻板成见”的相关观点。
汪英宾(1897~1971),别名省齐,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省)人。中国现代著名新闻理论家、新闻教育家。1920年9月起,在申报馆担任协理。曾由申报馆派往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进修,1924年5月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中国本土报纸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论文,获硕士学位。1924年秋末冬初,与戈公振创办上海南方大学报学系与报学专修科,任系主任。1925~1929年间,还兼任光华大学、沪江大学商学院报学系教授。一度为上海联合广告公司董事。1932~1935年先后担任《时事新报》编辑主任、总经理。1947年重返新闻界,任上海《大公报》设计委员。1950年担任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教授。1952年9月至1959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著有《美国新闻事业》、《中国报业应有之觉悟》等。他的《中国本土报纸的兴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记述“中国新闻史”的著作。
《中国报业应有之觉悟》据作者自述,其写作缘起是“环视报界之现状,有滋堪浩叹者,兹逐一讨论,期有一度之觉悟,得共谋改良之方法”、在该文的第二部分“当觉悟报业之各种问题”之“编辑问题”的“新闻采集”中,作者有如下引论:
我国报界对于采集新闻尚少根本之了解,故不惮麻烦,以采集新闻之根本意义,略加申述。在美人立浦门WalterLippmann著Puplic Opinion有曰,‘人类之脑筋,非似照片之收吸印象而已,其运用也往往创造,印象入脑中后复变淡之,或与他种印象相并,必经一番磨炼而后成各人之思想,盖一印象决不能久居浮面者,天生之诗情往往运用之使成个人之表现,(譬如罗素本是人名,然用之既久,人皆以之为一种哲学。又如武力统一为一种主义,用之既久则人皆以之代吴佩孚。)又曰,‘公众时事可于演说或报章中表现之,惟表现之时事,宜抽象于初胚,凡事物之不能见者,必难引起知之之兴趣,且公众之事闻,个人所悟到者,往往微细而不能及大要。‘故公共新闻,将成一种干燥无人愿知之者,惟具美术家描写技能者,始能以常人所不能见者,做成活动印象,使常人皆能引以为有兴味。新闻界当觉悟采集新闻之真义,进而以抽象于初胚之功夫,言人之不能言,见人之不能见,而后事半功倍矣。
汪英宾所引述的话表达了这样的基本思想: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象,这些想象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象之间的主要连接物。这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国内对李普曼《公众舆论》有关理论观点的最早介绍。
1937年5月。北平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举办第六届新闻学讨论会,围绕“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论题,诸多报界名流到会演讲。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梁士纯教授为此在《大公报》“新闻教育特刊”发表了“今日中国报界的使命”一文,该文开宗明义再次引用了李普曼的《公众舆论》一书:“列浦曼氏在他的名著《舆论》Puplic Opinion一书中,把正确的消息和公正舆论所包含的这种障碍,详加论列。属于内部的有个人的情绪和心理的形态蒙蔽着,使我们不容易领会一种真实情境。属于外界的,有言论的困难,交通的阻碍,当局的检查和统制,社会特殊势力的影响等等,都足以蒙蔽一般人的耳日,使他们不能得到真实的报告。至于所谓公正的舆论,更是一件难得的事,需要正确的消息来做基础。如果消息不正确,我们何由发挥公正的舆论呢?此外,一个人的意见往往被他所处的环境和他的利害所支配。因此种种原因公正的舆论真是一件不易得的东西。”
汪英宾与梁士纯当时都是新闻学系的教授,他们对《舆论学》一书的先后引用,从一个侧面说明李普曼该书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只是由于后来中美文化学术交流较长时间内的中断,人们仿佛遗忘了中美新闻传播学术交流过程中曾经存在过的这一具有意义的历史片段。
二
刘豁轩1939年3月在燕京大学“杂行会”一次以《怎么样看报》中,在论证“战争爆发后,第一个受伤的是真实”这个观点时,引述了李普曼一段关于新闻真实性的论述:
力普曼(Walter Lippmann)默尔(ChstlesMerz)曾对近代史上,一件大事的各种报纸记录加以研究,这件事就是一九一七年三月至一九二○年三月的俄国革命,他们在那篇研究报告的序论中说:‘大家都承认,没有真实的新闻,便不会有健全的舆论。但是在今日,对于一个争论的事件,是否能够得到正确的记录?对此,今日有一种很广泛而且日益增长的怀疑。在指摘当局腐政的时候,我们怀疑其中有不自觉的偏见。我们又怀疑某种新闻被染上了颜色,或者被搀入毒素,对于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需要证据,以下我们所研究的便是证据之一。著者自称他们的工作是‘新闻的试金石。这篇文章在一九二○年八月四日出版的《新共和》上占了四十二页的篇幅,这是对于现代战争时新闻可靠性的第一次不信任的有力表示。
这是指“《纽约世界报》社论版的李普曼和查尔斯·梅尔茨出版的一份专题报告,题为《对新闻的检验》(“A Testfor
the News”),作为1920年8月4日出版的《想共和》的附录,文中列举了美联社和《纽约时报》自1917年到1920年间对俄国事件报道的失实”一事。李普曼通过这个调查,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揭示了媒体报道受到意识形态影响而损害新闻真实性的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所谓完全客观中立的新闻报道几乎是不存在的,所有的新闻报道都会受到传播者主观倾向的左右与控制。李普曼的调查旨在抨击当时美国一些新闻媒体不尊重事实,往往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炮制新闻报道的不良行径。这一调查报告的结论因其材料翔实、论证充分、结论无可辩驳而备受人们称道,至今仍为人们常常提及和引用。
三
20世纪40年代,美国大众传媒的集中和垄断趋势日益加剧。出于对媒体所有者人数越来越少的担心,美国《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于1942年邀请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领导一群大学教授,以局外人和学者的身份探讨大众传播界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个后来以哈钦斯委员会闻名的研究班子,其成员包括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等十多名一流学者。这个委员会先后九易其稿,于1947年发表了后来被称作为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奠基的总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在该报告中就新闻界的角色提出了一些至今越来越受到肯定的重要建议。《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出版以后,虽然当时在美国学术界并没有获得一致好评,甚至其所提出的建议也受到了为数不菲的媒体及新闻从业人员的抵制,但李普曼还是独具慧眼,在该书问世之时,就撰写了《评批评者》一文,对之进行评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中央日报》1947年5月17日《报学》第20期,《中央日报》编辑武月卿即将李普曼的《评批评者》翻译过来,反映速度之迅捷和学术眼光之敏锐都令人惊叹不已。
武月卿,1941年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新闻系第10期毕业,后在《中央日报》工作,曾任《报学》双周刊的编辑,1949年赴台湾,任《中央日报·妇女与家庭》周刊主编,与林海音并称为50年代台湾文坛的“副刊双姝”,知名散文作家,著述颇丰。《中央日报》刊登《评批评者》时,文前有一“译者志”,对哈钦斯委员会作了简括介绍:“美国新闻自由调查委员会于一九四三年应报业巨子鲁斯之建议而组成,旋即开始工作,得到二百八十三人之证明,举行会议凡十七次,每次会议历时月二三日结果证明美国报业子偶目前虽无危机,然危机已潜在。该委员会已出版或即将出版之书籍达七种,并于三月廿六日发表长达二万五千字之总报告书:‘自由负责之报纸,对报界提出建议十三条,此对付妨碍发表社会所需要新闻之自由,并作互相批评于砥砺,李普曼此文即就该报之建议,加以论评。”文章署名为“李普曼作,武月卿译”,对李普曼名字的翻译已经与现在通行的译名保持一致。李普曼这篇评述性的文章,确实提出了新闻领域中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
目前事实上并没有人经常郑重的批评报纸,一本有关于苏联的书籍,出版后立到就有人作出书评;但是有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道与评论,一般而论,都没有人加以批评,若果鲁斯不承认仅有这种有来无往的批评存在的不合理——无人批评的报纸却批评其他组织与活动,那他决不会维持调查工作的经济费用:这种情形对报纸并无好处,更不保险。报纸能得到经常的批评,报纸自由才有基本的安全保障,报纸本身所主张的原则的利益均将因而失却。
因此,问题在监督监督者为谁,考查考查者为谁?巡查警察者为谁的问题。笔者猜想,委员会对于这一层也并不清楚,据称:“吾人建议报界人士作积极的互相批评。”在这一方面,他们需要新闻从业人员的劝告,然而他们错过了,他们并不讨论公众问题的辩论,因为这一方面也是够了,他们所讨论的是报人批评的问题。
我们大家都会受益惑,有时不免有纵容的事,但是一般而论,时常保持缄默,自然有充分的理由,律师,医生、演员、教授之所以鲜有公开声言律师辩护不行、医生诊断不内行、演员表演蹩脚,教授授课沉闷,就是这个原因。新闻从业人员和其他技术于职业一般无二,他们也有同业的关系:新闻从业人员不能闭门独处,他们彼此要见面,聚会,要共同工作,倘若彼此作剧烈的公开批评,结果势必不能相容。我可以说,我自己曾经作过这样的尝试,也曾使人对我自己作过尝试,我所得到的结论是所得不偿所失;因为有此而引起的不快感情远过于所得到的公益。
报纸相互间实无法作公开的批评,因此,公正的批评应发自胡琼士君一类的旁观者,因为要作公正的批评,有撇开私人关系的必要。世界报老编者柯白说过,剧评者不应该于演员交往,尤其是女演员,政治评论者如果于政治家常常见面,结果本身也成了政治家,金融评论者也一样成了金融家。
为报业本身利益计,积极批评报纸实有必要,然批评报纸须出自报界以外人士,几愿从事批评报纸工作者,都可以从胡琼士的报告中得到入门途径。
以监督政府、批评社会为己任的报纸,也应该接受批评,不然,报纸存在的合法性将因此而消失,但由谁来批评报纸确实是一个颇费周折的问题,让报纸在内部进行自我批评,似乎无法达到令人满意和信服的效果,因为新闻从业人员也于其他行业的人一样,也有同业的人情面子,也会自我包庇,形成某种权力共谋。李普曼据此论证了由来自报界以外的成员组成的哈钦斯委员会存在的必要性,这是一个极具远见卓识而又需要勇气的观点。因为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出版以后,便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如《芝加哥论坛报》的麦考密克声称他根本不屑于花时间来读这个不堪人眼的报告;《星期六评论》则载文嘲讽报告犹如“老鼠般的唧唧喳喳”。连花了20万美元支持这一调查的卢斯也难以接受,指责该报告甚至连“高中水平的逻辑都不具备”。历史证明:李普曼的思考和观点具有多么强大的时空穿越力量!这也是本文不厌其烦地对《评批评者》一文洋加征引的原因。
以上几个简短的历史片段无法固然复原李普曼对中国早期新闻传播学界产生影响的全貌,而且当时关于李普曼的译名也还没有统一,立浦门、列浦曼、力普曼、李普曼等译名同时使用,显得杂乱无章,接触之始常让人感觉一头雾水,不免限制了李普曼新闻思想的传播广度和影响力度。但管斑窥豹,仍能让我们依稀感受到我国新闻传播学理论建构中的美国因素,并进一步加深对中美文化和新闻学术交流史、李普曼新闻思想对中国现代新闻界的影响等相关问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