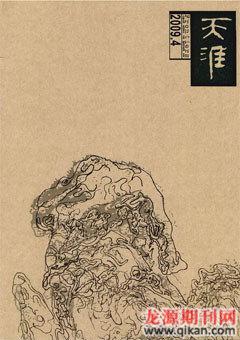英雄传奇、历史记忆与时代解读
新革命历史剧热播
新世纪以来,作为大众文化载体的电视剧,经常成为当下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2002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2005年是《亮剑》,2006年是《暗算》,2007年是《士兵突击》,2008年开春热播剧是《闯关东》,在此期间热播的相关电视剧,还有2003年播出的《军歌嘹亮》、2004年播出的《军人机密》、《历史的天空》和2007年播出的《狼毒花》。有趣的是,这些电视剧一般先在地方台播放,获得口碑之后(《士兵突击》的口碑最先来自网络),再进入卫星台或登上央视,进而席卷全国(《亮剑》、《闯关东》除外)。其中“激情燃烧的岁月”、“逢战必亮剑,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亮剑精神、“不抛弃、不放弃”的钢七连精神以及“闯关东精神”成为当年或当下的流行语。这说明这些电视剧并非市场预期的热门剧,但却在各地方台播映的过程中,赢得观众的广泛认可。这是近几年来超女比赛开启的选秀式栏目所引起的社会轰动效应之外,电视媒体所制造的最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难怪《新周刊》使用“没有电视只有剧”来点评2007年中国电视节目榜。上面所罗列这几部最热播的剧,并不是同一类型的电视剧,但无一例外都属于现当代题材的国产剧,从类型上大致涉及军事革命剧、涉案剧(反特剧)、传奇剧等(电视剧一般会重叠两三种类型),与1990年代末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热播的宫(清)廷戏以及韩剧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些电视剧大多属于现当代历史剧,如果把《闯关东》和《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连接起来,就可以构成一部贯穿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剧目。这些电视剧把传奇式的人物与现当代的历史变迁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带有英雄史诗的色彩,或被称之为“新英雄主义”(也称为“新传奇英雄”)。借用一篇报道中的描述,这些传奇英雄都是“草莽出身,投身行伍,娶了一个‘小资情调的革命女青年,引发诸多家庭矛盾,‘文革遭难、复出……从《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到《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再到《亮剑》中的李云龙,当红色经典翻拍剧屡遭滑铁卢时,将主旋律‘另类了一把的红色原创剧却为我们开创了一个荧屏‘新英雄主义时代”(《你拼你的绝活,我找我的娱乐》,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12日)。这些革命军事剧让人们联想起1950-197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多重意义上的改写,但基本上可以把这些电视剧作为对革命历史小说的新版本或“后革命”版本,因此,又被称之为“新革命历史剧”。
这种对革命历史故事的成功讲述本身已经涉及到中国当代文化史内部的一个重要问题,新时期以来,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方案,是建立在对“文革”十年的彻底否定以及对广义的革命文化的拒绝为前提的。这就造成现实生活与历史讲述之间的脱节,或者说以革命历史所支撑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及政党合法性与人们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存在错位,以至于官方意识形态在很长一段时间无法询唤人们的主体位置。1950-197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尤其是发展到极端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在新时期开启处已经被宣告为失败,这种革命历史故事的讲述也成为一种谎言,或简单地说所谓“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不再被观众所接受。1980年代中期以来所形成的主旋律、商业、艺术“三分天下”的艺术创作格局,已经说明主旋律自身无法统领意识形态的困境。1980年代后期,一批被称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作品把革命历史、理想、信念或信仰作为消解的对象,其基本策略在于把革命历史偶然化、庸俗化,非崇高化、“去革命化”,比如《红高粱》、《白鹿原》等作品,在这种“去革命化”的历史叙述中,革命历史中的英雄由为国为民为党的道德典范变成具有传奇色彩的性欲旺盛的血性汉子。经历八十年代末风波之后,这种被强化的官方意识形态更处在悬置状态,而伴随着1993年大众文化全面勃兴,官方意识形态能否在大众文化中获得领导权,就成为重塑主流意识形态的关键标尺,但是那些在红头文件保障下的主旋律作品很难获得市场的认可。而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借助红色经典的改编,红色经典中的英雄形象开始浮现,到了新世纪以来红色经典被大面积改编的时刻,往往通过增加感情戏或个人化的欲望动机等方式消解英雄形象。直到2002年《激情燃烧的岁月》出人意料地获得好评和轮番热播,石光荣式的英雄形象开始出现,一种新的讲述革命历史的叙述方式才被确立下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激情燃烧的岁月》所开启的对革命历史故事的讲述,使革命历史重新进入人们的历史记忆,尤其是到了《亮剑》,一种借重抗日叙述来重塑国家神话的讲述获得可能。革命与当下生活之间曾经存在的深刻矛盾或异质性被消化,革命“激情”以遗产而不是债务的形态被观众所接受或消费。因此,这种对革命历史的再叙述,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于,把曾经异质化的革命历史,尤其是1940-1950年代的国共之争和1970年代左右的“文革”历史,以非异质的方式连缀起来。这些新革命历史作品与1980年代对于1950-1970年代广义的革命文化的拒绝不同(如1980年代把“文革”/革命叙述为封建主义专制、恶魔,进而在“告别革命”的意识下否定一切革命文艺实践),也与红色怀旧中对革命的浪漫化想象不同,这种正面的英雄形象如同历史结点,或过滤器,成功地使对当下主流意识形态有危害的“污垢”(比如以阶级为核心的阶级斗争的革命)沉淀掉,并借助“英雄传奇”得以把曾经无法讲述的革命历史缝合进断裂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这成为这些电视剧所具有的时代症候性。
由《激情燃烧的岁月》所开启的革命历史剧开始热播于荧屏,对于1950-1970年代的历史,人们似乎找到一种可以接受和怀念的切合点,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与新历史小说、红色经典不同,这些新的革命历史剧不只是在消解英雄,而是重建一种英雄与革命历史的讲述。《激情燃烧的岁月》这部剧塑造了军人石光荣的形象,但是这个形象与革命历史题材叙述的英雄并不相同。石光荣虽然是一位戎马生涯的革命军人,立有赫赫战功,但剧中并不是在战场上展现石光荣的英雄主义,而是抗美援朝之后英雄解甲归田的儿女情长,或者说,通过家庭生活或日常生活来填补或修正革命历史中的大历史。但是石光荣个性鲜明的形象,却成为此后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所塑造的英雄人物的共同特征。石光荣身上具有正反两面的特点,正面:因为是军人(男人),所以具有卓越的指挥才能,勇敢杀敌,不怕死;负面:因为出身农村,所以没有文化、不讲卫生、说话粗鲁。因此,石光荣既带有土匪、土老冒、泥腿子的土气,又是不屈服、能打胜仗的有血性的男儿,这成为此后《亮剑》中的李云龙、《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狼毒花》中的常发所具有的
基本性格,与石光荣不同的是,后者不是一般的军人,而是更具体为抗日的民族英雄。如果仔细比较以下这些电视剧的核心情节,具有相当多的重叠之处。这些形象成功地吸纳了新历史小说以及红色经典改编中对英雄的改造。一个有趣的文学事实是,《狼毒花》的原版小说《酒神》是权延赤1986年写作后发表在《深圳青年》上的,因此,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新历史小说有更多的相似之处,比如使用“我”的视角来写父辈的故事、自叙特征明显、有意制造传奇故事与官方叙述之间的错位等,但是原小说中常发的匪气以及打仗的传奇性很容易就被改编成李云龙式的英雄。可以说,《亮剑》、《历史的天空》中土匪式的英雄更多地受到新历史小说的影响,尽管英雄传奇在1950-198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中也是重要的类型,但经过新历史小说的改写,这些英雄形象的匪气和草莽气息更为突显,以至于这种形象成为男性英雄的内在特征。
在这些新英雄传奇故事中,改写最大的是英雄成长的模式,如果说在革命历史小说中,英雄在领路人傍蒙者的启发下把善/恶、好,坏的民间逻辑上转化为政治信仰、革命逻辑,如《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吕梁英雄传》等,那么这些新的革命历史剧则采取正好与之相反的策略,是把政治信仰、革命逻辑还原为民间逻辑,正如《历史的天空》中,姜大牙与杨司令的关系,是杨司令不断地把思想觉悟、纪律观念、政治觉悟、信仰教育、《共产党宣言》、革命的性质、纲领和目的以及共产主义理想等属于革命的大道理还原为姜大牙能够明白的岳飞、文天祥、《飞云浦》中武松杀张中监等戏文里的故事(电视剧中,杨司令的扮演者是李雪健,曾批评姜大牙说,不要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想象成宋江和李逵的关系)。而更有趣的是,如果说作为革命历史小说,英雄最重要的成人礼是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为党、人民、国家而献身,牺牲小我融入到大我之中等等,而在这些电视剧中,可以说,这些民族英雄基本上没有经历什么成长,抗日、不当汉奸是他们天生的底色,而所谓成长,更多地体现在学习文化上,这就涉及到这些英雄最重要的特征,出身农民和没有文化,以至于退休后的石光荣要在自家院子里种地以消磨时光。这种农民出身的军人形象固然与中共的历史有关,选择农民,或许并非偶然,农民在共产党的“阶级”表述中处在暧昧的位置,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始终与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之间存在错位。因此,工农联盟、“工农兵”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践的“本土化”表述,而在这里选择农民作为传奇英雄的底色,恐怕还与革命文化中工农与知识分子的对立与冲突有关,尤其是在1980年代以来的反右叙述中,知识分子基本上成为革命文化唯一的受难者,把共产党的革命等于农民翻身的叙述成为反右叙述的基本支撑点。因此,这些新革命历史剧中的英雄就具有达成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和解的功能,而这些电视剧中一个重要的戏剧性元素是妻子把这些没有文化的将军改造成有文化的、讲卫生的。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石光荣与褚琴的争吵是泥腿子与小资产阶级的女文艺青年之间的矛盾,但他们毕竟能相互携手走过“激情燃烧”的一生;《历史的天空》中姜大牙在政委的调教下逐渐改调了自己粗俗的性格,并拔掉了“爱情的牙齿”,改名为姜必达;《亮剑》中李云龙与书香门第的妻子田雨在新婚之夜共同研墨写作了一首夫妻恩爱的《我依词》,而李云龙与赵刚政委(九·一二运动的参与者、燕京大学的高材生)之间是珠联璧合、相互赏识,小说版的李云龙最后在赵刚的影响下,成为挺身对抗国家机器的悲剧英雄。这诸种白头偕老的场景与1980年代初期讲述革命干部与年轻妻子的悲剧不同,这些出身农民的英雄人物具有化解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冲突的调解作用。另外,这些作品也借鉴了新历史小说中关于历史的偶然性的解释,像《历史的天空》、《狼毒花》等历史剧中,参加革命的过程被书写为历史的偶然或阴差阳错。如《历史的天空》中姜大牙本来要投靠国民党,因为听说国军有饷银能当官,却误入了新四军,并被一位女政委所吸引而留下打鬼子,与此相反,姜大牙的同乡青年才子陈墨涵原本要投靠新四军搞革命,反而误入国军,被拉了壮丁。
缝合历史记忆的方式
如果说这些英雄形象削弱了其革命色彩,而更像传奇英雄或侠客、义士,所谓“乱世出英雄”,但是他们所经历的历史毕竟是二十世纪最惊心动魄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在告别革命的叙述中往往作为负面债务而被剪辑掉,而这些新的革命历史剧又使革命历史重新浮现出来,那么这被重新唤起的历史记忆又是如何被讲述的呢?或者说,他们如何串联起二十世纪最纷繁复杂的历史以使革命历史与当下生活和谐起来呢?
简单地说,有两种不同的缝合历史记忆的策略,一种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包括《军歌嘹亮》)这种革命家庭言情剧,以家庭的连续性来保证历史的连续,正如评论者所说该剧“相当有意识地分辨了哪些历史是可写的,哪些历史是不可写的。它以一个家庭的成员三十七年的遭遇串联起了当代历史中所有的辉煌时刻,并以家庭的内在连续性缝合起历史,从而使这份‘激情穿越了裂隙重重的当代史,并营造了一副别样的、连续的当代史景观”(贺桂梅:《历史的幽灵——<激情燃烧的岁月>与红色怀旧》),这种书写策略与2007年热播的《金婚》有某种相似的地方,两者都以家庭为线索串联起四五十年的历史。与《激情燃烧的岁月》因石光荣的特权地位而与诸多历史事件擦肩而过不同,《金婚》则以都市普通职工的生活把波澜壮阔的历史排除在家庭之外,与关于1950-1970年代的书写中常见的关于知识分子蒙难(反右叙述)或普通人成为历史的人质(《蓝风筝》、《霸王别姬》、《活着》)的叙述不同(相比《蓝风筝》,在《金婚》中,历史就如同从来都没有发生过)。1980年代以来,日常生活、个人生活具有某种道德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建立在对1950-1970年代国家、革命对个体、家庭的迫害的批判之上,而这种使用家长里短、日常生活来填充“激情燃烧”的生活的叙述无疑修正了这种迫害的表述,如同情景喜剧,历史虽如年轮般过了一年又一年(《金婚》正好使用的是编年体),但除了岁月的增长以及室内布景的变迁,历史或者说革命历史似乎从来不曾改造或光顾这些“核心家庭”,这种家庭、个体与历史尤其是宏大历史的疏离感,恰恰是当下意识形态的有效组成部分。
第二种串联历史的方式与《激情燃烧的岁月》不同,《亮剑》等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在试图跨越1940年代到1950年代的断裂以及1950-1970历史中“文革”或日革命的异质性。具体来说,一是在抗日战争中淡化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争论;二是把1950-1970年代中的政治斗争尤其是“文革”的历史,或转变为一种心胸狭小的小人物得势的历史(如《历史的天空》),或是老干部蒙难(《军
人机密》)、自杀的历史(《亮剑》小说版),这基本上是两种超越冷战逻辑的历史叙述,而且在1980年代已经出现,尤其是“文革”作为知识分子受难记的描述已经成为某种叙述惯例,即使这样,电视剧《亮剑》出于审查的考虑也没有拍摄这段历史。
或许不无偶然,这些革命历史剧中,抗日战争被格外突显出来。无论是篇幅还是书写重点,这些军旅题材的电视剧都把抗日战争作为英雄登临历史的重要舞台,因此,这里的英雄无疑是抗战英雄,是国家和民族英雄,正如《亮剑》中“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台词被共军(我)、国军(友)和日军(敌)三方彼此惺惺相惜的将领所共享(见《亮剑》中的八路军李云龙、国军楚云飞、日军山本一木),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式的“敌我友”的和解成为后冷战时代穿越冷战意识形态的重要表征。抗日战争成为主人公大展风采的战场,与2005年作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有关,但是,把抗日战争作为这些军人建功立业的主要战场依然是意味深长的。抗日战争在官方叙述中存在着暧昧性,因为作为民族之战的抗日战争,毕竟与共产党以阶级为意识形态核心的表述之间存在错位,当然也恰恰是这个时期,共产党在毛泽东的论述中完成了“本土化”,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共产党。国共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也隐而不见,一个有趣的遗忘是,在这些开始于1937年或1940年的叙述中,无论是《历史的天空》中的新四军,还是《亮剑》中的八路军,对发生于1941年“兄弟阋于墙”的皖南事变都讳莫如深,只字未提,反而是国共两党中各有英雄惺惺相惜(《历史的天空》中八路军是姜大牙,国军是79团团长石云彪和参谋陈默涵;《亮剑》则是李云龙与楚云飞,最动人的场景是,小说《亮剑》的结尾,李云龙在“文革”中开枪自杀,海峡对岸的楚云飞为其广播悼词),甚至与日军将领也彼此致敬,因为彼此都是职业军人,打仗不过是各从其主(国家),如果没有战争,敌人也可以成为好朋友。如果说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之战的话,那么解放战争就变得比较暧昧了。在《亮剑》中,在女儿与作为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的父母商量与李云龙的婚事时,争论之一就是李云龙究竟是一党一派的英雄,还是抗日战场上的民族英雄?在《历史的天空》中,国军将领79团团长石云彪为避免与共产党的内战而选择与日作战时战死,更有趣的是,《历史的天空》中共产党内部的路线派系斗争,远远超过国共之间的对立,不懂军事的政委江古碑借纯洁运动(暗指“整风运动”),把情敌姜大牙关进监狱,这为解释其“文革”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因此,对于“文革”的叙述,在《历史的天空》中就变成了一场小人得志的阴谋剧,从1940年代的纯洁运动到“文革”中的造反派运动,姜大牙的遭遇,都是一个心胸狭窄的政工干部江古碑的所为。与此相比,《亮剑》小说版要更复杂些。尽管《亮剑》电视剧版结束于1955年,但主要人物丁伟、岳父、赵刚等对前苏联威胁的预言以及对国内特权阶层的批判,已经暗示了各自的历史命运。《亮剑》小说版中,李云龙在经历了岳父劳改致死(因批评国家没有法治、言论自由在1956年定性为极右分子)、丁伟被捕(1959年为彭德怀辩护)、赵刚学习俄国十二月党人而自我流放(为罗瑞卿辩护)之后,也陷入了矛盾之中,终于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占领了某师部,李云龙在保护国家安全还是镇压造反派之间选择了前者,成为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当造反派群众去李云龙家抗议亲属被杀时,李云龙开始内疚于自己的行为,陷入极度悖论之中:“群众响应领袖的号召起来造反,又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捍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老百姓本来挺安分的,没打算造反,是党让他们造反的,听党的话这好像也没错。而军队也没错,军队的职责是保卫国家,维护社会安定,在遭到武装攻击时必然要还击。那么,谁都没错,错在谁呢?”革命/反革命的二元对立逻辑无法为李云龙提供恰当的解释,这种叙述不同于1980年代以来关于“文革”已取得共识的典型叙述:“法西斯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人性、传统和美德都要毁于一旦,它造成的破坏力和恶劣影响绝不是几十年能够恢复的,它是幽灵,是瘟疫,是噩梦,历史会永远诅咒它”(李云龙的妻子田雨的话),呈现了“文革”历史的某种复杂状态,不过,狱中的李云龙终于明白了人性的价值,对待敌人也要人道,暴力来自兽性和邪恶的心灵,这种悖论和复杂性最终还是整合在人道主义的话语之中。
另外,在这些文本中,一种超越冷战意识形态的方式,却也呈现了冷战历史在中国的特殊状态。中国在冷战历史中处在一种比较暧昧的位置上,可以说中国在冷战的逻辑里面——从建国初外交上一边倒向前苏联到1960年代初期中苏交恶,同时又在冷战之外或试图超越冷战的逻辑——从六十年代的反帝、反修到七十年代初期与美国建交,这种特殊的位置,使这些文本中把前苏联而不是美国作为国家的敌人,如《亮剑》中丁伟在1955年从国土安全的角度把前苏联作为中国未来的敌人,再如小说《暗算》也是以前苏联为假想敌。而作为这些历史叙述的终结点1980年代,非常自觉地选择了与美国的和解,如《历史的天空》结束于中美军事交流,小说《亮剑》把历史的大和解设定于阿波罗11号登月飞行,作者动情地写道“在这个躁动的、喧嚣的,充满暴力、鲜血和争斗的地球上,各种不同肤色、不同政治信仰的人群都暂时停止了争吵和厮杀,全人类都怀着庄严肃穆的情感迎接这伟大的新纪元,这是人类的骄傲,人类的希望。……在这伟大的时刻,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响起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中那辉煌的第四乐章。那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大合唱《欢乐颂》,把全人类的情感都推向了极致”,只是阿波罗登月发生在1969年,中国还在“文革”之中也在中美建交之前,显然无法分享这份“人类的情感”。
无论是在抗战背景下的国共和解,还是李云龙所认同的人道主义叙述,还是选择与美国的和解作为历史的终结点,这些新革命历史剧的历史表述超越了冷战意识形态中对立的双方,但这种历史表述在1980年代初期已经出现,只是在这些电视剧中更突显了超越国共意识形态之争的叙述。
重塑国家与民族神话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可以看出,支撑这些英雄形象的历史动力,是民族英雄的正义性,而作为民族之战的抗日战争也是一场国家之战,因此,这些历史讲述所重塑或唤起的恰恰是一种国家神话。有趣的是,2008年年初的一部热播剧是《闯关东》,正好讲述了清末到抗日战争时期,一位参加过义和团的拳民朱开山逃到关外,带领一家人在东北落户生根并兴旺发达的历史。这部剧采用了新历史小说中常见的家族史的方式来讲述历史,这段白手起家的发家史被称为“底层英雄的史诗”和“中华民族精神”,
最后家族的兴旺维系在与日本人对煤矿的争夺上,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就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了,正如朱开山的豪言壮语“只要国家不亡,我们老朱家就不会亡”,家与国的叙述顺利地耦合在一起,阶级冲突恰当地消弭于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作为主角的朱开山,也是一位具有民间道德的传奇英雄,《新周刊》的评价是“他集仁义礼智信于一身,商业头脑、大智大勇、手足情谊、朋友义气、民族大义样样俱全。他的经历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观,从一无所有、白手起家拼搏为一方富豪,身份则兼具地主、商人、矿主、爱国者、资本家、血亲宗族掌舵人、现代企业领导者……他是旧中国男人所有正面形象的集合,囊括了中国民间史诗的所有元素,是中国观众对传奇英雄的普遍幻想”。如果把《闯关东》读作这些革命历史电视剧的前传,这种英雄传奇的“谱”系就更加完整,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就成为“中国人”艰苦奋斗、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民族发展的历史。而在大量热播的反特剧中,所涉及的也是国族身份的认同,《暗算》对国家主义的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叙述扭转了1980年代以来建立在个人主义上的对国家的批判。
与此相似,在每年一度的年度经济人物评选的颁奖晚会中,获奖企业家似乎只能选择一种民族企业、中国企业的身份来界定自身的位置。这种民族英雄、国家英雄的重塑,很必然地是一种男性传奇的故事,这是否说明1980年代以来伴随着以经济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一种男权中心的文化已经重建完成,还是“大国崛起”的内在需要?正如前面已经提到,对于国族神话的重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已经出现,成为应对意识形态危机的有力方式,而当下为什么如此强烈地需要这样一种国家神话呢?恐怕与国家体制本身的转型有关。新时期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中后期,共产党不断调整自我定位,以弥合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巨大裂隙。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执政为民等一系列表述,共产党由一个革命党转型为相对“中性”的执政党,尽管党政一体的国家体制并没根本改变,但是党与国家的关系转变为管理国家、为民执政,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新的合法性资源。去革命化的工作还具体体现在国家职能部门的转变上,比如革命历史博物馆变成国家博物馆、国家大剧院的成立以及在地方党政领导中压缩党委的职位,这些都内在地需要一种关于国家故事的讲述,一种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历史的重温。这种对革命历史的重新改写,使得讲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大国崛起”的民族/国家的大故事获得内在支撑,或者说无论是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是经过艰难曲折寻求现代化成功的历史,都需要一种把1950-1970年代的历史中获得主导和霸权位置的革命文化改写成为国家/民族神话的方式。
新的时代解读
这些革命历史剧以种种方式抹平革命历史中的异质性而达成某种和解,可是对于观众来说,这些革命历史剧以什么方式与他们发生连接的呢?或者说,在这些电视剧中,观众究竟认同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后革命或冷战结束的时代,诸如历史、国族身份对于每个个体来说,这些电视剧真的能询唤出这些身份吗?或者说电视剧毕竟是在家居环境中来观看的娱乐品,如果能够打动观众,似乎还有比历史记忆、国族神话这些宏大话语更为切近的理由。因此,与上面的分析不同,在观众看来,石光荣、李云龙、常发等不守规矩、经常违背上级命令、但却能屡建其功的英雄与其说是民族/国家英雄,不如说是这个时代最成功的CEO,李云龙挂在嘴边的话,打仗永远不吃亏的生意经,也早被人们看成是这个时代最有商业头脑的职业经理人。
相比《军歌嘹亮》、《军人机密》、《历史的天空》,《激情燃烧的岁月》和《亮剑》更为热播的原因,或许因为这两部剧提供了两种更有效的与当下嫁接的方式,前者达到了“在一个市场化的环境下,它再次证明了理想的价值和激情的含义”,这或许是这个功利主义时代最缺乏的东西,因此,需要“从上世纪下载激情”,后者则贡献了“亮剑”精神,按照李云龙的说法:“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深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简单地说,亮剑精神就是明知失败也要勇往直前的精神,这种精神很快被成功地转化为团队精神、职业培训和励志教育,比如已经有“亮剑拓展培训中心”成立。“亮剑”已成为流行语被挪用到各个领域。同样,《闯关东》中的闯关东精神,《士兵突击》中的“不抛弃、不放弃”也可以为人们在市场经济中挣扎、竞争获得某种想象性表述。
另外一种与当下观众更为契合的意识形态表述是关于成功与失败的故事,正如这些新革命历史剧中的英雄们,一方面他们的成功与国家、民族利益有关;另一方面这种获得成功的方式更多的是他们个人的努力和聪明才智。而不再是为人民、为革命事业,这与电视剧中所反复突显的对职业伦理的高扬有关。正如上面提到,这种职业军人的理念本身在于消弭敌我双方的意识形态之争,常发被认为是“对工作比对家庭用心,对同事比对亲人细腻。他们要慈祥有慈祥,要威严就很威严,永远在以自身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对撞”的典型。而另外一部电视剧《士兵突击》更能凸显这种成功与失败的逻辑,这虽然是一部军旅剧,但更像《奋斗》这些励志题材的青春剧。作为普通士兵许三多,需要的不是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而是在部队的一个又一个的比赛和考验中脱颖而出。在经历了新兵连、场站训练场、钢七连、特种大队等一系列PK比赛,许三多最终获得了胜利,成为“兵工”特种兵,而这种胜利被归结为一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即不抛弃理想,不放弃战友,这成为每一场PK比赛中赢家的逻辑。这部电视剧与诸多电视台的PK比赛充当着相似的意识形态功能,就是在比赛或游戏中,明白胜利与失败的道理,而不去质疑比赛或游戏本身的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热播的创业栏目《赢在中国》或许更凸显这种赢者何以为赢、输者何以为输的市场逻辑或现实逻辑,因为评委都是这个时代的最成功者:蒙牛集团总裁牛根生、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脑白金神话史玉柱等,赢者的位置是确定的,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再加上一部古装剧,或许更能说明这个时代为何如此需要讲述赢与输的故事,在《神探狄仁杰》(第三部)“黑衣社”故事的结尾处,狄仁杰终于揭穿了由年轻女子组成的黑衣玉女军的阴谋之后(木兰从军的故事变成了恐怖分子——女性对抗社会),黑衣社的头领小桃说“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公平和仁慈可言,是非功过只有胜利者才有资格评判”,而狄仁杰的回答是“所以你们永远也不会成为胜利者”。从这些种种成功与失败的案例中,观众找寻着自己何以失败的原因,并心悦诚服地认可这种成功的逻辑,尽管只有成功者才有机会讲述成功的故事。因此,恰如一篇报道中指出:“‘二战以来,美国最著名的三所军校:西点军校、海军学院和空军学院,已经培养了1531位500强级首席执行官、2012位公司总裁、五千多位副总裁,以及数以千计小公司企业家。美国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以及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曾被问及同一个问题:在培养领导者方面,谁做得最好?他们的答案既不是哈佛商学院,也不是通用电气,而是美国军队。”也许石光荣、李云龙、常发、许三多就是“军队”这个商业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吧。
张慧瑜,学者,现居北京,曾发表论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