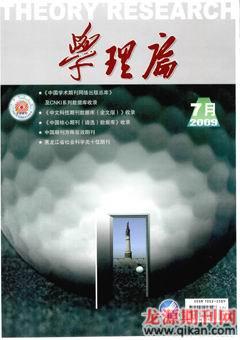“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当代诠释
卞 康
摘 要: 孔子认为大多数人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犯上作乱、“放于利而行”的人都是“喻于利”的小人,需要付与献身精神“喻于义”的君子占据统治地位以制服他们,从而达到恢复周礼的目标。孔子关于社会需要担当道义的精英和大多数人由自身利益出发走向道义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
关键词: 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義;孔子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7-0177-02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 ·里仁》,以下只注篇名)是人们谈论孔子义利观常引用的话,一般解释为君子关注道义、追求道义通达,小人关注利益、惟利是图。还有人说这是孔子对剥削阶级的美化和对劳动人民的污蔑,因而持绝对否定态度。笔者认为,这些说法虽不无根据但都失之简单,故作一深入探讨。
孔子视野中经常喻于利的小人
“喻于利”是指自身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成为行为动机的基本出发点。不过,孔子讲“喻于利”并非一般地讲人的趋利,而是讲那种突破统治集团的义的规范肆意妄行的趋利。以当代视角审视,孔子所讲的“喻于利”又有两种情况:
第一,广大劳动群众都是“喻于利”的。作为被剥削压迫的对象,广大群众对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义的原则不可能采取积极支持认真遵循的态度;作为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管理活动之外的社会群体,一般群众缺乏充分了解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协调处理基本情况的条件,更不可能对统治阶级提出的义的道德原则有深刻的把握,从而决定他们不可能采取超越一般直接利害的社会道义标准来支配自己的行动;贫困境遇、现实生存压力更使大多数人只能以自身直接利害来判断是非善恶;在各种关于义的主张莫衷一是争论的社会背景下,广大群众虽然也有自己关于义的是非观念,但处于高度分散状态、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他们没有机会形成系统共识并以自己的义去与统治者义的主张抗衡,更不可能使自己的主张上升到社会舆论的主导地位,所以其主张的义就不可能以抽象的道德意识形态形式而只能以与日常争取自身利益活动的形式来表现。只有在农民起义中下层群众才有可能明确地提出“等富贵,均贫富”那样义的原则,这种时候他们也同样能自觉地做到以阶级大义为重并义无返顾。对于这种实现另一种义的主张,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孔子当然不可能认同,所以其基本判断就只能是“小人喻于利”。
第二,统治阶级内部犯上作乱者和“放于利而行”(《里仁》)的成员更是“喻于利”的。如果说孔子对前一种小人“喻于利”还能表示某种宽容和理解的话,那么对后一种人则是无比痛恨和毫不留情的。孔子生于奴隶制开始崩溃、封建制开始兴起的春秋末年,他耳闻目睹了臣弑君、子杀父、“礼崩乐坏”、“邪说暴行”不断发生的现实,站在奴隶主贵族立场上,他把发生原因主要归结为统治集团内部人们突破周礼即传统等级制、分封制、世袭制约束私欲的膨胀。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孔子的一生,就是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奋斗的一生。他认为要恢复周礼,主要靠成功地超越了自身私欲而“喻于义”的君子壮大力量去制服那些拥有一定实力和地位、原先就是奴隶主阶级统治集团成员又“喻于利”的小人。在一定意义上,孔子的看法并不错,因为历史上封建制取代奴隶制,虽然根本原因是生产力发展和奴隶们的反抗斗争,但领导这个变革得以实现的新兴地主阶级成员决不是胸怀进步理想并勇于献身的志士仁人,而是利欲熏心的势利小人,至少从整体看不能不是如此。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①
孔子心目中应当喻于义的君子
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②剥削阶级及其成员当然也不例外。与后来极端重义轻利的儒家后学不同,孔子并不讳言包括物质利益在内的利益。其一,孔子把富民放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把给人民带来富裕看作道德教化的前提。其二,孔子将能不能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作为评判政治得失的基本标准。子贡说:“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孔子回答:“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其三,孔子还直言对富裕生活的渴望:“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然而,孔子又清醒地认识到基于统治阶级物质利益需要的义的需要。“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可见,孔子重视利益但主张要“喻于义”,而不能简单地“喻于利”,他要求站在统治阶级根本和长远利益的立场考虑问题:“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季氏》)
按照孔子的观点,在乱世中要维护和保障整体、根本、长远的利益,统治阶级最需要的是能担当其道义的主体,即能超越“喻于利”而“喻于义”的君子。君子的道义担当,如果归结起来又有两方面内容:一是选择、诠释、捍卫义并以那义为标准实际处地理各种利益关系,二是身体力行地做践行义的表率。“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孔子一生向学,就是希望能成为“喻于义”并实际担当统治阶级道义的君子;四处游说,就是为了寻找占据当权地位并具有这种政治觉悟的君子;开办私学,就是为了培养这样的君子。孔子认为君子应当“以义为质”(《卫灵公》),具有统治阶级道义担当的觉悟:“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并且,他对君子控制局面和道德表率的作用充满信心:“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孔子强调,为担当道义,君子应准备承受普遍的不解和常人难以应对的困顿:“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 他还树立了一个合格君子榜样的颜渊:“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在此同时,孔子也非常讲实际,他告诉学生做君子并不总要一味苦行,反倒能够获得更大利益上的满足:“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
按孔子论断,可将人回应义利归为四种境界:其一,“放于利而行”(《里仁》)。这种境界着眼于物对自身的有用性来决定取舍,是发自趋利本能的决定方式。其二,利义综合判断。即不仅着眼于物的有用性,而且考虑争取它可能产生的对自身利害全面性的后果,如果争取它可能遭到制裁或遭到非议以至舆论谴责继而更大程度损害自己的利益,也会放弃或改变自己的行为。“小人喻于利”指的就是大多数人面对利益作出决定通常处于前两种境界。其中第二种境界是先考虑利,再考虑义可能对利造成什么实际影响从而被动地服从义,虽然道德境界不高,但毕竟还是由利走向了义。其三,“见利思义”(《宪问》)。面对利的诱惑能够自觉地以社会道义衡量,无条件地遵循道义做合乎道义的事情,如此就对义的态度讲已经达到君子的境界了,然而这种人还不是孔子心目中完全意义上的君子。追求达到这个境界,不过是为后来提升到最高境界创造自身的道德人格条件。其四,见义勇为。孔子注重君子道德人格的培养,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为了敦风化俗,不是为道德而道德,而是为了恢复周礼。道德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具体地说,孔子认为需要有一小批真正意义的社会精英,他们通过自身长期的道德人格修养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靠强大的道德人格魅力,既争取民众的人心更争取当权者的人心,从而最终掌握到政治统治的权力,再以此为杠杆重新建立起符合周礼的社会利益关系格局,如此才是孔子讲“喻于义”的最终归宿和义利关系把握的最高境界之所在。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7页,199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
(责任编辑/王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