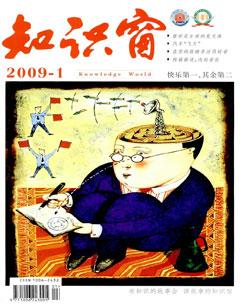初遇
安 宁
那一年我刚刚大学毕业,在北京的一家公司做文字工作。因为薪水太少,租不起贵的房子,便住最便宜的地下室;而为了尽可能地省下车费,则会早起半个小时,以便走一段路,乘坐公交,而不是近在眼前的地铁。
这样的生活,搅缠上并不怎么喜欢的工作,便让我整个的身心都觉得疲惫、孤单,且无助。周围的同事,皆神情淡漠,从不关心别人的私事,亦不想关心。大家只埋头做事,至于谁头疼脑热,情绪不佳,谁家人生病需要请假陪护。谁被领导批了需要安慰,无人会去关注。小小的格子间里。人与人之间,小心翼翼地行走,偶尔碰撞到,便倏地躲开去,似乎,怕被彼此,窥去了提职加薪的私密。
我那时是个生手,因为工作不熟悉,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没有人伸出手来,给我点滴的帮助。常常下了班。别人都已经走光,我还在为了一个文案,一次次地修改、完善。那时已是深秋,傍晚的风,自窗户里旋转着吹进来,将天蓝色的窗帘,吹成一朵蓬起的荷花,只不过,是要凋零且有衰颓的色彩的残荷。偶尔,走廊上的风,会吹开门,而后将桌上的纸张,哗啦啦地吹落到地上,或者席卷到门外去。
每每此时,总会有一个比我年长的男人,一张张地帮我捡起,而后温和地敲几下门,示意我将之拿回去。这是个笑容温暖、衣着素朴的男人,我一度以为,他是公司里与我一样底层的新人,或者,是那些来去自由的保洁员、电脑维修工;因为他温厚友善的举止,总是让我将之与格子间里的同事。自然地区别开来。所以当他一次次为我捡起文件,或者悄无声息地帮我关掉走廊上的窗户,我都只是微笑道一声谢谢,并不曾想对他做更深一层的了解。
后来有一天,我在公交站牌下,又看到他。他双手插在裤兜里。正轻松地吹着一首曲子,唇边依然漾着微笑,那微笑,似有一抹清香,若有若无地,飘散过来,将我轻轻地环住。他显然也是在等公交。正是下班的高峰期,接连开过去两辆车,都因为人满为患,到站未停。许多人都在焦虑抱怨,时不时地抬起手腕,看一下宝贵的时间。而他,则撅嘴吹着那首节奏明快的曲子,看着路上流来流去的风景。眼睛里,始终不曾有过丝毫的烦乱与厌倦。
我略带好奇地走过去,与他打一声招呼。他看一眼神情倦怠的我。便开玩笑说。看,你脸上的烦恼刮下来,能捏成一个活灵活现的面人呢。我终于被他逗乐,问他,你的眼睛,究竟看到了什么,可以让你一连被几辆公交落下后,依然这样喜悦歌唱?
他的眼睛,瞬间像点燃了一盏灯,有比刚才更明亮的光彩。他指指路上行色匆匆的人群,说,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身边的每一个点滴,都是一个电影的镜头呢。我不解,他便指着人群,一点点地解释给我听。你看,那个在小车里熟睡的孩子,他的一节小腿,像新生的莲藕一样结实有力,或许此刻,他在梦里,正奋力拔节呢。还有那个一脸浓妆艳抹的中年女人,卸妆后会不会还有这样昂扬的自信呢?而刚才那辆车里一边打电话一边掌方向盘的中年男人。心底定是骄傲自负的,总觉得世界缺少了他,连车轮都转不起来。至于你这个愁眉苦脸的女孩子,如果让你去演电影里被爱情围追堵截、找不到出口的女孩,定是连化妆也不用的。
我终于被他这最后的一句逗得前俯后仰。笑完之后我问他,你究竟在公司里做什么工作?他眯眼笑看着我,说,肯定是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小职位,否则,怎么会被你视作可以忽略不计的空气?
我是在几天后的公司集体会议上再次看到他的。彼时他在主席台上,与公司的领导骨干坐在一起。神情里依然带着笑,自信、平和、从容、洁净,又柔韧无比。他原来是被公司重点培养的中坚力量,而他的幽默、风趣、豁达与宽容,一度让公司的许多女孩子,迷恋不已。
而我,却是因为一味地斤斤计较于自己的小悲伤,而忽略了他曾经告诉过我的,那些在生活表面的亮丽多彩的风景。
我在一年后,终于寻到一处喜欢的工作,离开了那家公司。但我却再也难以将他忘记,就像,在此后/的行走中,我不会再忽略掉生活中任何可以让生活丰富灵动的风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