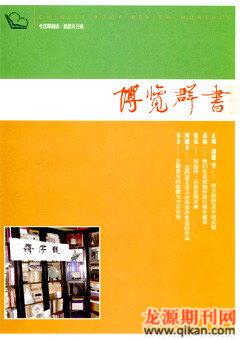我怎样整理和注释《溥仪日记》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能折射中国的20世纪,他的存世日记也因此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本文是《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一书整理、注释者王庆祥先生谈自身经历的真情实况:他怎样因李淑贤授权而获得整理和注释溥仪日记的宝贵机遇,又是怎样整理和注释溥仪日记的,《溥仪日记》再版时应该主要解决哪些问题。它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1996年6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一书。该书封面上作者署名为“爱新觉罗·溥仪遗稿、李淑贤提供、王庆祥整理注释”。当时,溥仪夫人李淑贤还健在,这一署名方式主要就是尊重她的意见而确定的。
李淑贤授权
197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溥仪的遗孀李淑贤相识。在北京东城北小街草原胡同23号院内一问不起眼的厢房里,我惊奇地见到了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遗留的大量日记、信件、文章、发言底稿、与各界人士的谈话记录等亲笔手稿,还有各种出席证、请柬和家庭影集。这些原始的文字和图片资料,真实再现了溥仪特赦以后的崭新风貌。我当时特别激动,“这些太珍贵了!它能让我们更多地了解溥仪的一生”。我当即提出合作整理溥仪遗稿,李淑贤欣然同意。1980年6月以后,李淑贤亲笔签署了多项授权书、协议书,我们的合作关系就此正式确立。
溥仪一生勤于日记,在前半生岁月里就曾写下许许多多的日记篇章。现在还能看到他8岁时所写的日记,因为当时年纪小,每天所记都很简短,但从中也能了解逊位小皇帝所受的教育,读过哪些书,见过哪些人,他每天怎样生活等。后来他寓居天津、度过伪满年代、被俘并成为战犯,其间日记大部损毁,却也有痕迹可寻。虽然天津时期的日记被溥仪亲手烧掉,然而,历史档案中还保留了那些年代里形成的多本溥仪的《召见日记簿》,翔实地记载了溥仪每天见过哪些人,这是他政治活动最重要的第一手见证。一些关键的历史情节得以再现:溥仪离津出关是主动行为,还是被“劫持”?是个人意志还是受到欺骗?他到底是真改造好了,还是伪装?他怎样看待新世界、新中国、新社会?
溥仪特赦后的日记存世较多,这位当过皇帝的公民,以关心时局的普通人身份,记述了当时国内、国际上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更从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的特赦人员的角度,记述了作为同事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情况和相关史实。特别是记述了他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以及聚餐、谈话等,他怎样看待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等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在日记中,溥仪还一笔笔记下了他与新婚妻子的婚姻家庭生活。他娶了李淑贤后,两人生活在国家供给的房子里,溥仪依然保持着每天写日记的习惯。从某一特定角度说,他们是一对不幸的夫妻,没有衾枕之乐,不能生儿育女;同时,他们又是一对幸福的伴侣,相伴为生,相依为命,谁都离不开谁。两人还经常开玩笑、侃大山,有时李淑贤被溥仪逗得捧腹大笑。应该说溥仪是位很友善的人,能够真诚对待一位普通工友。这就是我们可以从日记中看到的溥仪,看到他特赦后过着怎样的生活。
溥仪的绝笔日记写于他去世5天前。那篇日记简短且字迹潦草,除了“蒲老开方”外其它的几个字都不认识。甚至连日期都没有记下。我与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原处方核对,才确定日记的日期为1967年10月12日。
怎样整理和注释
根据公开出版的需要,以及李淑贤的意见,我对溥仪日记做了大量整理工作,主要涉及6个方面。这些都很重要,不做整理,这本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一、格式和文字整理
这方面整理包括正确辨识字迹、调整混乱文序、规范行文段落和标点符号、换补文字误漏、准确标识日期,以及必要的文字规范如删字删句删段等。这一项项整理还涉及溥仪日记的内容,如事件、人物、单位等,都必须弄清楚。
二、内容整理
根据适合条件,把并非溥仪写入正规“日记”册中的文字,编入《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一书。这是在内容整理方面,我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具体包含6类情况。
1、把1956、1957年溥仪到各地参观的实录和观感编入日记
收入《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一书中溥仪1956年和1957年两年内的“日记”(第46页至96页),其实只是溥仪在抚顺关押期间随同战犯管理所组织的参观团,到外地参观之际而在当日写下的实录和观感。管理所领导要求溥仪和伪满几名大臣,每人写一份“认罪书”或称作“悔罪书”。后来又统一给这种材料取名“我的前半生”。溥仪、张景惠等每人都写了一篇“悔罪书”,也都叫“我的前半生”。应该说明的是,这与溥仪特赦后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的那本《我的前半生》不是一码事,体例和内容完全不同,而且只写到1957年7月为止。
1959年12月第一批特赦战犯出狱时,中央领导非常关注溥仪,希望了解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的表现,就让管理所领导把那份“悔罪书”用铅字8开本印出几十册,以供阅读参考,而印到白封皮上的名字即为《我的前半生(未定稿)》,其中就有溥仪在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参观的内容,溥仪自己保留了这种8开铅字本一套3册,他去世后一直由李淑贤保存。1980年李淑贤把这套资料和溥仪日记原稿等一同交给我整理。为了弥补溥仪并未在其人生中极为重要的改造时期留下日记的缺憾,征得李淑贤同意,我把这些经过考证、核实的内容,编入《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一书。
2、“大海捞针”,找回已失日记中若干得以保存的篇章
溥仪1960、1961、1962三年的日记以及1964年(除3月11日至4月29日以外其它时段)、1965年(除1965年4月15日至年底时段)、1966年(除5月至8月间时段)这三年之部分日记,均已经失掉。为了弥补这一重大缺欠,我付出“大海捞针”的努力,坚决要把已失日记中若干因当年曾被抄录于另本而得以保存的篇章,即那种写在非正规“日记”册中、而且是散落在上百万字溥仪遗稿中间的“记事性记载”文字一一寻找出来,再按时序编入《爱新觉罗·溥仪日记》。对此,书中也有明示“是溥仪亲手摘抄在有关笔记本上而幸运地保存了下来”。
3、把在别处找到的相关详细记载合并入日记本文
溥仪日记中本文存在,但属简记。我又从溥仪的非日记性笔记本上费力找到了相关详细记载,把它们按时序编入《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中,以补充同日由溥仪写入正规“日记”册中的文字之不详或不足。溥仪遗稿中“1963年5月22日”相关详细记载即这种情况,全书约有30例。我在《关于整理和注释的几点说明》第二项中专门谈到这种情况:“同日日记而分写两处的,整理时合并,但隔行单列不相混淆,并对移入的部分加注说明。”
4、以收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的定稿代替溥仪的记录稿
1959年12月14日,周恩来接见首批特赦战犯并讲话,溥仪在笔记本上留下了这次讲话的亲笔原始记录,题为《1959年12月14日周总理对我们讲话》。在溥仪的笔记本上,还有一篇《周总理讲话、语录(第一次接见时)1959年12月14日》,这是事后亲历者相互对照、传抄而形成的,溥仪又亲笔抄写在他的笔记本上了。还有第三篇《补录周总理谈话1959年12月14日》,这是事后由溥仪亲笔补录在笔记本上的。由于其内容涉及国际关系和对台关系某些不宜公开事项,这在当年是不可能原样发表的,也是非亲历者不可能看到的。
以上三篇原始记录与收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一书的正式谈话记录,除大致意思相符,具体用词、组句、成篇都不同。在周恩来《接见首批特赦战犯溥仪等十一人时的谈话》几种文本并存的情况下,我经过比对,乃选定收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一书文本,用以取代溥仪的原始记录稿和“对照、传抄”稿。
5、把书写在溥仪日记行文之外的记载纳入正文
就是说,本篇日记中的一两句话,在原文中并不存在。而是写在日记行文之外,实为某种备忘性或提示性记载。例如1965年10月5日日记正文行文外,有一句:“他说从皇帝到人(公)民,是史无前例[的]奇迹。”经考证而把它纳入《爱新觉罗·溥仪日记》正文,并加注释:“此句是溥仪补写在日记正文之外的,现据内容插入正文。”这种情况全书有46例。
6、史实纠误,排除“硬伤”
溥仪原文或有“硬伤”即出现重要史实错误,经查阅存档历史资料,对溥仪原文“硬伤”,加以考订和纠正。这一项整理全书有19例。例如1963年3月22日日记,溥仪原文为“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经查阅历史档案,我将“第二届”改为“第三届”(《爱新觉罗·溥仪日》)P137)。又如1965年10月5日日记,溥仪原文为“政协祭严济慈先生的追悼会”。经考证,我改定为“政协祭严口口先生的追悼会”,并加注文“是日,全国政协为严希纯先生开追悼会,溥仪却误记为别人了。严希纯逝世前任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国政公党中央常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学委会主委等职。”
三、注释,文字量已超过正文
因为溥仪身份复杂、经历丰富,其日记涉及一千多位中外人物和众多的历史事件,又恰可折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社会变革,内容博大,这势必影响到注释文字的数量和质量。整理他的日记必须广加注释,才便于读者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说,注释溥仪的日记,等于编一部溥仪辞典。同时,这也是印证和传播历史史实的好机会。为此,我整理溥仪日记特别着重注释,其文字量已超过正文。就我的能力以及目前占有的资料而言,可能还是难以尽如人意。
四、有创意的“篇后附录”
关于“篇后附录”,我在《爱新觉罗·溥仪的遗稿与日记》一文中说到这一发现与创意的由来:“溥仪日记中的某些记载过于简略,以致内容不能明了,对此而有其他可靠资料能够补充或佐证的,都尽可能注出或作为‘篇后附录而完整引证出来,似有助于环境的补充。本书‘篇后附录较多地利用了董益三先生的日记资料。董先生是溥仪特赦后的同事,他们都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同室办公,朝夕相处,在60年代中期前后五年多时间里,他们不但有共同的业务生活、政治学习生活、劳动生活和参观旅游生活,两人还成为邻居和相知的朋友,发生了比其他专员间更密切的个人和家庭之间的交往。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年代里,董先生帮助溥仪分析形势、正确处理面对的各种难题,使两人的情谊在新的考验中得到深化和发展。当我在80年代初走访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时,他热情而直率地提供了自己的日记(1962年~1967年)以及当年的工作笔记等珍贵手稿资料。董先生的生活规律性极强,日记准确、详明、生动、具体,富有思想性和史料性。他提供的资料不仅能够核实溥仪日记中的许多记载,而且有助于丰富溥仪日记的内容,使其失于简略的涉及专员共同生活的记述,得到了必要的补充性的具体说明。尤为难得的是,董先生日记中还有数量不少的关于溥仪言行的生动的直接记述。引证董先生的日记、工作笔记作为‘篇后附录和注文,等于保存了一批有关溥仪思想和生活轨迹的重要佐证资料,他填补了溥仪遗留的部分空白。”
五、保护原文原意
溥仪作为中国末代皇帝,又经历了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社会变革,他的日记恰可折射中国近现代历史,重要而珍贵。因此,整理他的日记必须慎之又慎,重在保护原文原意。
对溥仪原文。或因文字重复,或因字迹不清,或因记载简略以至语意难明,或因关涉隐私,或因受限于当时的政治因素,或因其它种种原因而删字、删句、删段。内容取舍涉及要对本文从多角度考量,要与溥仪日记关联、比照,藉以认定是否可以如此取舍。我做这项整理时,一般都以删节号表示,并在注文中明示,对读者有交代。此类删文。全书可以列举82例。
例如1957年6月9日-12日日记(在长春参观第一汽车厂)。溥仪原文:“还有在幼儿园也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感动。当无数天真活泼的儿童,向我们表示欢迎并伸出那可爱的小手打招呼,有的还发出感人的声音说着:‘叔叔你好!也有的说:‘叔叔抱抱我!等等的话。真使我‘自惭形秽,我暗想到:你们今天欢迎的这一群人们,都是在过去曾经骑在你们父兄的头上,压迫过他们,榨取过他们,甚至还曾经杀害过他们的血腥凶手啊!可是现在呢,却都怡然自得地受着这群可爱孩子的欢迎!”我整理后删去溥仪原文中“还有”、“当”、“们”、“在过去”、“的”、“曾经”等多余虚字,增加了“这些话”三字,使文字精炼、通顺、规范(《爱新觉罗·溥仅日记》P85、86),而实质内容,凡属表达一定意义的用词、用字,都要尽可能保留而不随意改变,如需变动,一般采取“虚改实留”的原则。不能把溥仪日记作为手中玩物,随便“创造”,改变原文,篡改内容。
再版时的建议
我整理溥仪日记主要是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的。受到时代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有缺欠。我在《爱新觉罗·溥仪的遗稿与日记》一文中就谈到了这一问题:“关于本书的整理,首先应当指出,溥仪日记中记录的某些讲话、记述的某些见闻以及其中反映的某些观点,由于受到当时政治背景、特殊环境或其他因素的影响,现在看来是不合时宜的,这当然不应苛求于写日记的人。对此,除删节一些内容外,均加注释说明。如加注引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有关段落加以说明。尽管如此,当年的日记不能不带有当年的痕迹,‘而且作为个人的日记,受到经历、感情及特定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在记人记事方面也难免带有个人感情色彩或看问题的片面与偏见,谨请研究者和广大读者联系历史背景正确对待之。”对《溥仪日
记》再版,我提出一些建议。
一、恢复因政治因素而删除的内容
日记的主要功用就在于记录时代,展现真实。因政治因素而删减内容,现在看来很不合适。例如1957年8月28日~30日日记(二次参观沈阳),整理时删去原文中“也使我认识到,章、罗等右派分子集团的阴谋诡计的可恨可耻”一句(《爱新觉罗·溥仪日记》)p95),“反右”是当时背景下很真实的情况,删去此句不合适,完全可以不删除。此外还有误删的,如整理1966年12月23日日记时误删“每天睾丸酮注射二次,佚剂一片”一句,更应该恢复。
二、纠正失误
整理、出版《爱新觉罗·溥仪日记》是一项巨大工程,工作量极大,虽历数年精心整理,也不可能丝毫不出现失误。此类情况可以列举出56例之多。例如1957年6月4日~8日(在哈尔滨参观)。溥仪原文为“绿树涟漪相衬成趣”,《爱新觉罗·溥仪日记》(P67)错改为“绿树涟漪相见成趣”,文义已不通;1967年7月6日日记原文:“下午,王毓超突来访”,《爱新觉罗·溥仪日记》(P688)误以“下”为“上”,写成“上午”等。
三、天津时期溥仪《召见日记》增加注释
《召见日记》中可见大量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例如当年健在的清朝遗老,民国政府的高官,英、美、法、德、意、西班牙等欧美国家驻天津的政界和军界人物以及来访的各国政要,特别是日本军界、政界、文化艺术界各类代表团等,他们在天津会见溥仪都存有现实或长远的目的,其中还有一些人物正是后来伪满14年中与溥仪又发生多种关联的人物,例如德穆楚克栋鲁普、邢士廉、谢介石、陈曾寿、郑禹、土肥原贤二、吉冈安直等。当时溥仪会见过的人物中,还有一些后来又与新中国发生过某种关联,例如章土钊、周善培等。对这些人的政治倾向、简单经历以及他们与溥仪的交往加以注释。有利于显示溥仪会见他们的政治目的、内涵和实践,很有必要。希望了解内情的国内同行学者共同做好这项工作。
四、把《溥仪生平大事记》作为附录编入书中,不可缺失
存世溥仪日记固然珍贵,但毕竟由于历史原因缺失过多,如能把经过考证而确认的溥仪生平细节列入大事记附于书中,则非常方便读者和研究者了解并理解溥仪存世日记。应特别侧重属于“大事”的细节,侧重把时间定位在某年某月的某日,而使之真正可与溥仪日记相辅相成。
(本文编辑张云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