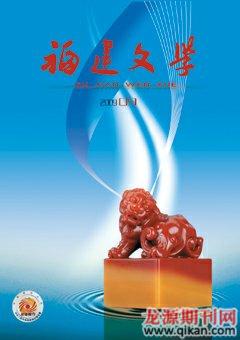我的大学不再见
我从未想过我的大学,我为之奋斗了十二年的大学竟然是这样开始的。
福州有句俗话:“七溜八溜,不离福州。”直到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才明白了它的意义。后来在我的母校福州一中,我俨然成了名人。在学弟学妹步入高考考场以前,老师总会以我为反面教材,提醒他们务必认真,切勿漏题,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有个女生告诉老师,传说中的我就住在她家的对面。
还有一句俗话叫:“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我走进大学的那一天,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电视上反复播放着被恐怖分子劫持的客机冲撞世贸中心的录像。我沿着浑浊的相思河到管理学院报到,陌生的校园,陌生的路人,只有我被调剂的大学,它和我出生的城市有相同的姓氏,令人窒息。我被学校安排走读。从家骑车到学校,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比高中还近,完全没有上大学的感觉。
军训后不久,秋天如期而至。福州是没有秋天的,冬夏交替仿佛只是一念之间。在临江五楼的教室里,望着闽江对岸水墨般缥缈的远山,迷茫的江面上偶尔传来几声尖锐的汽鸣,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刺骨的秋凉。老师关上门窗,继续讲授高等数学,而台下的我一头雾水。尽管我依然毫无感觉地拿着奖学金,我却再也无法专心读书,纠缠于退学和复读的问题,情绪周期性发作,弄得全家鸡犬不宁。我就像一个困在迷宫中的人,在漫漫长夜里寻找着出口,为了忘却无法忘却的记忆,为了在茫茫人海中不被平庸地埋没,我开始用文字书写内心的彷徨。
适逢第十三届全国书市在福州举办,陆天明、石钟山等著名作家到温泉公园签名售书。我当了回追星族,签名,合影,那是我和作家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书市期间,我还参加了李胜杰的心灵财富训练。他说亿万富翁也有破产的时候,只要认清自身的价值,就有可能东山再起,人生有许多条路,不要在弥留之际留下丝毫遗憾。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高二我就在《散文》发表了处女作,高三入围了新概念作文大赛,但高考时却并未因此报考中文系,到福州大学后也没有加入文学社。转眼大二了,我感觉到有一股力量驱使我回到文学道路上来。
在相思河畔的书摊上,我买了本《诗江湖·先锋诗歌档案》,封面很黄很暴力,是个裸体女人的侧影。通过诗集上提供的链接,我开始上网写诗,最初在“唐”、“个”等论坛活动,以写口语诗为主,到“哭与空灵性诗歌”论坛后,开始回归传统和抒情。那时我还没有笔名,随便取了个网名“布什”,不时有诗人问我何时攻打伊拉克。美国在次年发动战争时,我已经开始启用笔名“三米深”了,又不时有诗人问我为什么不是四米深。世界上本是没有问题的,问的人多了,就有问题了。我特意弄了个标准答案:“一米只能埋住下半身,两米可以没过头顶,但由于人求生的本能,挣扎着还能爬出来,而三米的深度就永远深埋地下了,这样就可以把不堪回首的往事忘却。”
在钟声文学社的社刊上,我读到了福州大学历史上十四个诗人的作品,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和届别,大多已经毕业,包括法学院的欧亚,电子系的康城,会计系的吴语、吴季、黄沙子,土建系的张幸福。上世纪90年代是福大诗歌的黄金时期,作为一所理工院校,能走出这么多诗人并活跃于中国诗坛,不能不说是个有趣的现象。他们从网络和报刊上走到我的面前,又过了一个月。
由《海峡都市报》举办的诗歌朗诵会在翠湖阁举行。我家住在西湖附近,就顺便参加了。朗诵会来了许多福州本地的诗人。见到欧亚、吴语、吴季等学长,倍感亲切。朗诵会正是由欧亚策划的。因为有自由朗诵环节,我就叫母亲打印了首诗带出来。我最后一个上台,朗诵的是自己写的《家园梦想》。第一次当众朗诵诗歌,手脚哆嗦得厉害。另一个上台朗诵的福大学生是化工学院的风贼,他穿着一身黑色风衣,朗诵的是一首即兴创作的诗。观众通过举起手中的玫瑰给朗诵者投票,第一名是福建师大的潇潇枫子。后来《海峡都市报》做了专版报道,在最大的一张图片上,我举着一朵玫瑰花,神态极其滑稽。因为是广角镜头,脸还有些变形。另外还刊登了一个花絮,说我是“诗歌发烧友”,还说我的母亲听着我的朗诵,“眼里满是幸福的泪花”,纯属无中生有,很长时间成为大家的笑谈。
朗诵会无形中成了福州80后诗人的首次聚会,虽然我们还互不相识。过了不久,风贼打电话给我,约我在东区食堂二楼的网吧见面,我们一眼就认出了对方。我们把散落在福大校园里的诗人聚集起来,包括机械系的小佰、经济学系的黎中虚、中英学院的笔尖。同时我又陆续结识了闽江学院的管路、师大的杨澍澍和张标明、财会管理干部学院的梁辰、玩乐队的阿草等校外的80后诗人。我和潇潇枫子、风贼创建了“零空间”论坛,后来发展成为福建80后诗歌的阵地。
接着,我和风贼策划了福州大学首届诗歌节。由于缺乏经验,我们跑了一天场地和赞助,一无所获。校团委提出要办理一系列手续,还要支付场地费用,但没有一个商家愿意提供赞助。没钱有没钱的办法。我们分头打电话邀请了一些诗人,在子兴楼找了间闲置的梯形教室,进行了简单的布置。出乎意料的是竟来了不少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朗诵结束后,谢宜兴、余禺、程剑平、伊路等诗人走到诗歌爱好者中间,向他们赠送诗集和诗报,与他们触膝谈心,将诗歌节推向了高潮。
2003年5月,我的第一首诗在《海峡》发表,此后我的诗歌陆续发表在全国各大诗刊和纯文学期刊上。我的生活因为诗歌充实起来,通过诗歌我重新找回了自信。我享受着这种诗意的生活,那时我特别喜欢黄磊主演的《人间四月天》,为了买到徐志摩戴的那种纯圆眼镜,我几乎搜遍了福州所有的眼镜店。我们还经常去学校北门附近的一个露天茶座聚会,喝茶,大声朗诵诗歌。我甚至把诗歌带进了课堂,上课时遇到灵感就随手写下,还心血来潮地在邓小平理论课上做了个题为《诗歌创作与三个代表》的演讲,更不可思议的是老师竟然赞不绝口地给了我最高分。
尽管如此,我的写作却一度陷入迷惘。我上网之初写的一组口语诗在钟声文学社内部会议上遭到了批斗;虽然我的诗在省外获得了不少好评,但福建的诗人,特别是福大的学长对我的评价始终不高。正当我站在十字路口,徘徊不前的时候,我结识了南京作家吴晨骏。
第一次和老吴吃饭是在二环路边的一家小吃店。那时他刚刚结束了自由写作的生活,来福建当编辑。老吴三十多岁,说话不疾不慢,他的眼睛始终给人没有睡醒的感觉,恍恍惚惚,像游离于梦境。几杯啤酒下肚,老吴的脸就红了,红扑扑的,像抹了胭脂。他憨憨地笑着,有些不好意思。看来老吴和我一样,酒量都不好,可是老吴敢喝,而且酒后特别真诚。老吴阐述了他对诗歌的理解,他说诗歌要贴近生活,要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我当时负责编辑系刊和院刊,邀请老吴做名誉顾问,老吴欣然答应,并为刊物题了词。每次去老吴那里玩,总有说不完的话,有一次聊到了凌晨,老吴向我透漏了他写作的秘密:“写作就是梦游。”我把新写的诗作给老吴指点,他说我进步很大,形成了写作的意识,是福建80后中最有潜力的。如果没有老吴的鼓励,我不可能写到今天。
福大诗歌节的成功举办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海峡都市报》对我进行了采访,他们对我从高考落榜到走上诗歌道路的人生经历很感兴趣,刊发了通讯《校园诗人:我们的灵魂偶尔歌唱》,展现了校园诗人的精神世界。半个月后,福建教育电视台也联系我,为福大诗歌拍了一个专题片《校园里的麦田守望者》。诗歌一度成为福大的关键词。
大二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认识了钟声文学社的社长葛剑锋。他也是金融系的,是我的学长。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上选修课。老葛对我说他卸任了,我劝他和我们一起上梁山吧。第二天,老葛取名“子规”,也开始上网写诗。他的诗如其人,有一种特殊的硬度和质感,正如他严肃的外表下那颗柔软的心。那段时间老葛经历了许多变故,正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候,诗歌让他得到了解脱。
暑假过后,不久就是国庆,一个80后的民间诗会在南昌举行。我对老葛说现在你也是诗人了,一起去江西参加诗会吧,老葛居然答应了。诗会地点在南昌大学附近,开幕式上有许多南大学生围着我们索要签名。研讨会上,我提出“诗人首先要真诚”的观点,某个中年诗人偷换概念,对我展开人身攻击,甚至歪曲、误导,最后演化成对80后整个群体的攻击,让我难以招架。老葛挺身而出,为我据理力争,不惜得罪诗坛前辈。就这样,老葛成了我患难与共的好兄弟。
战火又从南昌蔓延到了厦门。一个月后,福建首届青年诗人交流会在厦门召开,我和风贼、笔尖、潇潇枫子一同前往。在会上,我们向与会者分发了《零诗报·福建80后诗歌专号》,著名诗人舒婷询问了福建80后的写作状况,表示了对校园诗人的关注和鼓励。交流会的最后一天,那个中年诗人再次向80后发难。在全国五大诗刊主编面前,年轻气盛的我拍案而起,与其展开激烈的争论。我再次阐述了“真诚的三个境界”、“写诗从做人开始”的观点,得到了在场诗人的肯定。主持人说:“我们都应该问问自己真诚吗?只要你真诚,就有了成为诗人的基本条件。”是非终于有了公断。这次诗会也标志着福建80后以整体的姿态进入诗坛。
大三分专业后,课程多了起来,除了应邀参加福建作家沙龙,我逐渐淡出了各种文学活动。在出版大厦对面的餐馆里,老吴对我说他要调到北京去了,我低着头喝着啤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风贼开始参加工作。从南昌回来后,我经常跑到老葛的宿舍去玩,问专业课的复习重点。我上大四的时候,老葛也毕业了。其他在福州求学的80后,也相继毕业,各奔东西。小佰虽然大我一届,但因为学分不够留级,所以大四那年,福大的80后只剩下我和小佰。
我中午常从管理学院骑车到东区,找小佰一起吃饭。小佰很瘦,又老爱吃一些素菜。我有时买烟给他抽,他都是一支一支地买。然后我们一起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散步,或者坐在小佰宿舍后面的平台上,谈人生,谈诗歌,谈感情的虚无,谈触不到的将来……天空格外湛蓝,平台上落满了叶子,偶尔有微风吹过,和煦的阳光透过树阴洒在水泥板和落叶上,发出轻微的细响。小佰最喜欢海子的诗,经常会背诵几句。还有那么两三次,小佰到管院陪我一起上大课。有一回我要指一个可爱的女生给小佰看,结果脸还没有看清楚,小佰就趴在桌上睡着了。
老葛毕业后租在离学校不远的公寓里,我偶尔跑到他那里做客。他换了几份工作,又为情感所困,放下了手中的笔。小佰家境不好,除了发奋学习把挂掉的学分补回来,周末还要勤工俭学补足拖欠的学费,也不再写诗,甚至连过去的诗作都找不到了。在生活中漂泊的人,诗歌也成了一种负重。大家都渐渐疏远了诗歌,只有我还在坚持。大四上学期末,我以80后的身份入选了《诗选刊》中国诗歌年代大展,并加入了福建省作家协会。在网络上偶遇初中的同学,我们一直热爱着文学,在高考后死而复生的我竟忘记了少年时的理想,我们都曾追寻的作家梦,而今只有我实现了。
最后一个学期,忙着实习、求职、毕业论文和答辩,在校的时间越来越少。回学院拿就业推荐表那天,我发现相思河两岸的树上又开满了沉甸甸的红花。我对植物知之甚少,不知道那是不是木棉。我停下车,缓缓走到树下。四年了,我是第一次如此认真地仰望它们,以后它们只会在我的记忆深处开放,也许我会怀念那些熟悉的声音。
毕业典礼在逸夫馆举行。穿上学士服,黑袍子,方形帽,彩色披肩,排队,喊“茄子”,拍毕业照,欢呼着把帽子抛向天空,天色慢慢暗了下来。从院长手中接过学位证书,院长把学士帽上的流苏从右边拨到左边。最后是合唱《毕业歌》,我并不会唱。播放这首歌曲时,大家都不会唱。曲终人散,我的大学就这样落幕了。
当我第一次走进福州大学,我就开始幻想离开的情景。我常常这样安慰自己:大学已经过去百分之几了,再过百分之几就可以逃离。我没有想到,在走出校门的一刹那,一阵莫名的失落和感伤竟侵袭而来。是这所大学让我成长起来的,这四年来,我和它始终若即若离,现在是真的要离开了。我不知道将来我会不会怀念这里,怀念这漫长却又稍纵即逝的四年。
7月初,导师打电话祝贺我的毕业论文被评为校优秀论文,这成为了我的学生时代一个貌似圆满的句号。小佰发短信告诉我,他找到了一个制造游艇的工作,就要动身去罗源了。我们在学校对面的德克士喝着可乐,吃着薯条,感叹着福州的80后全散了。我们在空荡荡的校园里走着走着,小佰抽着烟,风吹在背上很凉爽,我抬起头来,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属于这所学校了。走到车站,我们都累了,恨不得回家好好睡上一觉。小佰的车很快就来了,他边说再见边跳上了车。我目送着公共汽车的背影,渐行渐远,和我的泪水渐渐模糊成一片,变得并不真切……我在熟悉的站台上站了许久,好像公车一来我就和身后的大学,和那四年毫不相干……
再见了,我的大学!我的大学,不再见!
责任编辑 贾秀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