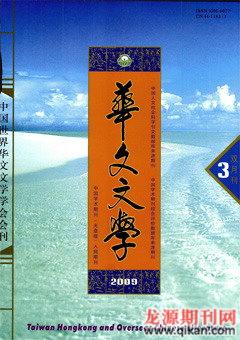舞鹤创作与世纪末台湾
李 娜
舞鹤创作以“复杂”、“晦涩”著称,他的作品,与当代台湾的文学书写脉络和文化思潮形成呼应,并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具有与“潮流”的自觉对话和反思意识;在艺术审美上,具有强烈的实验性和探索性,形成了在癫狂姿态中蕴含细腻深情和深刻批判的个人风格,而这是与世纪末台湾的政治文化和精神内涵密切相关的。
将舞鹤的作品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起来,俨然是为30余年来台湾文学生态绘制的一幅地图:写于学生时代末期的《牡丹秋》、《微细的一线香》,散发着20世纪70年代现代主义余绪和乡土文学主流暧昧相杂的气息;写于隐居时期的《逃兵二哥》、《调查:叙述》,在解严前后蔚为大观的反体制与“伤痕”文学中,不加入激越或悲情抗议的行列,却以逃兵的“神话”和历史的“神化”,对体制对历史、也对模式化了的历史书写,作了独特的反思;走出淡水之后,交出的《拾骨》、《悲伤》,有关台湾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与城市的遭际,最是触动台湾的痛楚与远忧,而舞鹤付诸暴烈而癫狂的文字,在在惊动人心;走出了隐居的小镇,再走向岛屿的高山密林,《思索阿邦·卡露斯》和《余生》对原住民的当下生存和历史记忆的探访,是对长久被侵犯、被出卖的少数者群体及其文明的关注也好,是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也罢,舞鹤都展示了一个有人文关怀的书写者的诚恳和深度;而在世纪末台湾由“同志”至“酷儿”、以及“情色书写”的热潮中,舞鹤又以《鬼儿与阿妖》、《舞鹤淡水》眩人眼目:对文学文化作为“时尚”的刻薄嘲讽、对生命与书写之自由的信仰,寓于猥亵狂放的“肉欲书”,正是舞鹤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他有意寻找其个人化的美学风格的见证。在最新的作品《乱迷》中,“情色”不减,“自由”更甚,早年书写“家族史”的野心与身而为人、为台湾人、为世纪末台湾人的困扰生活,出之以断片残章、呓语“天书”似的文字,舞鹤俨然有了一种更为决绝的书写姿态,书写是自由的获得,也是求道之路。
第一章微细的一线香——舞鹤创作
的身世来源与70年代台湾
舞鹤在青年时期接受其时蔚为主流的现代主义思潮的熏陶,相对成熟的作品则产生于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时期,此一论战,事实上是70年代戒严体制下台湾社会政治、文化矛盾以文学形式的显现,对此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通过《微细的一线香》等早期创作,可以看到“乡土”与“现代”的交缠,如何奠定了舞鹤创作的关怀意识和审美追求,而这也透露了此后30年台湾文学流变的内在线索。初登文坛的舞鹤吸收了现代主义、乡土记忆、古典中国的养分,有一种以叛逆之姿来表达对现实的强烈关注的倾向。作品虽不免于稚嫩、矫饰或芜杂,却透露了可贵的自由品格与批判立场。
第二章叛逆者的逃亡——《逃兵二哥》
与解严前后的反体制文学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台湾反对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而舞鹤隐居淡水小镇,写下《逃兵二哥》,小说来自舞鹤两年军中生活的经验,作为小说核心的“自由”意识不但与“国家”势不两立,而且试图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在民主大潮的映照之下堪称消极。舞鹤对“自由”的强烈感受,首先产生于个体与体制的抗辩关系之中。在兵役这一国家强制行为中体会到自由被剥夺的滋味,舞鹤的“自由”包含了强烈的反专制体制思想及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其哲学基础是对个体生命自主的肯定。其二,在精神渊源上,舞鹤的自由观是承继庄子哲学的。他认为自由是生命的本真状态。从此出发,脱离了现代场域,所追求的自由不是理性话语,不是“主义”。也正因此,对军队体制压迫的强烈感受,虽然让他开始关注反对运动,却并没有置身其中,因为那将面临再一次成为“螺丝钉”的危险。事实上,对“自由”的追索,是贯穿舞鹤全部创作的内在线索。书写和文字,都是通往“自由”之境的道路。
在解除战时戒严体制前后,台湾涌现出大量反体制的、政治的文学创作。《逃兵二哥》实为先声,以“逃兵二哥”这一荒诞而饱满的形象,及其独特的、具有疏离感的“自由”观,较之解严前后义愤填膺或疾言厉色的“反体制”书写潮流,提供了一个更具内省意识的政治文学文本。
第三章被拆解的悲情——《调查:叙述》与台湾“二二八”文学的演变
《调查:叙述》以“二二八事件”的平反、调查为题材。在这一被视作“伤痕”文学的经典题材上,舞鹤所采取的恰是一种“反伤痕”的书写。他警惕于“二二八”的被符号化、悲情化乃至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刻意扭曲。而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政治的实相。
小说交换使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宛然在历史的真实场景中纵横,又限定在一个“调查:叙述”的框架中,不时用现实场面中喝茶、吃饼和岔开的话题,来提示读者,刚才激荡心魄的故事,不过是经过“叙述”的“回忆”。这种文本组织方式本身或可看作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叙述者早已明白历史的不可还原。其实,“历史”、“记忆”、“真相”之间密切而又游离的关系,已经愈来愈被探访历史伤痕的人们知觉;以书写“还原历史真相”的强烈渴望,已经一再受到挫折,舞鹤试图超越这一挫折。他的纪念碑,与其说要铭刻一段真实的历史,毋宁说要铭刻一种真实的伤痛。感知这从身体到心灵的痛,人们才得以穿越时空的阻隔,窥探历史的真相。然而随着时光流转,随着当事者和直接承受者的纷纷离世,伤痛也在八哥“痛痛痛”的学舌中变得滑稽和稀薄了。纪念“二二八”的大会或许仍会逐年召开,然而人们注定将忘记真实的伤痛,而只能通过各种各样或扭曲或残缺的文字记载,通过仪式化的行为,来获得而无法真正“获得”对历史的认识。如此,对“伤痕”的“辩证”书写,使得舞鹤对“二二八事件”这一伤痕文学经典题材的处理,超越了在现实中被反复强调的族群悲情,也超越了政党之争反复涂抹于“二二八”之上的“族群仇恨”,展现出更为深刻的历史悼亡和现实批判精神。作为一个精神意义上的永远的革命者,舞鹤的革命对象不仅是专制与暴力,也是一切政治行为的虚矫与功利。也因此,在台湾“二二八”小说的书写脉络中,舞鹤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本章进一步追踪“二二八文学”半个世纪以来的流变。在“二二八”被简化为本省人特有的“悲情”、外省人与生俱来的“原罪”,被塑造、供奉为“国殇”,相当程度上成为一个政治符号的同时,文学一直在提示着更复杂关系的存在。文学一方面反映、见证了这个过程,一方面以疏离或辩诘主流意志的书写,消解着这一狭隘的政治操作。事件之后流亡海外、大陆的左翼人士虽然难以在台湾发声,而左翼的思想传统并未从台湾消失,陈映真、蓝博洲乃至侯孝贤等人对50年代那些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台湾知识者的探访,呈现了被当下主流刻意忽略的另一脉历史;而郭松棻、李渝这些70年代的红色学运分子,以最精致的现代主义书写铭刻刻骨的历史伤痛,已然祭起了永远的“边缘”思想与美学。90年代以来舞鹤的反伤痕叙事、林耀德的原住民理想以及“亲反对阵营者”李昂以女性角度对反对运动神圣性所做的内部颠覆,使得“二二八”的文学思考呈现更复杂的面向。作为战后出生的一代,他们与林双不、宋泽莱等一样,都一再剥落曾受的官方历史教育,但选择了不同的精神路向。总之,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人们的书写,以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情感,消解了狭隘的政治操作。从中展现了台湾知识者的心灵历程,也清晰地映照出当代台湾政治文化的变化。
第四章拾骨者——《拾骨》拾起
的庶民社会
《拾骨》是描写台湾庶民生活的出色之作。小说中的拾骨师用铁铲、麻袋为死者拾骨,小说家舞鹤用文字、语言为已然或正在消逝的乡土记忆拾骨,为曾经生动而今飘零的礼俗与情感拾骨,更为无所依附的生命的乡愁拾骨。拾骨者“我”有无法停止的暴烈情欲与痴心妄想,在这情欲与妄想的碎片残骸里,现代化投射在古老礼俗上的阴影、庶民生活的暗淡与个体精神的虚妄,这些已经为我们习焉不察的日常景观,仿佛被重新观礼。
本章探寻舞鹤对台湾庶民社会与文化的关怀,并与其早期类似题材作品比较,分析其书写美学的转向,以及建立在反现代性思想基础而非“本土意识”之上的“母土情结”。在90年代台湾的社会政治氛围中,《拾骨》曾被当作从“乡土中国”到“台湾本土”的认同转变的典范文本。本章透过《拾骨》对“现代化”笼罩之下庶民社会的价值沦落与粗蛮生命力的描摹,指出其“本土”书写恰恰消解了“本土”原本僵硬而单一的色彩。他的“本土”也是“反本土”的,反对的是一切断然切分并归类的、以“正确”自居的、简单化的概念。就舞鹤整体创作而言,与其说存在一个“去中国化”的“从乡土(中国的)到本土(台湾的)”的转化,不如说存在一个“去意识形态”的“从乡土(观念的、想象的)到本土(物质的、原欲的)”的过程。所谓转变,在文学想象与书写美学上的意义远大于政治上的意义。
第五章淡水的孤独之鹤——台湾现代化情境下的古典寓言与情欲书写
书写时代转折中的台湾,以为历史作证,是台湾文学的一个传统。舞鹤的中篇小说《悲伤》描写淡水小镇在全球化经济时代来临之际被“脱胎换骨”的改造,从一个具有田园之美的安宁之地,变成钢筋水泥都市的复制品,但并未停留于对“现代化”台湾的作证或简单批判,而是构建了一个在现代化情境下寻找古典人格的寓言。小说中弥漫了台湾古镇和乡间的各种传说、历史和民间生活场景,甚至点染了对淡水人与台湾先住民平埔族、“小矮人”血缘关系的似假非真的考证与兴趣。小说批判现代经济发展对自然生态与社会传统的伤害、守护原乡的主题,已然呼之欲出,但以此涵盖“悲伤”的寓意是不够的。论者多有论及作为“纪念碑”的《悲伤》如何纪念着“消逝中的淡水”,却可能忽略了“消逝中的淡水”的守望者的精神磨砺与冒险。在一个不断向深层推进又不断自我消解和意义再生的文本中,对小镇历史、传统、自然的极端熟稔,出之于一个萎弱现代人的迂曲复杂的精神空间,展现了淡水/台湾的自然与人文精神流失过程,非在朝夕之间。这使得舞鹤对台湾现代化情境的反思,超出了乡土—现代两元对立的简单格局。深藏于失散的人、失散的古典、失散的自由与创造力之间的“悲伤”,将使《悲伤》在更久远的时空中存留。
几年后,舞鹤又以《舞鹤淡水》再次回顾淡水小镇在台湾经济起飞中的“历劫史”, 有意从日常生活的层面将淡水和作家之间的关系做一番清理。公共空间的喧嚣变动与私人领域的情欲冒险交相映衬,淡水与叙述者的生命在十年间同步演练。作为舞鹤的第一部长篇,《舞鹤淡水》的意义更在于以“情欲书写”引导对其美学的追索。情欲的百般试炼、书写中,有惊人的创造力:《逃兵二哥》中“我”那伸向女人的手是一种委琐而可怜的求救姿势,而在风尘二姐与英雄二哥自我禁闭的情人洞房里,食与色是对无所不在的体制的对抗;《调查:叙述》中,那与国家暴力的血腥屠杀一墙之隔、同时进行着的剧烈动荡的欢爱,不但让人免于死亡,更在历史的恐怖中为草芥之民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记忆版图;《拾骨》中眷恋母亲的孝子,将乱伦冲动寄托于妓女之身,于猥亵中表达母亲/母土之狂恋;《悲伤》中“我”的萎靡与纵欲散发着末世的颓废气息,与“你”那禁闭、治疗皆无法压制的勃勃性欲相对照,对性的崇拜几近图腾化;到了《鬼儿与阿妖》,舞鹤干脆提出“肉体自主”、“肉体有其完整自足性”,有意抛开情的羁绊来创造一个肉欲的乌托邦。《舞鹤淡水》是一个集大成,最终落脚是生活的自由和书写的自由。这种书写实验,与“世纪末台湾”所盛行的“情欲文学”虽有呼应,但走得更远。在舞鹤这里,“情欲”不是人性解放,不是另类风尚,反而是实现最严肃的反省和批判意图的道路。
第六章卸除殖民历史重轭,回归祖灵之地——《余生》对原住民问题的思索
近十年来,有关殖民地历史与文学的研究,在台湾成为“显学”。 而在创作上,除老一代本省藉作家的“大河小说”外,当代作家涉入殖民历史题材的并不多。这固然是时代的隔膜使然,而殖民历史的幽微复杂,与现实政治的密切纠葛,或许是更深一层的“难度”。在此背景下,舞鹤的长篇小说《余生》(1999),尤其值得关注。本章在原住民文化复兴运动与“多元族群”的社会背景下,解读《余生》。90年代原运退潮之后,“原住民”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一种象征“进步”的社会观念。在大众文化的普及中,原住民及其文化被纯净化、神圣化,成了与现代物质文明的堕落、喧嚣对立的另一种“桃源”想象,有关的文学书写,不乏猎奇或心灵鸡汤般的消费性质。在学术的层面,则被“知识化”,被供奉起来。也因此,原住民可以轻易成为“多元族群社会”的点缀。
在这种背景下,最初进入屏东的好茶部落,舞鹤对汉族知识分子的位置和可能性,便有其反省。《思索阿邦·卡露斯》里,阿邦这个汉族“素人摄影师”,为鲁凯文化折服,通过自己的相机,拍下族人最生动的日常瞬间,与致力于鲁凯历史文化整理的“民间史官”卡露斯,结合为一个“新人”:“阿邦·卡露斯”。这是其时舞鹤理想中的原汉互动。阿邦作为一个“素人”,既非怀抱着人类学或社会学或历史学的臃肿的知识分子,指点原住民应如何如何;也不会以“原罪”感和“代言”意识而矫揉造作。到了《余生》,小说摆脱历来对日据时期“雾社事件”的残酷与传奇性的关注,贴近当代原住民面临的生存与文化处境。同时,《余生》质疑事件发生的“正当性”和“适切性”,不仅是以当代的价值观重新审视历史,更是以当下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包括弱势群体生存的、族群关系的、经济开发的、环境问题的,等等——来反溯历史的现场,从而触及到当代台湾未曾解除的历史重轭与现实问题。
综上,奇崛晦涩又富有生命力的书写,及其与现代台湾(文学,以及社会)之间密切而又疏离的关系,使舞鹤成为当代台湾文坛的一个“异数”,成为“90年代台湾文学最重要的现象”,也成为解读世纪末台湾的一个大有意味的入口。从“异质的本土”到“另类的另类”,舞鹤与台湾嘈杂的文化生态始终是一种似近实远、既亲又疏的关系。舞鹤创作具有现代主义的文本实验与批判精神,关怀的是台湾庶民生活的各个层面,又游刃于90年代台湾浓郁的后现代话语氛围中,由此所记录(或狂草)的当代台湾及其所背负的或远或近的记忆,往往给人面目怪异却又似曾相识的惊悚。它戏弄了我们的阅读惯性,又挑战着我们的思维惰性,然而当我们埋首于文字的刺丛,孜孜以求其真义的时候,却又发现,戏弄也好,挑战也罢,原来并非刻意。众声喧哗、全球互联的时代中,舞鹤不过是一个“择荒谬而固执”的书写者,以“田野”的双脚感知岛屿上的未知土地,以手工书写人心对自由的向往,以最无羁的声音,追问历史、社会、人性、欲望及其之于个体生存的意义。如此,秉持“邪魔”的巨大能量,保持一种永远的批判立场,对身处其间又游离其外的世纪末台湾社会发出孤独而不祥的声音——这是舞鹤生命存在的形式,也是他的文学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