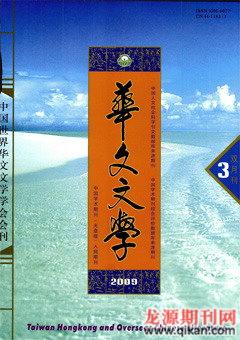摇曳在椰风蕉雨中的“南洋梦”
肖 成
摘要:林义彪长篇小说《椰风蕉雨白楼梦》讲述了一个华人家族数代奋斗,终于实现“南洋梦”故事,其意义不仅在于构筑了一个关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多重寓言,更重要的是此文本中还积极倡导“和解共生”与“悦纳异己”的21世纪新思维,清晰勾勒出了海外华人逐渐融入“全球化”的轨迹。
关键词:林义彪;南洋梦;和解共生;悦纳异己
Abstract:Lin Yibiaos novel The Wavering Dream of the White Chamber recounts the tough journey that a Chinese family goes through and eventually succeeds in realizing their “Nanyang Dream” at the cost of hard work by several generations. Its significance lies not only in its construction of a multi-allegory about history,reality and future,but also in its advocation of the new-centurial ideas of “reconciliation and coexistence” and “tolerance and acceptance of difference”. It depicts such a harmonious picture of overseas Chinese gradually melting into the globe under the climate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Lin Yibiao,Nanyang Dream,reconciliation and coexistence,tolerance and acceptance of difference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09)3-0081-07
长篇小说的昌盛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学成熟的标志之一,印尼华文文学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一翼,其长篇小说的发展也必然会经历这样一个从荒芜到逐渐兴盛的过程。印尼华人老作家林义彪先生的长篇小说《椰风蕉雨白楼梦》,可谓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当代寓言”文本。在当今这个倡导“和解共生”与“悦纳异己”新思维的世纪中,重新审视它,很容易就发现其独特历史前瞻性,其特别意义在于:这部小说构筑的文学世界在发生的刹那,就已成为了镌刻于物换星移、沧海桑田的历史坐标上的一则新传奇。它的确带来了别一种角度、别一种辩证、别一种洞悟,与以往人们对海外华文作品的认知大相径庭。它通过一个华人家族故事讲述了一个关于历史的过去与明天、关于拯救过去和走向明天的寓言。这一寓言中或许浸透着幽愤,浸透着无以填补的缺憾,浸透着不堪回首的记忆和埋葬在记忆中的刀光血影,浸透着“以德报怨”的中华传统文化,浸透着作者从这一切中提炼而出的痛苦的清醒。但是,有一条是千真万确的,这里没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自怨自艾,也没有流不尽的苦难哀矜之泪,因为作者眼中有着比怨艾和眼泪更重要的东西,那便是《易经》开篇所述之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它不断强调的是如何紧紧把握住——在历史和现实流变中未曾昭明的不断流变的人生和普泛性命运的轨迹。
毋庸讳言,只要是作家,其创作意图显然均欲以自己的作品参与历史的进程和社会舆论的塑造。这不单纯是为了记录历史,更是为了赢得讲述历史的话语权,因为历史是人类最后的精神归属地。而长篇小说显然更为容易达成这一目标,因为追求宏大的历史叙事一直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传统之一,创作出一部“史诗”式的鸿篇巨制也始终是作家的毕生追求之一。这种重要传统和毕生追求不仅表现在作者对历史框架的文学建构方面,而且更重要的还体现于作者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和历史经验的复制上面;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了人们对文学的想象,甚至还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此,著名作家沃尔夫曾打比方说,文学就像一张悬在空中的蜘蛛网,它的四角还是很微妙地挂在什么地方,还是和生活有联系的。这点从小说的叙事模式和结构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采用的不是东方“串珠式”的传统线型结构,而是“攒聚式”的网状结构。这种结构模式有点类似蜘蛛织网,不仅使小说中的重要事件、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能够在中国大陆、南洋群岛和香港三地展开游刃有余的演绎,而且还可以使这部人物众多、事件纷繁的小说在叙事方面占有某种优势——杂而不乱。从小说人物关系来看,该家族颇为庞大,家主白大头先后娶了两房妻室,原配周银妹,续弦蓝妮,共育有“文武英雄豪杰”五子一女。他们分别为长男白伯文,娶妻李淑美,育有一子白小亮,长媳则为美国波士顿一家银行副总裁之女露丝;次男白仲武,娶日本侵略南洋的“皇军”之女田中幸子,育有白希凡和白小娟两个子女;三男白文雄,娶具有深厚政治背景的卡尔蒂尼为妻,育有白梅、白兰一对双生姊妹;四男白文豪,娶马丽亚为妻,育有白大头最疼爱的两个孙子叮叮和;长女白文英,嫁给知名律师周密,无子女。五男白文杰(苏文彬),未婚,因不知情与同母异父的妹妹燕妮相恋。此外与白氏家族有密切关联的人物,还有同白大头有着45年深厚情谊翁东·普提曼一家以及当地华人富豪周友良一家,以及白大头在当地的几家儿女姻亲。在围绕白家展开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的纷繁复杂的关系网络中,作者竭力表现的不是“白氏”家族在历史长河中沉浮的规模和气势,而是通过白大头数十年来耿耿于怀要建筑一座“白楼”来作为维系家族纽带,使之成为“白氏发展公司”象征的梦想的逐步实现过程来反映时代世情的变迁,因此小说关注的重心不是那些具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商业或文化事件在故事中的作用,因为那些所谓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些塑造和诠释人物形象时的背景资料,如经济危机、环境污染、政治贿选、自然灾害、劳资冲突、“空巢”家庭,以及殖民依附经济的危害等,这些20世纪冒出来的典型历史事件,小说中虽有所涉及,却非小说反映的重点。作者更为关注的是白氏家族每一个成员的独特姿态和神情,是他们每一个人如何地介入到“白氏发展公司”这艘家族商业“航空母舰”当中的行为、选择和位置。而也正由于作者的这种特殊关注立场,使得作者笔下宏大的历史叙事走向了表现个人的主体主义叙事之路。也就是说,主体主义叙事在历史情境中得到延展,并不断构成历史本身。这在小说所塑造的一系列具有典型形象中得到了生动诠释。
若从作者表现人物的文学手法来看,其功底确实十分深厚,深谙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文艺美学的核心理论,着力塑造了一系列“扁平人物”——性格单纯一致的人物,白大头、白伯文、白仲武、白文豪、白文英、白文杰(苏文彬)、燕妮和蓝妮;以及“圆形人物”——性格复杂矛盾的人物,白文雄和周密(周子建)。在众多形象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白大头、白文雄和周密(周子建)三个人物。相对于白伯文的自私悭吝、白仲武的豪爽自信、白文豪的聪明机智、白文英的热情犹豫、蓝妮的温顺坚韧、燕妮的美丽纯真,以及白文杰(苏文彬)的善良博学,小说主人公白大头最能打动人心的是他的高尚品德——无论在何种历史情境中都始终不忘对中华民族传统“道义”的坚守。小说以浓墨重彩精心编织了系列情节,描绘了白大头对友情的执著、对爱情的忠诚和对家庭的坚守。作者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侵略南洋的日本“皇军”宣布投降的前夜,白大头不仅坚决不肯出卖杀死“皇军”田中武夫的土著朋友翁东·普提曼,还以其智慧化解了拉哈尤村所面临的一场大屠杀的危机。对白大头而言,帮助土著朋友和村民,这不仅是对友谊的坚守,更是对道义的坚守。然而更打动人心的是白大头对爱情和家庭的坚守。年轻时,单身流落南洋的白大头面对土著少女苏米亚蒂的真情示爱却委婉地拒绝了。他宁愿在孤独寂寞的思念中苦捱,也决不稍微放纵自己,对家乡的妻子保持忠诚,这等情操和这般道义的坚守确实令人敬佩。而儿子白文豪的一段话更能让人们进一步领会到白大头的人格魅力:“在对待婚姻和家庭上,爸爸更是难能可贵的。我听爸爸说,他十七岁和我妈结婚不上半年就逃壮丁逃来南洋,1935年回国不上一个月又被保长敲诈勒索逃了出来。1950年爸爸回国接了妈妈和大哥二哥来南洋后的五年间,是爸爸的家庭婚姻生活最美满的时期。哪知好景不长,1955年我两岁时,我妈妈又死于火灾。由于翁东·普提曼一再劝诱,加上那时文英姐、文雄哥和我都小,所以爸爸1956年,娶了蓝妮婶。但过了半年,蓝妮婶又不知去向了。你们算算看,爸爸和我妈结婚到现在50多年,真正享受婚姻生活只有六年。古书上有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的记载,是否真有其人也无从稽查。而现在活生生的例子就在我们的身边。几十年来爸爸是怎样地克制自己呵!”而且,每当白大头希望有生之年看到他的“白楼梦”实现时,总是不忘不明失踪的妻儿。他和儿子文雄对谈的场景是这样的:
“自从你妈妈惨死于火灾后,我们家庭就全靠蓝妮来料理。那时还炒咖啡粉;几个月之间就赚了一笔钱。可是,就在我们白家复兴的时候,蓝妮却失踪了。蓝妮在的时候她曾经对我说,她会做虾片。但是做虾片,需要宽大的晒场。所以,我失望之中,一连买了这两块地,借用翁东·普提曼的名字。我总是希望蓝妮会回到我身边……蓝妮! 还有她腹中的孩子!”
“‘爸爸!白文雄也不知道怎样来安慰自己的父亲。早在十几年前,文雄懂事时,他就劝爸爸再娶一个。可是爸爸的心中只有蓝妮。爸爸盼望着蓝妮会回来。可是,等啊,等啊!已经廿五年了。人生有多少廿五年呵!文雄望着爸爸陷入沉思的神情,心中感到无限的惋惜和悲哀。”
是啊,“人生有多少廿五年呵”!的确只有这样对“道义”始终不渝的坚守才能使他们一家的最终团圆震撼人心。就在这廿五年的漫长岁月中,蓝妮被陷害绑架而被迫流落异域他乡的痛苦挣扎求存;白大头的痴情不改和苦苦寻找,都不仅一再激起人们心底深处那根感动的“弦”,还使我们在小说中真的看到了每一个鲜活的个体生命是经过了怎样痛苦的挣扎才获得了不易的新生。白大头和蓝妮这对夫妇在坚守中经历的深哀巨痛,一度可能遮蔽了照耀在人间的阳光和温暖。然而,我们终究还是在白大头这样的中华文明和文化传统的坚守者身上看到了明媚春天的美丽,感到了阳光洒在身上的温暖。白大头对蓝妮数十年不变的眷恋和孜孜寻找,实际上已使他成为道义和温暖的象征或化身。而白文雄是整个故事中最具有“现代性”色彩的人物,他一出场就带有游戏人间的意味,早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时,白文雄就被称为“情场圣手”,一副放荡不羁的公子哥面孔,不仅未婚先有子,而且同贤惠的妻子卡尔蒂尼生下一对双生姐妹花的同时,仍然不改随时随地拈花惹草的习性,还瞒着妻子同女秘书尼亚蒂搞婚外恋。白文雄确实是一个相当成功的现代商人和企业家,与坚守中国传统道德婚姻观念的白大头完全不同,他的情感生活确实是相当紊乱多姿的,他的婚姻情爱观是全盘西化了的,虽然小说最后让白文雄妥善地处理了他的多角婚恋关系中的诸多麻烦,但是他确实是作者创作出来的一个超脱出读者“期待视野”的一个现代性意味特别浓厚的人物,是“白氏家族”人物形象中的一个“异端”。至于周密(周子建)这个人物,则最能凸显作者塑造人物的深度和力度,虽然这是一个令人极端憎恶的反派人物,身上充满了虚假丑恶。小说主要运用了两个章节的文字来加工这个形象。一是通过蓝妮的回忆片断来间接刻画;一是运用人物自杀前对自己一生的直接回顾,将这个绑架贩毒、杀人越货、作奸犯科、诱骗伪善的恶棍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对于已是人到中年的著名律师周密而言,他是燕妮和哈娜两位少女眼中亲切慈祥的长者,对于被诱骗成婚的妻子文英来说他是“同床异梦”的丈夫,对于偷情对象萧丽芬而言,他是个慷慨的情人,自杀前还给情人留下了五千万盾的现金支票和一粒钻戒。在青年白文杰(苏文彬)面前,周密则是雄辩滔滔、主持正义的成功律师;可是对于备受摧残和惨遭蹂躏的蓝妮来说,青年周密——周子建则是她一生都无法忘记的“噩梦”,对于白大头来说,周密既是曾经一度令他满意的女婿,但又是侮辱和损害他和妻子幸福的刽子手。小说精心刻画了周密(周子建)这个人物的多副面孔,虽然花费在这个人物身上的笔墨并不算最多,但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周密(周子建)这个人物不是一个单一化的形象。在周密(周子建)这个人物身上,他的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其中既有命运冲突的成分,又有自身性格中善恶因子之争,还有与之伴随而来的患得患失的矛盾心态。以至于周密最终选择了以车祸自杀的方式来结束其罪恶的一生方式,也可以有多方面的解读:从主观自利的立场上看——周密的自杀,既保住他本人的声誉和体面,又逃脱了后半辈子身陷囹圄的监狱生涯;从客观上看——周密自杀,不仅使岳父白大头、蓝妮夫妇保住了面子和名誉,同时还使婚姻出轨的妻子白文英获得了解脱;更进一步说,还令未知的私生女燕妮不必在生命最后时光中再受一次致命伤害。我们之所以能够毫无疑义地说,周密律师是这部小说中塑造的一个最为成功、最具有代表性意义、最丰满生动的“圆形人物”,是因为周密律师确实是这部作品中性格得到了最为深入开掘的一个典型形象。通过白大头、白文雄和周密这三个人物,很明显可以看出,作者采用的这种主体主义叙事一方面强调的是历史人物的个体性,之所以是个体的,就是想表明——只有这种确定了的个体,才能证明历史是鲜活的、流动的、富有感情的,而现实也就变成是可以把握的,而未来亦是可以期待的;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以主体主义叙事方式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也于无形中进一步增加了小说的魅力。
恩格斯曾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这部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总是能从历史意蕴出发,尽量观照到人在历史发展中自我选择的可能状态,并按照作者的审美理想去营造历史细节。其核心是追求人的基本属性,也就是在物质流和时间流中,人是以一种怎样的状态存在着。虽然文学是通过审美改善世道人心的,是通过对美好事物的描述来塑造灵魂的,但传统悲剧中那种哭泣的、颤栗的形象就一定会实现这种承担吗?不见得!小说中的蓝妮和燕妮这对母女的形象就打破了人们既定的认知经验,却同样承担起了引导人心“弃恶向善”的神圣使命。从贯串全文的蓝妮和燕妮这对母女的爱情故事来看,无论母亲,还是女儿的身上都流淌着浓厚悲剧意味。她们爱情之路都颇为坎坷。母亲蓝妮虽然在小说中正面出场的章节并不多,但却是小说网络结构中的核心人物,因为这个地道的南洋土著女性的命运联结起了白氏家族及其亲戚朋友等一系列重要人物。小说采用了类似侦探推理小说中“解连环套”的方式来推进故事进程,藉由蓝妮出场推出一个又一个悬念,然后又一步步揭开谜底。蓝妮少年丧母,寄居于白大头家,自小就辛勤操持家务,16岁豆蔻年华时成了40多岁白大头的续弦,刚刚怀孕却因美貌而遭亲戚陷害,被绑架到香港成为毒贩的“性奴”,惨遭蹂躏摧残,亲生女儿燕妮一出世就被迫送到孤儿院去,因为她无力养活两个孩子,当她好不容易逃出毒贩的牢笼,却只能隐姓埋名地流落到香港成了女佣,孤单艰难地抚养儿子白文杰(苏文彬)成材,身心备受煎熬之下却始终无法回到南洋的家。在历经了25年的岁月风霜洗礼之后,这个受过最深重侮辱和损害的女性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终于与丈夫白大头团聚了。可其复仇对象周密(周子建)律师却没有给她讨回公道的机会就自杀了。对蓝妮来说,这样的人间确实不公平,她却并没有过多抱怨。她的遭遇确实令人唏嘘不已,但小说赋予她的却不是一个哭泣、颤栗的软弱形象,而是一个温顺美丽、善良勤劳,又坚韧不屈的形象。女儿燕妮同样是一个悲剧人物,她一出生就打上了不幸的烙印,她是母亲被恶棍周子建强暴后生下的私生女,无力养活她的母亲只能将其送走,成了一个被遗弃的孤儿。初尝甜美爱情却又痛失情郎路迪·普提曼;然而她的不幸并没有到这里就结束,当她再次从香港电脑工程师苏文彬身上收获新的恋情时,却又发现患上了白血病,虽然她积极配合治疗,但终究无力回天。后来她又发现自己和苏文彬是同母异父的兄妹,根本无法获得“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幸福机会,虽然在生命最后一刻,终于和生母蓝妮相认,但燕妮还是死于白血病,带着无限遗憾结束了她若火花般短暂的青春、爱情与生命。蓝妮和燕妮母女两人一生遭遇到的不幸是如此之频繁,有时不禁会让人在阅读中对作者产生某种“怨怼”情绪,作者为什么要这样虐待这对真善美化身的母女呢?到底它们母女所受的伤害和不幸何时才是个尽头呢?也许作者的意图就是想淋漓尽致地贯彻那所谓的“悲剧就是把美丽东西摧毁给人看”的艺术原则吧。然而不管读者怎么想,燕妮最后在慈善晚会上那优雅得宛若“天鹅之死”般的最后一舞,则为这首凄凉落幕的生命挽歌抹上了几缕美丽的夕阳余晖,令人于人生无常的惆怅中沉思人生价值。引人注意的是,燕妮虽遭遇了命运悲剧,却也同蓝妮一样,不是以哭泣、颤栗的面孔站立在人们面前的,而是以柔美聪慧的精灵形象,承担起了引导人心向“真善美”方向发展的使命。此外由于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或隐没了历史背景,没有在文本中试图建立宏大历史结构,而仅是确定一种特殊的历史情境,描写在此情境中人的自由选择和所受的制约,致使在探究关于白氏家族未来将如何发展和走向问题上,作者亦无法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只是给出了某些可能的暗示;尤其是在经济和文化面临全球冲突窘态的当今社会,若硬要作者从纷繁复杂的事实中给出一个确定的途径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小说在暗示某些可能性答案的同时,其实也在进行着新提问;而且还使我们认识到每个历史时段都会有基于当下生存世界和现实境遇而产生的新的关注点。就作家而言,重要的不是作品解读的年代,而是解释作品的年代,文学创作虽然是人们认识历史,把握现实的一个出发点,但它并不是在文学叙事和历史记录之间完成一种简单综合,事实上那是复杂得多的事!
尽管如此,这部小说还是如同许多西方作家创作的移民新大陆,白手起家,终于走上成功之路的“美国梦”作品一样,对20世纪南洋华人的创业史做了极为生动的演绎。或者说作者其实讲述的就是南洋华人白手起家的“南洋梦”,是一则关于如何通向成功之路的南洋华人的“新传奇”。作为常识,虽然我们都知道人类发展的历史和文学中的历史本来是由两种历史构成的,也就是说,我们既不能将社会历史当做一个确定无疑的文学文本来阅读,也不能把文学中的历史当作现实的历史来阐释,尽管历史充满了想象,但历史只可想象而不可经验。前者的任务是由历史学家来完成的,后者才是文学家的责任。因此人们非常愿意在文学作品中经验着我们现实的历史,并以此来评判作品的好坏和得失。这部小说就使我们有了一个亲历和体验历史的大好机会。小说是在浓郁的南洋热带风情习俗背景的映衬下,娓娓述说了一个飘移到海外的华人家族将其“南洋梦”成功变为现实的奋斗和开拓历程。白大头和他的儿子们的创业故事并非一帆风顺,也经历了几起几落的风霜雪雨。白大头曾多次回忆往事:“我一九三○年来南洋,在周家碾米厂当了五年的学徒和伙计。对!对!就是那一年我积了一些钱,回中国去探亲一个月,然后再到南洋时就住在你的老家拉哈尤村。那时,我手里只有一点钱,收购转手一些农产品、象咖啡、玉米、辣椒之类,还顺便放一点债。” 当生计刚开始有所好转时,白大头却遭遇了火灾,承受了丧偶之痛,续弦不久又遇到严重的商业欺骗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几乎使他彻底倒下。这可真是“屋漏偏逢连天雨”啊!在此后岁月里,他又遭遇了被亲侄子设计陷害,怀孕的妻子遭绑架流落香港,夫妻父子被迫分离长达25年的梦魇,虽然终于全家“团圆”了,但白大头坎坷一生方实现的“南洋梦”中留下的遗憾恐怕比幸福要多得多吧。白大头次子白仲武的创业历程也与其父相类似,几经沉浮才成功。白仲武曾不无自豪地讲述了白氏一族“白手起家”事迹:“就说我的爸爸吧!青年时他避壮丁,来到南洋,还不是只带了一双手吗?以后积蓄了钱,回到闽南,带了我妈,我哥和我来南洋。以后又生了我的弟弟妹妹。我们家几次三番的被抢劫,遭火灾、水灾,爸爸失败了又站起来。我的五个兄弟中,我和文雄弟多多少少受到环境的帮助,不足为例。我的哥哥伯文、妹妹文英和弟弟文豪都是靠一双手创造出一番事业来的”。小说就是这样采用直接和间接两种艺术手法来烘托这个创业艰难、守业不易的“南洋梦”。这个掩映在“椰风蕉雨”背影之下的“白楼梦”,的确可以作为千千万万海外侨民和华人“寻梦”历程的文学写照。而也正因为作者所叙述的这个“南洋梦”中所蕴涵的南洋华人社会历史内容和人生命运成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才使得我们对这一段的历史认知确实具有了重新亲历的意义。
虽然在我们的记忆中,几乎所有关于历史的写作都会带有作者强烈的主观情绪,常显得缺少默默的静观和承担;然而同样是面对历史的写作,这部作品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文学肚量和承担历史的勇气。在小说所叙述的故事中,彻底“背叛”了我们已知的历史经验,也完全“背叛”了我们的生活经验。众所周知,海外华人,特别是印尼华人,在数百年的异域生存挣扎中,遭遇过无数次灭绝人寰的大屠杀、暴力排华、华文禁绝,以及种族歧视等不幸事件,这使他们不得不在生存现实逼迫和历史风雨吹打中自觉地选择为自己所属的族群言说他们一再遭受到的种种反人类迫害和不公正待遇,希冀讨回一些迟到的“公理”和“正义”,这是人之常情,理所当然、无可非议的事;然而这部作品却并没有全然沉湎于这些血泪斑斑的感伤烙影与苦难创痕之中。因为作者在重祭历史大旗时,他查看的不仅是这面大旗上所染的硝烟和血迹,而且还要翻出这迎风飘展的大旗阴影所遮蔽的文化,因此它不断透露出来的是一种崭新的思维——“和解共生”与“悦纳异己”。譬如白大头的五子一女中除了尚未结婚的小儿子白文杰,嫁给周密律师的女儿白文英、和娶了同是南洋当地华人之女的长子白伯文和四子白文豪之外,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和长房长孙的婚姻都属于异族通婚或跨国姻缘。次男白仲武娶的是日本侵略南洋的“皇军”之女田中幸子;三男白文雄所娶的妻子则为南洋当地的原住民女性;而长房长孙白小亮更是娶了美国波士顿一家银行副总裁之女露丝为妻。不仅如此,随着时代发展,人事变迁,白大头一家的身份和心态也早已有了巨大改变,虽然还是念念不忘坚守民族的传统和传承中华文化的薪火,但是他们全家人可以说都已经确确实实由“落叶归根”的“侨民心态”,自然自觉地转变为“落地生根”的“公民心态”了。而且作者还一再叙写了白大头和翁东·普提曼一家长达45年的深厚友谊,如此渊源流长的两族友谊宛若涓涓细流,又如春雨润物早就渗透到了他们和他们的后代的骨肉血脉深处了。故而白大头和翁东·普提曼在一起时,常出现这样的闲聊场景:
“你还客气什么呢!我和你几十年住在一起,早就是一家人了。”白大头说:“二十五年前我们一起从乡下你的老家搬到这里来,你放弃了的士司机不做,帮助我这个咖啡厂,你的太太把文英、文雄和文豪当成自己的儿女。一个个抚养成人,说实在话,伯翁东啊,我们已经糅合在一起,分不出彼此了。”
“说得对呀!印度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几百年来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翁东·普提曼的一杯酒下肚,话也就多起来了。“我从国家博物馆那里知道,公元一四O五年,你们的明王朝的使者就和我们这里的马差巴王朝有了联系。以后你们的三宝太监郑和先生几次指挥船队带着瓷器、丝绸等贵重物品来和我们做生意。我们两个民族有了将近六百年的友好的关系了。”
“这是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历史啊!”白大头说。
显然,小说中叙述的这些内容,涉及的不正是当今世界人们谈论得方兴未艾的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和解共生”与“悦纳异己”吗?而早在20多年前,林义彪就在其构筑的文学世界之中开始竭力倡导这种“和解共生”与“悦纳异己”的思想观念了,这实在是不得不使我们更加敬佩作者广阔而远大的前瞻性眼光和全球化意识。
总而言之,林义彪这部巨著《椰风蕉雨白楼梦》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历史小说所擅长的文本内部的“宏大叙事”,而是试图把以往对于南洋华人历史与文学中所忽略或排斥的东西结合起来思考,从而使那些藉由小说所反映出来的南洋华人历史中局部的、破碎的意义得到肯定,并由此开辟出自由交流和阐释文学文本的多重空间及多种可能性。但愿这部作品对处于边陲地带、屡屡遭受挫折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意义,不是某种期望的幻影,而是成为一种力量,成为响彻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飓风与海涛之上的一声震撼人心的惊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