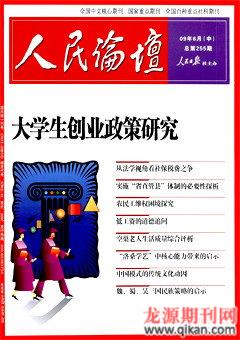农民工维权困境探究
叶 迎
摘要农民工维权遭遇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的弱势地位,无法对处于强势的企业和政府的利益偏向形成制约。因此,社会权利的平衡是解决农民工维权困境的根本途径与思路。
关键词农民工维权劳动关系参与主体
农民工在维权实践中的地位与行为分析
行为基础:农民工在劳动关系形成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在劳动关系形成过程中,农民工无法积极主张劳动法律赋予其的权利,对用人单位的权利侵害也常常采取不反抗的态度。这种行为的基础在于农民工在劳动关系形成过程中的弱势地位。在供求严重失衡的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在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之初就处于绝对的弱势。这使得农民工对用人单位严重依赖,很难具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不得不在职业选择、劳动报酬、劳动条件等问题上降低要求来迁就用人单位,不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行为选择:生存理性与成本收益分析。农民工权利受侵害后,通常都希望靠自己和雇主协商来解决。如果雇主合作,那么这种途径是成本最低的。但是,农民工自身力量弱小,很难对强势的雇主造成影响,雇主通常是不会选择主动赔偿的。此时,农民工可能的选择有:以合法方式寻求工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寻求司法救济、自行组织地域性维权组织进行维权等,或者以不合法方式进行暴力报复、破坏私人财物等。由于维权行动成本常常远高于收益,因此,农民工的维权行为很难进行。以工伤保险为例,其争议处理采用“一调一裁二审”程序,走完整个程序至少需要360天到510天。如果工伤者没有时间或经济能力去应诉,他们索赔的决心会因漫长的等待而动摇,最终只能接受用人单位极不公平的调解方案。
行为约束:维权的社会资源匮乏。首先,农民工经济资源缺乏。许多农民工的收入除了维持日常开支外,其余的基本上寄回家乡。这样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无力负担高昂的维权经济成本。其次,农民工群体意识薄弱,他们不愿意采取有失业风险的共同社会行动。第三,信息不对称。劳动者缺乏对制度规范、政策法规信息的掌握与理解。同时,农民工能力和资源的缺乏不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表现为他们的主观感受。在各种宣传符号的作用下,通过逐步的内化过程,他们逐渐认为自己是无助的、无奈的和被人遗忘的。他们既对现实不满又因无力改变而接受现实,其弱势地位也进一步加剧。
企业侵犯农民工权益的行为及其原因分析
目前,在劳动关系中,资本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劳动居于从属和被动地位,劳资力量对比失衡。同时,法律制度对处于强势的企业的违法行为,往往规定“限期改正”或“通报批评”,这种处罚力度不够,对企业来说无关痛痒。因此,用人单位常会因为违法成本小,而出现不签订合同、压低或拖欠工资、不为工人提供相应的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等行为。
企业侵犯农民工权益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企业掌握强势资源。这在某种意义上改变着制度环境。企业资本集团不仅掌握着经济资源,而且这种资源也相应地为他带来了另外两种重要的资源:文化技术资源和政治资源。伯恩斯指出,“在社会情境中拥有大量知识、较有权力的行动者,能够充分剥夺较弱行动者和其他知识较少的行动者的机会。”企业资本集团就是这种能够支配和改变制度环境的角色。掌握强势交易资源的企业,在市场上具备较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和改变市场交易规则的能力,他们往往可以按照他们的目的和利益,来逃避或变通制度对他们的约束,侵犯劳动者的利益。
政府在农民工维权中的职能与实际作为
政府在与用工单位的法律关系中,行使的是劳动行政管理权,其直接目的是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具体内容则是规范劳动关系中用工单位的行为,并排除其对劳动者正当合法权益的侵害。政府介入劳动关系,即通过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来实施对于劳动关系不平衡的矫正。这种介入的实质是以公法来限制私法,特别是限制私法中的核心权利——财产权。具体表现为对于私法的契约自由、财产绝对权、过失责任等原则的修正。这种修正以社会利益的保障为出发点,以劳工利益的直接维护为目的。劳动法的这种特点与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它更多地强调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对处于弱势一方的农民工提供优先保护和倾斜保护。这是政府在农民工维权中的应然职能。
但在实际作为上,政府很容易转变成一个利益主体,甚至与当地用工单位、农民工之间形成博弈关系。政府执法过严,会影响用工单位的效益进而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执法过松则损害农民工的利益和当地政府部门的形象。有学者犀利地指出,在政治过程和市场过程中,任何人都在寻求促进自己利益的目标,而在个人目标之外,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类似于“社会目标”、“国家目标”和“社会福利职能”之类的东西。地方政府及官员在其目标、利益与责任上存在矛盾和冲突,他们更趋向于追求自己的目标、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政府工作常常是低效率的,并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违规行为视而不见。
社会权利平衡视角下的农民工维权思路
通过对农民工维权过程中三方主体行为的分析,可见,农民工维权遭遇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的弱势地位,无法对处于强势的企业和政府的利益偏向形成制约。因此,社会权利的平衡是解决农民工维权困境的根本途径与思路,这有赖于农民工与企业的社会权利平衡以及政府强势在社会权利平衡中的消解。
农民工与企业的社会权利平衡。农民工弱势地位的形成,其核心原因之一是社会权利在配置和实现上的不平等,这是起点的不平等。因而农民工维权困境的解决,关键在于改变强弱分化的社会权利格局,使农民工与企业间的社会权利的平衡配置通过公正的制度来实现。制度的公正是多元利益主体多次反复博弈的结果。农民工的社会权利弱势无法与企业的强势地位抗衡,也就不可能平等地参与到权利义务配置的制度设计中,其平等权以及以此为前提的劳动权、社会保障权等权利也无从得到保障。因而,政府应当以保护弱者为原则进行制度设计和改革,矫正社会权利分配不公和社会结构不合理。
政府强势在社会权利平衡中的消解。如前文所述,若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转变为一个利益主体,其利益取向偏向用人单位,那么将产生权力和资本的联合,给农民工的维权行动造成隐性的障碍。维权过程中的农民工对政府的救济和强弱矫正尤其依赖。因而,政府强势的消解,是指在维权制度的运作中,政府应依照法治政府的标准,依照法定的行使权力的方式和程序来履行法定的职权和职责。政府是否越权和滥用权力由法律来评价,权力的行使过程及其结果受到法律的监督和控制,从而实现农民工与企业维权过程中社会权利的动态平衡。
注释
①汤姆·R·伯恩斯等著:《结构主义的视野:经济与社会的变迁》,周长城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73页。
②詹姆斯·布坎南,理查德·瓦格纳:《赤字中的民主》,刘廷安、罗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