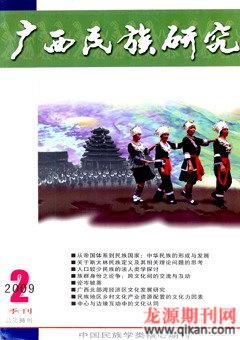《三千书》新探
摘要:《(三千书)初探》一文中认为《三千书》深受越南方面的影响,是越南字喃对地区性的方块壮字之影响的结果。实际上《三千书》的使用者壮族布傣族群的前身是越南的王族,《三千书》现象反映了布傣族群深厚的帝王情结。
关键词:三千书;布傣族群;帝王情结
作者:何明智,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广西龙州,532400
中图分类号:H2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2-0121-003
一、话题的缘起
《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刊登了戴忠沛撰写的《(三千书)初探》一文(以下称戴文),是迄今为止学界对广西龙州金龙镇壮族布傣族群民间保存的古籍抄本中的首次关注。文中将流传于广西龙州县金龙壮族民间的“一部汉字与方块壮字对照的杂字体字书”与越南汉喃字书《三千字》进行比较,从而得出“《三千书》乃以《三千字》为蓝本”,是受越南字喃对地区性的方块壮字之影响的结果的结论。同时,提出了《三千书》“到底是先写成于越南岱族地区,再传人中国广西的龙州县,还是直接于龙州写成的疑问。对于作者的这一结论和疑问,笔者难以苟同。
据作者介绍,《三千书》原为广西龙州县金龙乡(笔者注:应为金龙镇)立丑村逐立屯黄家豪先生家藏,1987年征集,今藏于广西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以前未见,是一本供初学者学习用的杂字体蒙书。对于该书的编写者,作者认为“书写这些方块壮字的人本身必对汉越语音有相当认识。甚至以汉越音作为读汉字的主要依据,而非使用邻近的汉语方言或其他壮语方言的读书音。此亦揭示了解读《三千书》之一重要法门,即其壮字释音,必须充分考虑该字在越南语内的汉越音,否则书中很多同类壮字之构成将难以理喻。”在这里,作者依据古代越南自创制喃字(或字喃)以后,为方便学习而编制识字本《三千字》的做法推论古代壮族地区仿照越南编制古壮字识字本《三千书》。实际上,古壮字也叫土俗字,它产生于唐代,盛于明清时期,是由壮族一些受汉文化教育的文人(包括民间巫师)借助汉字或汉字的偏旁部首创造的。壮族民间普遍用它来记录或书写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剧本、楹联、碑刻、药方、家谱、家族、契约、讼诉、经文、记财等。一个事实就是,古壮字的使用者一般仅限于有文化的壮人,他们本身已精通汉字,古壮字本身又是由他们自己创制的,古壮字从来也没有被当作一种正式的文字登堂入室,被官方正式推广过。而当时广大的壮族子弟,凡学习时必以习学汉文化为首选,而非选择自创的土俗字。究其原因,壮族人实际上都以能经常地使用外民族语言进行交际为荣,关于这一点徐松石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中将其归结为壮人开朗的民族心理和绝对开放的性格及吸收力的宏伟。以历史上的汉、唐等朝代为例,尽管汉武帝平定南越、东汉的马援南征时,都曾有意识地采取了“以其故俗治,毋赋税”、“与越人申明旧制”的宽松政策,从而保留了南越的奴隶制。但当时的汉文化已如春潮洪水,相当迅猛地占领了岭南广大的地区。到了唐代,壮人纷纷采用汉文汉字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致使大批的壮族文人如雨后春笋般脱颖而出。至柳宗元贬官至柳州时,岭南闻为士子者,一时间莫不离家奔走,“从宗元游”。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当时当地的壮族士子来学习“前景不明”的土俗字,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这也就是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古代广大的壮民族地区,从来都不需要类似《三千字》这样的一本蒙书,也从来没发现过这样的一本书。壮人在创制壮字时,往往随意性很大,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写法或不同的意思。例如,同样是汉借字“一”,在北壮有“一”、“一旦”、“将要”、“阳光”、“一会”等意思,而在南壮的左江与语区中,却单有“歇息”的意思。因此,制定一本“通用”型的字书实际上是行不通的。那么,究竟如何看待布傣族群的字书现象呢?这得从布傣族群的族源背景去考察。
二、布傣族群是壮族的一个分支
壮族布傣(或布岱)人现集中居住在广西龙州县金龙镇内中越边境线中方一侧,与越方一侧的岱侬族比邻而居,曾自报“苗族”、“彝族”,后来改报为“傣族”,1958年被定为僮族,1965年改为壮族,是南部壮族的重要支系。根据民间文献资料和口碑资料记载的情况,可知布傣先民迁入(进入)金龙的时间大致于明末清初之际,至今已有近20代约400年时间,壮族布傣是典型的跨境族群,至今仍与越南北部的岱侬族往来密切,“有田一起耕,人死一起抬”,双方村与村之间最近的距离仅1.5公里,其民间古籍文献中所使用的文字与越方岱侬族的完全一致,也与京族民间流传的喃字大体相同,而与古壮字相比,却差别巨大。例如,仍以古壮字的汉借字“一”为例,也表达“最小的正整数”这样的意思,与汉义的相同,而在布傣和京族的哺字中均没有“一”这样的写法,表达“一”的意思时,其喃字写成“悖”或“爻”、“漫”(从中可看出不同喃字间的差异性),读音均为越音mot。由此,我们可以推定布傣族群民间中所使用的文字就是“岱侬喃字”,也就是傣喃字。
壮族布傣历史上的归属问题比较复杂,金龙历来为中国国土,但清朝时由于地方统治者的腐败,曾一度将金龙外借抵债,直到中法战争之后,1892年中法双方议界时,由于中国方面的坚持,金龙最终才得以回归祖国,这使得布傣人在历史上经历了“中国一越南一法国一中国”几个特殊的阶段,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也屡次听说过去布傣人所交的公粮均挑往越南的下琅县,显示出其回归前确为越方所辖。此外。布傣族群的身份也较为特殊,根据1998年广西民族大学组织民族学专业师生到金龙开展田野调查所得的结论,布傣人迁来金龙的情况虽然有多个版本,然而最令人信服的则是当时的横罗村党支部书记沈汉卫关于当地傣人来源的传述,即其祖上为明朝时越南莫姓的权贵,其家族因与黎王争权夺位失败而被迫逃亡,其中的一支成为现今金龙布傣的祖先。特殊的身份决定了布傣人至今在生活诸多方面仍处处流显露出其王族“做派”,例如族群中十分注重族群文化的延续性,并通过字书等方式普及具有族群特性的“帝王学”教育等等。据调查,清代以前布傣乡村中普遍开设喃字识字课程,并依据18世纪越南著名学者吴时任编纂的《三千字解音》(又称《字学纂要》)编制了“岱侬喃字”体系的《三千书》(或《三千字书》)。前者“是一本汉字与越南喃字对照的启蒙字书,采用字义相随的方法,以押韵的方式将汉字和对应喃字编为四字句,方便背诵。其中每句第一字是汉字,第二字是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喃字,第三字是和第一字意义有关联之汉字,而第四字是与第三字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喃字。句与句之间押尾腰韵,即第一句的第四字与第二句的第二字押韵,第二句的第四字再与下一句的第二字押韵,如此类推。”《三千书》仿其体例,“书内每字条由三部分所组成,大字属被解释字,为汉字,其下双行小字中,右行为越南喃字,左行为方块壮字(笔者注:应为岱侬喃字),其内容分别为汉字的越南语与壮语(笔者注:应为傣语)同义词。”这种民间自发性学习的情况,在同居一地的侬人、广人中从未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