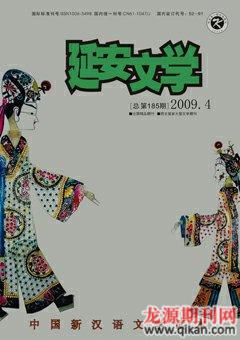黄土崖(外一章)
郭 群
家在沟畔。黄土坍塌,形成模样儿各异的崖壁断面。那些印象深刻家乡的脸,总让你怀疑是上帝疯魔所致。他挥将刀斧,昏天黑地一阵乱刺乱砍,便给大地胸脯留下如此巨大、如此深刻的创痛和裂痕。
住在沟畔,守着他们的棚屋和窑院,从幼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一茬茬地生,一茬茬地长,一茬茬地老,一茬茬地由生到死,不知不觉,地老天荒地变换呐!
短短的三、五十年,一眨眼地过去。从沟畔走出去再回到沟畔,保准让你成为乡音未改的外乡人。儿时的伙伴,也不过一夜之间,青丝变白发,秃顶的,驼背的,豁牙露气的,再看那不敢相认的脸,全都沟壑纵横,显示着饱经沧桑和风雨剥蚀既久的崖面。
崖面没有喜悦,似乎也没有忧伤,说不上苦辣,也无所谓酸甜。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一切都全无知觉,一切都跟平常日子一样平常。平常得让你不由得要心悸打颤,忽然就觉到,内心有什么东西轰然坍塌啊……
于是,你就由不得地要凑近了去细看他们。
结果,出乎意料。因为你最终看到的居然不是他们,而真真切切竟是你自己——你自己的混沌,你自己的漠然,你自己的蹒跚,你自己的苟且和随遇而安!
你在颤栗中无可奈何了。你清清楚楚地看着有些东西,就那么走远了。是背着生的旗帜向死走去,永劫不归,不再回头!就像站在故乡的沟畔,你却再也回不到故乡里去,而只能是一个永失乡土的流浪汉,而且差不多还是一个孤儿。这一切,都那么确定,真实无疑。有些东西,看起来依然活着;有些东西,却已经悄然地死去;还有些东西,则继续像死一样地活着。
就是这样。
就在沟畔村子的某个地方,坐落着另一个村子。那里有你至死魂牵梦萦的双亲,有许多的亲人和乡亲,他们鲜活地深居在那个被叫做坟地的村里,但却始终对你关闭着探寻的门。你当然知道,死亡的壁垒,对你来说比纸还薄,像对一切一无所有的穷汉那样,几乎等同解脱和救赎。一只黑白相间的杂毛狗发现了你,它机警敏捷、亢奋豪勇,远远地狂吠着向你扑来,亏得主人及时出现,大声喝止,才乖巧驯顺,十二分献媚地向着主人摇尾乞怜,但同时依然不忘掉过头来,对着你压低喉咙,发出示威性的怒吼!
正是这样一只有归属的狗,和一个没有归属感的你,彼此权衡之下,让人着实吃不准谁更不幸,或者说谁更幸福?
巨大的疑问,一如你面前无法填充的深沟巨壑。你和阅世千年万载的黄土崖久久地相对凝视,但只是无言。
日子如水土
泉在沟底最幽深的根处。
站在沟畔看,泉是一颗星子,一明一灭地闪烁。及到跟前,才得见是面一尘不染的明镜。镜里,有一眼看不穿的深邃,微微晃荡,生怕惊扰了梦境似的,轻漾着蓝天、白云、红花、绿树,一幅幅景象。当然,还有人脸、狗脸、驴脸,偶或,还有狼和狐狸狰狞狡猾的面孔……
是因为泉,荒凉空寂的沟,曾经怎样地繁荣热闹来着!人喧马叫,四邻八乡的老少,挑的、背的、抬的、用牲口驮的,沿着弯弯曲曲的沟路,把那些源源不断,永远勺不完、挑不完、运不完的清泉,分别请回自家的缸里、瓮里,盆、碗、桶、罐里,一户户全都小心金贵地守着。你来讨要铜钱、饭食,都可以给,只有泉水吝啬,万不得已,是绝不会赐舍点滴去的。
怎的如此?
是泉水神奇着哩!没见沟畔的男人,全都健硕壮美,而女人水灵鲜俊,连笑声都比别处的女人响亮清脆么!据说喝泉水长大的人,到老百病不生,平日里稍有头疼脑热、眼疾腹痛什么的,用泉水洗洗,或喝几口泉水,都会立见奇效。
所以,泉曾经叫作过神泉,曾是沟畔人家的荣幸福祉。当然,也曾是他们的不幸和伤痛。战争年代,沟畔的村子正好处在“红白交界”的边区前沿,为了不让前来烧杀抢掠的白匪喝上和玷污泉水,村人们宁可饮用混蚀肮脏的窖水,硬是断然毁了神泉——他们用石板封死了泉眼,然后给泉覆上了厚厚的黄土。据说,仅仅是为此,村上就先后折过七条人命……
后来解放,神泉重新开启兴旺,但不久又遭遇“革命年代”的红色风暴,神泉被视为“迷信四旧”,再次废弃“扫除”——泉眼被喝泉水长大的“红卫兵”们,绝然捣毁,沟路也被人为掘断毁坏。再后来,村上就有了深达百米的机井。而等到机井供不应求,终于抽不出水的时候,沟畔人也开始像城里人一样,喝上了百里之外引来的“自来水”——方便自然是十二分方便,在自家的锅台上一扭龙头,水就可以哗哗地无节制地奔流出来。只是人们饮用这样的水,还是感叹有些咸涩。他们说,那有咱们的泉水好呢,那可是一准的甘醇呢!
听起来,像回味和赞美某种名贵的佳酿。
到再后来,慢慢地,连这样的感叹也听不到了。缘于淡忘,人们早已习惯了漠视许多其实不该漠视和淡忘的东西,比如身边的沟底深处,像女人养育生命的私阴之地,那一眼圣洁神奇的清泉。尽管,它于今已被黄土崖的多次崩塌,深埋于九层粘土之下了。
但它还在。不死的泉,顽强坚韧,这里那里地,从崖壁石缝渗出一股股细若游丝的水注。它们潺潺汩汩,汇集成沟壑底部一条淙淙流淌的小溪,日夜不停,载着四季变幻的无数日子,向着远方的大河一路赶去……
流不走的,是那些享用泉水滋润的黄土,春夏秋冬,枯荣之间,在阴晴雪雨中,变幻着生命的颜色。当然,还不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