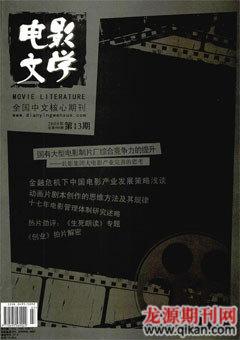论音乐在电影中的叙事要素
方 倩
[摘要]电影音乐已成为影片叙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并为提高影片的美学价值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可以将其他艺术转变成为自己的叙述对象,观众在观赏影片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受到电影音乐的感染。在陈凯歌所改编的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文学作品叙事中的淡化与回避的歌唱与演奏都进行了有效的再现。
[关键词]音乐;电影;叙事要素
音乐在形式趣向影片的成归化运作中,常常是一个独立的叙事要素。这使音乐摆脱了画面的附庸地位,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与深度。更符合音乐本身的抽象性与暧昧性。正因如此,音乐为观众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得到更多的启示,读出“不在场”的作者对这些画面之所以如此安排的寓意。并由此激发出自身的评判。克劳迪亚·戈布曼说:“在我们认识到电影音乐能在何种程度上构成我们对叙事的感知的那一瞬间,我们不再认为它只是电影的一个附加成分”。
电影音乐作为影片的一种叙事语言,对提高影片的美学价值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观众在观赏影片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受到电影音乐的感染。同时。电影音乐作为影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提升了影片观赏价值。也丰富了影片的内涵。电影中,对声音的再现将不成为问题。在陈凯歌所改编的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文学作品叙事中的淡化与回避的歌唱与演奏都进行了有效的再现。
一、电影音乐成为影片叙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影视音乐作为电影的开场自并不只是影视画面的配角,它本身及其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传递了观众的价值取向和时代观念。音乐构筑了一个有序的世界和即时的幻想空间。
音乐在电影之前就已存在。对音乐的解释在我国古代已有记载。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记·乐本》)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荀子·乐论》)
音乐介入电影的历史源于电影的公映。最初的歌舞片《爵士王国》是电影与音乐、舞蹈嫁接的产物。在当代电影中,音乐已成为叙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对画面叙事的一种补充与修饰。如:特定的乐器奏出特定旋律。可以对影片中的故事发生背景进行补充性说明;利用具有时代、地域特征的音乐,能迅速而简便地营造故事特定的背景氛围。利用音乐对动作、场面、情绪进行修饰更是多见。好莱坞影片无疑更精于此道。以约翰·威廉姆斯、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为代表的好莱坞式音乐格局,在1975~1985年的影视音乐中重新使用了交响乐,它吸收了20世纪50年代的大众音乐和枯燥的现代音乐中的创新部分,使音乐为影片平添了绚丽的色彩。
在洛杉矶波士顿音乐厅中,《拯救大兵瑞恩》摄制组完成了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后期制作。威廉姆斯和斯皮尔伯格都认为音乐是体现影片内涵、烘托影片气氛的重要一环。著名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和泰戈伍德音乐节合唱团由作曲家约翰-威廉姆斯指挥,为电影录制了主题曲。一组节奏悠长、缓慢的音乐在影片中伴随米勒上尉和士兵们在敌后搜寻瑞恩的旅程,而在打出演职员字幕影片结束的时候,一组抑扬顿挫的羊鼓乐作为片尾音乐,那悲壮的声音自始至终萦绕在观众的心头,离开影厅仍久久不能散去。
爱森斯坦著名的“听——视对位说”理论中提出画面影像必须与音乐主题相对称。让·雷诺阿也曾提出采用现存的音乐和古典音乐作为影片的主题音乐。主要有两个理由:首先,怕自己感情用事;其次,古典音乐家们在表达感情方面提供了某种克制的范例,这给了我莫大的帮助。
音乐在影片中的超然与冷静,构筑了隐喻与象征的世界。影片的高潮既是剧情的高潮,也是音乐创造感受的高潮。每一个电影导演都试图把观众的注意力导向一定的方向,并造成悬念。因此,在每一个特定的场合导演都将求助于他们认为最合适的配音方法。
二、电影音乐为影片完整叙述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叙事并非是仅仅借助视觉的手段构筑出来的。音乐也是将叙事信息传送给观众的程序中的组成部分。音乐的运用为影片的完整叙述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诗意电影强调的是诗一样的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最终达到作品思想内涵为目的:并运用形象的含蓄性为接受者提供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会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一段歌曲、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前半部,女兵们展现的是一种清新、健康、令后人崇敬的力量,战士们尽情地享受着从炮火中偷来的一丝快乐与轻松。但是在此之后,前半部的那种战时暂时的宁静气氛没有了,代替它的是残酷的局部战斗。是肉搏,是死亡。音乐节奏也开始由舒缓到紧张。而姑娘们的命运已经在前半部的结尾处改变了。仔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从丽莎被派回去送信之时就已开始,情节沿着一条曲线急剧上升,影片以越来越短的间隔来表现奔跑的丽莎和中尉及留下的四名女战士的活动,丽莎的镜头越来越长。五人的活动镜头越来越短……
在影片中一个妇女从虚影逐渐变成实影。音乐和从虚到实的镜头处理给我们一个错误符号,以为丽莎一定是这个虚影。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熟悉了这段由三角琴弹奏的俄罗斯民间曲调中丽莎的闪回镜头,但是当影片中的影像变为实景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房东太太。主题音乐引出的这个镜头的内涵凸显复杂。
在这部影片中,简洁的音乐运用得十分成功。史诗般悲壮的主题音乐出现在上下集的片头片尾。当出现主题音乐时,观众感觉即将看到的是一个悲壮的、史诗般的故事,但是由于尚未看到影片全部内容,因此观众只能冷静地、沉默地接受这段音乐。然而在前半部的结尾,我们的观众看见那个红衣姑娘在数数。从而与过去的那些姑娘的命运形成尖锐对比,此时的音乐——号角声对观众感情的冲击是不可抗拒的。动机不同的音乐以及音色不同的乐器展现了五位姑娘的特征:加丽娅运用的是前苏联音乐片的轻音乐;丽莎则运用的是代表俄罗斯农村的民族乐器三角琴;热妮娅运用的是象征现代的、时髦的管乐队演奏的三步舞曲;加之钢琴和大提琴的使用者索妮娅,它的音调明显是悲剧性的,当钢琴后面出现大提琴时,它的悲剧性更加增强。影片的抒情歌调与诗意电影的完美结合,彰显了前苏联的民族特色,也展现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试想一下。如影片中没有了温柔浪漫、如歌如泣、温柔细腻的象征了每一位姑娘的音乐以及出现在片头与片尾的,主要由小号吹奏出来史诗般的雄浑与悲壮的主题音乐,结果则迥然不同。
三、电影音乐成为影片直接叙述对象
电影再现时空这一特点也使电影与电视有一个其他艺术所不可企及的特点:在理论上,它可以完整地再现其他艺术。也就是说,它可以将其他艺术转变成为自己的叙述对象。当在其他艺术(比如文学)叙述遇到了它必须面对却无
力面对的对象时,它就只能将其淡化或者通过间接的方式叙述,甚至干脆回避。对于电影的改编来说,它完全可以将被文学叙事回避与淡化的东西进行很好的呈现。当电影传人中国,国人首先想到就是拍京剧《定军山》。这恐怕是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潭鑫培精彩绝伦的表演只有电影才能将其再现出来的结果吧。
在小说《深谷回声》中,柯蓝对音乐的描绘集中于翠巧送别那一段。这时从山顶上传来一阵歌声,一听就知道是姑娘在山上高唱着民歌“兰花花”为我送行。有人曾经说这一小说最好能配上秦腔的光盘。让人们在必要的时候聆听一下主人公是怎么样吼秦腔的。散文中翠巧唱了十里山路,可以想象,唱了许多。声音是电影叙事的构成要素,改编就会向声音倾斜。电影《黄土地》就能够利用媒介的特点再现翠巧的歌喉。它使翠巧一连唱了四首歌。此外,电影中也再现山谷中的风声,这就构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情景。当电影通过它的镜头、画面与音响将它再现出来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激动,也就会更让我们对这位女主公更加同情。就《黄土地》将音乐作为叙事对象而言,除翠巧外,电影给每个主人公安排了一首歌曲,并且也给另外一个(婚礼上的)民歌手安排了四首歌,这样大大加强了音乐的分量。音乐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电影中对音乐的使用也自然会使音乐的魅力进入电影中。使电影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这当然会引起电影艺术家们的重视。
“眼睛(一般来说)肤浅,耳朵深奥而有创意”。布烈松此话提示了电影的重要意义,声音能够将画面的意义升华,使画面的意义明确。陈凯歌自己对此也很有认识,他说:“有时没有声音,画面什么也不是。”
在影片《黄土地》中,有一段几个人在茆顶上耕地的场景。陈凯歌借助于声音媒介来开拓电影的叙述维度,将画面这种具体的物像构成一幅意义丰富而深长的艺术图景。电影叙述者在画面加上音乐后,声音与画面叠加在一起而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意效果。音乐的声音“悠长而又悲怆。”当画面出现时,相应的音乐就奏响了。音乐作为一种抽象的艺术,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品格,只要我们想一想最为思辨的德意志民族培养出大量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同时,造就出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等音乐家,我们就不难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音乐同时又是最容易打动人的艺术,它那特有的旋律直接涌入人的心灵,作为一种纯粹时间的艺术。它能将人的思想引导超出单纯的画面的作用。当用电影呈现时,影像和声音就对主人公所存在的世界进行较为完整的呈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会变得明确而具体。而叙述者所叙述的理性内容就越加清晰。茆顶上的耕作,配上音乐,完成了对画面的超越,它超越了时空,成为我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象征。
在小说《命若琴弦》中,主人公老瞎子是一个琴师,是一个极其精于音乐的人。就我们的观影感受而言。电影中对老瞎子的琴声的再现可以说很忠实于小说。本来,电影《边走边唱》的音乐是由蜚声中外的著名音乐大师谭盾作曲,这既保证了《边走边唱》中音乐的质量,也保证了电影中的音乐符合老瞎子的思想、情感与情绪。电影中老瞎子弹琴时用了一系列特写。这使我们既看到了老瞎子拉琴的动作,也看到了他拉琴力度的变化,这些统统都是他内心的外化。我们看到了他不断变化的表情。听到他那不断变化的旋律与不断起伏的声音。这些使我们直接感受到了老瞎子心灵中的动荡。观影时,我们立刻为音乐所打动,随着音乐,我们径直走进了老瞎子的心灵深处。《边走边唱》中,当兰秀和小瞎子在神像前许愿,竟然响起了悲悯哀怜的受难曲。这是教堂的合唱的歌曲,借用到这里来表现叙述者态度,对兰秀和小瞎子爱情持着一种悯天悯人的情怀。同时这也是一种叙述策略上的暗示,暗示了兰秀与小瞎子这场恋爱的不幸结局。
电影使我们全方位地感受着音乐,感受着它那独特的旋律、音质和音高;感受着演奏者的动作、姿势和力度,感受着演奏者的表情变化,和他一起呼吸,分享他心中的喜怒哀乐。
在小说中,老瞎子弹断最后那两根琴弦时,作者一笔带过。到了电影中,陈凯歌从多方面对他进行呈现。老瞎子爬到影片中的最高峰,或坐或立,弹琴不停,老瞎子自己的琴声充满了生命的快意、酣畅和激动,惊得山下路人侧目而视,驻足而听。此外,还有天音渺渺,好似老瞎子儿时所唱的那首“千弦断”的童谣。正如布烈松所说:“人们轻易忘记一个人与他影像之间的差异,又忘记他说话的声音在银幕上与真实生活中并无差异。”电影媒介再现叙事语言的逼真性与直接性是其他媒介所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