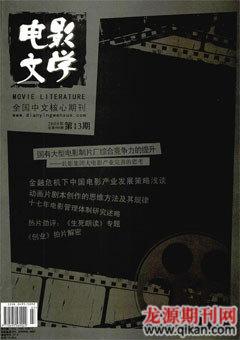只关生存的挣扎
李彦洁 章 妮
[摘要]台湾作家王祯和的小说《嫁妆一牛车》被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本文通过对故事主人公万发内心活动变化的分析,揭示了这部小说能够以看似老套的故事布局引起学界极大重视的原因。作家王祯和善于描绘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描写他们在面对残酷命运时进退两难的内心挣扎,通过强烈的戏剧冲突展示小人物坚韧的生命力。
[关键词]《嫁妆一牛车》;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小人物
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荣获“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内容不外是三个成年人(两男一女)的纠葛——似乎很俗套的故事布局。作者以重聋的主人公万发为主要出发点,展示了始终处于角斗场域中的万发卑微挣扎的命运。他先是和命运角斗,他是一个败士;然后和阿好角斗,仍然是一个失败者;闯入者——姓简的成衣商加入进来以后,无声又强有力地战败了万发,俘获了阿好。虽然万发在一系列角斗中都是失败者,不得不接受种种“安排”,他其实是抗争了的,或者说面对艰难的生存本身,他还是作过一番挣扎,希冀摆脱“命定”的角色。父亲留下的三四分薄地。他努力种植过;耳聋以后,他努力寻找过工作;流落到当前村庄后。他拉牛车、看墓地、抬棺材等,希望拥有自己的牛车,挣实实在在的钱。他是一个努力挣扎于半无声世界里的小人物,卑微到极致,却不曾放弃希望,拥有强韧的生命力。面对妻子阿好与成衣商的苟且之事,万发卑微的挣扎更是未曾放弃过,即使接受了姓简的牛车。
消息攻进耳城来的当初,他惑慌得了不得,也难怪,以前就没有机缘碰上这样——这样一的事!之后,心中有一种奇异的惊喜泛滥着,总谩嗟阿好丑得不便再丑的丑,垮陋了他一生的命:居然现在还有人与暗暗偷偷地交好——而且是比她年少的,到底阿好还是丑得不简单咧!复之后,微妙地恨憎着姓简的来了,且也同时醒记上那股他得天独厚的腋狐味,姓简的太挫伤了他业已无力了的雄心啊!再之后,脸上腾闪杀气来。拿贼见赃,捉奸成双,简的你等着吧!复再之后,错听了吧!也或许根本没有这样的一宗情事!也许真是错听了,阿好和姓简的一些忌嫌都不避,谈笑自若,在他跟前。也或许他们作假着确不知道有流言如是。骤然间两地隔断,停有关系,更会引人心疑到必定首尾莫有干净的。
乍听得消息的万发心内三起三落,念头真可谓九曲十八弯。流浪到此地如此之久,首次有此等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不能不让他惊慌——是不知所措的惊慌,也是害怕失去的惊慌。虽然他在事实上的地位弱于阿好,但他潜意识深处还是有强烈的男子中心主义,始终未曾忘记“妻子”阿好甚至是“所有物”的身份——多数中国男人的典型心理。所以他一开始高兴,高兴于自己的“所有物”并非自己想象的那样糟糕,高兴于自己还有一丝脸面。但一想到阿好毕竟是“自己的”,非他人可以随便取之,陡然有一种被侵犯的感觉,故而“微妙地恨憎”起简。万发与简之间的壁障,首先源于耳聋带来的心理弱势"--和对简的“几分憎恶”。后来在阿好的协助下,他一度以为双方势力均衡。但很快又被简“那股得天独厚的腋狐味”击败,万发在“男势”方面的弱势得以凸显——而这正是他在阿好面前失去势力的主要原因,自尊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因此他内心升腾起一股杀气,似乎惟有除掉姓简的方解此气。但流言只是流言,万发“拿贼见赃,捉奸成双”的念头体现了他隐忍的一面,这也是弱势者常见的思维方式。决心已定,万发的盛怒渐渐平息,不禁怀疑自己的听力。也不由得从阿好他们一面想想。想来想去,万发终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长期忍受的结果),对简并无什么火暴的抗议,乃至革命发起。“所有者”与“主人”心态促使万发把一腔愤怒之情全部指向简姓商人。弱者心态又阻止了他的强烈抗议,仅单方面终止了“朋友”关系,并试图通过缄默表明自己的态度。他的善良与生活条件得以改善的满足(尤为后者)又使其仅限于自我约束与监督,“再未曾让阿好和简的单独一处”。但所有者心态与弱者心理交织在一起,使得他只是把对简的“抗议”缓解为对阿好的“守卫”(与武大郎行为何其相似!都是弱者丈夫在行使自己的所有权)。由对外愤怒转为对内监视。
两次生存困境使万发逐渐认识到简对他家的重要性,从而渐渐承认简的强势位置。第一次困境使万发在村人面前成为“拘人的鬼判一般”,过了好一段“十分之一饱”的日子。两人自食其力的想法根本无法实现,“在外头摧眉折腰怨气受太多”,直到简的两个月又十天以后归来,他们的生活状况方再次得以改善。阿好自然“激喜”于简的归来,无法掩饰内心的那一层雀跃的兴奋。万发呢?
一个月多二百元进入。也或许不至于让肚皮饿叫得这么慌人。简直无时无准,有了故障的闹钟。不能的——不能让她知悉也在欣跳简的家来。万万不能够给简的有上与了人家好处的以为!万发自己也奇怪着,怎么忽然之间会计斤较两得这般。人穷志不穷吧!
在生存事实的考量下。万发内心不是一般的高兴,是“欣跳”,是激动得呼呼直跳啊!可他的心跳也是五味杂陈的,既高兴万分,又要防着阿好,以免她看出他内心的高兴而轻视他,更怕她把他的高兴传给简的,以至于完全丢掉自己的“尊严”。他的“人穷志不穷”是刻意表露的、虚假的、伪作的,他自己也充分认识到这点,所以他才意想不到那“疏冷多么的回口”竟是如此成功!
在简凭借“丰厚”的报酬搬进万发家以后,万发刻意的情绪控制、作为丈夫的监督职责有增无减。但他一贯的弱势,使阿好与简经常忽视他的感受,仍然常常兴奋地攀谈着。自觉被隔绝的万发为了行使自己的权利,在一番激愤之后,却又主动放弃战姿:
他干咳了几咳很严重性的警告,他们依旧笑春风地轻谈着,聩耳了一模样,简直目无本夫。斯能忍,孰不能忍?万发豁琅丢下碗筷,气盛气勃地走出来——撼金伐鼓,要厮斗一场。二十四小时不到,两汉子就不战而和啦!几乎都如此地,每当万发气愤走出来,有人觑不到的地方,便解下紧缠在腰际上的长布袋,翻出纸票正倒着数,才——啊!离顶台牛车还距远一大截,多少容纵姓简的一点!这样的财神,何处找去!以后的几天万发就稍为眼糊一些。
面对两人的谈笑风生,万发身为丈夫的所有者意识勃发。从情绪到动作,他都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战斗性与防卫意识。但他单方面的宣战还未引起决斗与厮杀,就偃旗息鼓啦。平息的原因只在于生存现实问题一顶一台牛车的钱还不够,他还不能够在谋生方面战胜强势的简。经过内心一番自我厮杀,他战胜了自己的激愤,也“战胜”了自己的尊严,部分放弃了自己的所有权!这里有个细节很值得注意,即万发数纸票是“正倒着数”。他每次都是正着数、倒着又数,数了一遍又一遍,确认了确认,正可看出他顶牛车心情的急迫——这是他急于摆脱尴尬、寻回尊严与男性力量的惟一途径!
卖酱菜邻居的一番恶语犹如导火索,点燃了他心中半明半暗的抵抗意识。此时的他清清楚楚感受到尊严被践踏,他不再把轻微的抵抗施于阿好,也不再在内心作一番生存与激情的辩论,而是利用语言的强势直接驱逐了简,“每句的句首
差不多都押了的雄浑浑的头韵,听起来颇能提神醒脑,像万金油涂进眼睛里一样。”火爆到极点的万发首次表露出强硬的势头,使简“有着给洗空一尽的感觉”,走时连瞅阿好一眼的胆量也给万发一声声“干”掉了。万发在简面前曾经被阉割了雄性,终于得以“回归”!他消遁已久的雄风终于吹起,连阿好也在这里噤声了。
无业的万发虽然驱逐了姓简的,赢得心理上的优势,但生存现实又一次亮给他残酷的一面:田地没有了,地瓜赔偿金极低,挣钱的老五又生病住院了。没有了经济来源,万发缠在腰际准备顶牛车的钱很快用完。他那强忍屈辱换来的美好梦想又一次成为水中月。内心的悲痛应该到了绝望边缘吧!入狱之后,万发不得不替妻、子的生存担优,激愤已经黯淡:
不详知为什么有一次突然反悔起自己攻讦驱撵姓简那桩事,以后他总要花一点时间指责自己在这事件上的太鲁粗了一点的表现。有时又想像着简的趁着机会又回来和阿好一寮同居。听狱友说起做妻的可以休掉丈夫的,如若丈夫犯了监。男女平等得很真正的。也许阿好和简的早联合一气将他离缘掉了!这该怎办?照狱友提供的,应该可以向他们索要些钱的。妻让手出去,应该是要点钱。当初娶她,也花不少聘礼。要点钱,不为过分的。可笑!养不起老婆,还怕丢了老婆,哼!
出于对妻儿的爱、现实的残酷,万发已然牺牲了自己好不容易挣回来的“尊严”,部分舍弃自己的抵抗。在反悔、自责中挣扎着。作者经由叙述者的直接陈述,渐至万发的内心独自,节奏骤然加快,比之前几次写到其挣扎时叙述者的不断插入,能更有力彰显万发的内心矛盾与汹涌澎湃。一句“男女平等得很真正的”打破了万发一贯拥有的所有者心态,竟有些惊慌失措。弥补此惊慌的又是钱——他一辈子做梦都想要的东西。他既要为索要钱的行为寻求辩护,又在心里瞧不起自己,挣扎于生存与情感之间。当最后接受简的牛车时,高兴之余又很是自我鄙视——他一辈子想要获得的独立生存能力与尊严竟是以这种方式获得的,他的尊严还是失去了。最终万发未能像沈从文《丈夫》中的丈夫毅然携妻回乡一样。决然拒绝简的“馈赠”,而是接受了两男共一女的尴尬格局。在这个格局中,万发向严酷的生存低下头,在村人的嘲笑与自我压抑中把痛苦死死地关在自己的世界里,在口腹欲求的“满足”中稀释难以磨灭的苦楚。每次喝简送的酒,他都有胸口紧迫得要呕的感觉。所要呕的正是他苦装的“漠泠”“心安理得”“闲适”,是他过着的舒松得相当的日子,是他从简那儿得到的生存能力。
面对在生存与情感、尊严纠葛间挣扎的万发,读者能做出多少道德层面的评判?生存本身是残酷的,舍去生存的情感可能更多的是海市蜃楼。倒是万发为了生存而压抑情感的痛苦,更能彰显小人物强韧的生命力及其苦乐哀愁,更值得为之掬泪。万发的困境就像作者在文本前的题词,“生命里总也有甚至修伯特都会无声以对的时候”,是“某种甚于死亡的悲哀”。
生存问题是万发最终妥协的根本原因,是在生活情境中艰难流浪的他做出的抉择。万发与阿好失去了土地,亦即丧失“农民”之实,更多的是“流浪”性。他们居住在四荒里“鬼们歇脚的处所”,是被人遗忘的一家;万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阿好与简常当着他的面吟吟哦哦,他又是被彻底遗忘的“那一个”。作者王祯和笔下的人物其实多数并非农民,而是市镇小人物,即惯常所谓“小市民”。他习惯将这些小人物置于残酷的命运、强势、自身弱点、集群意识等包围之中,赋予他们强烈的“流浪性”与被遗忘感。他们“流浪”在自己世界的边缘地带,在极端艰难的生存情境中展示其“柔弱”的挣扎。如《伊会念咒》将阿缎置于丧夫、流言、强横的章议员一家、雨祸、违章建筑限令拆屋等不测中,一波一波汹涌而至,令其不得有稍事回神的功夫。因为儿子这个希望,阿缎温柔而坚强地“忍受”着一切。正因其忍受,她不曾倒下,不曾被人口水淹没,不曾把房子卖给章议员。面对房子是违章建筑的诬告,她恳求过,奔波过,像祥林嫂一样哭诉过,甚至给章议员下跪,终于在气得结舌的情况下咒其不会有好报应。这种忍受而不是退缩,在忍受中有所作为,正是王祯和很多小说人物的生命力所在。在强烈的戏剧冲突中展示人物的生命力,揭示生存、强势等的残酷,是作者常采用的叙述策略(与作者强烈的戏剧意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