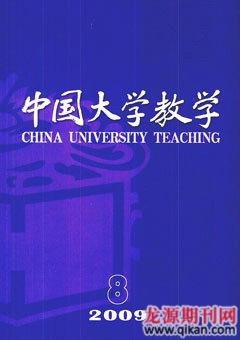诲人不倦 薪火相传
蒋绍愚 吴世美
蒋绍愚,男,籍贯浙江富阳,1940年出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第二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常务理事。
吴世英(下称吴):您是哪一年进入北大学习,哪一年毕业的?大学教育对您后来的工作有什么帮助?
蒋绍愚(下称蒋):我1957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62年毕业。在校学习期间,我们的课程大部分是北大中文系的名师教的。如古代汉语是王力先生教的,现代汉语是朱德熙先生教的,语言学理论课是高名凯先生教的,方言是袁家骅先生教的,古代文学是林庚先生教的,现代文学是王瑶先生教的。这些先生个性不同,讲课的风格不同,但他们深厚的学术功底,他们讲课博大精深的内容,都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在将近50年之后,我还能清楚地回想起他们讲课时的神情风采。尽管这五年中政治运动不断,我们不能集中精力学习,但还是打下了相当坚实的专业基础,这是使我终身受益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教授都是既从事教学,又从事研究,而且在自己的领域里很有影响的学者。所以他们不光教我们一些基础知识,而且引导我们去思考问题。这样的一种方式对我后来的整个教学和研究工作都有很大影响,这更是使我终身受益的。
吴:走上教学工作岗位以后,您是怎么样开展教学工作的?在当时的教学过程当中,学校有没有给您什么帮助?
蒋:1962年我毕业留校,立即就走上了讲台。我教的第一门课是写作课,是给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上的,班上有很多同学年龄比我还大。第二年,古代汉语组缺人,就把我调去了,从此我开始教古代汉语。我学习教古代汉语,主要有两个环节:一方面,我去听那些比我资历深的老师的课,看看他们怎么上的。这与做学生时候的听课,角度就不一样了。这是我学习提高的好机会。另一方面,我上课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年长的老师来听,对讲得好的地方给予肯定,对不足之处就提出改进意见。我觉得,教研室同事互相听课对提高年轻老师的教学水平是很有好处的。
吴:据说20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北大教务部有一个老教授教学督导组,让老教授去听一些课程。课后还了解学生的反映。然后综合起来向讲课教师提出意见,和讲课教师一起讨论如何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您知道这种做法吗?
蒋:我知道。好像原来数学系的李志忠老师就是这个督导组的。我有一次给理科学生上“大学语文”的时候,突然李老师进来了,他说:“我就是要趁你不知道的时候来听听,看效果怎么样。”
吴:您觉得这种做法效果如何?和您刚才讲的上世纪60年代初教研室成员的相互听课相比,您觉得有什么不同?
蒋:李老师是教数学的,他从宏观的方面、从教学法的角度对我的课提出一些意见,我认为对我是有启发的。但如果是同一个教研室的相互听课,那么在具体教学内容上对年轻老师的帮助可能会更多一点。
吴:现在课堂教学比较流行的是追求趣味性,要把课堂搞得很风趣。但是古代汉语、汉语史是比较严肃的学科,课堂上很难搞得很风趣。您是怎样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的?
蒋:我认为课堂教学一定要使学生感兴趣。如果一门课让学生听得索然无味,只是由于课堂纪律的约束才不得不坐在教室里,那只能说是教学的失败。但“兴趣”不等于“风趣”。“风趣”不是教学的根本。有的课程,教师在保证教学质量和讲授深度的前提下,经常有一些风趣的言谈,使得课堂气氛很活跃,这当然是好事。但是,课程的性质不同,教员的风格不同,并不是每一门课程都必须讲得很风趣。如果一味追求风趣而不在课程的质量、深度上下功夫,那就是舍本逐末,甚至会成为哗众取宠。“兴趣”就不同了,它是引导学生进入科学殿堂的必由之路。一门有质量、有深度,特别是有新意的课程,只要讲授得法,必然会使学生感到兴趣。“兴趣”并不是只能由文学的形象性带来的,任何一门深奥的、抽象的科学,只要教师善于引导学生思考,带领学生去发现问题、思索问题、解决问题,学生都能从中感到一种乐趣。这是一种探求的乐趣,发现的乐趣,是每一个曾经从事过创造性的研究的人都会感到的乐趣。和听了几句诙谐的谈吐以后的哈哈一笑相比,这种乐趣更为深层,更为久远。在这方面,我觉得朱德熙先生的讲课是我们的典范。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老校友的一次聚会上,有人总结出中文系老师讲课有三派:“考据派”、“意兴派”和“逻辑派”。“考据派”着重讲一字一句的推敲或者一首诗的来龙去脉,材料非常扎实,态度非常严谨。听了以后,不但知道了很多以前都不知道的东西,而且学到了严肃的治学方法。“意兴派”主要是一些以文学鉴赏见长的老师,把作品的意境、韵味分析得十分透辟,而且讲课时神采飞扬,带领学生全身心地进入到作品的艺术氛围之中。听一堂课就是受一次情感的熏陶和美的教育。毫无疑问,这两种讲课,学生都非常有兴趣。“逻辑派”主要就是指朱德熙先生。他讲的是现代汉语语法。在很多人看来,语法是枯燥无味的,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也有很多人钟情于文学,对语言学不感兴趣。但是,听朱德熙先生讲语法,却没有一个人说不感兴趣。这决不是夸张,你可以向听过朱先生的课的任何一个学生作调查,准保回答都是一样的。朱先生讲课从不离题,都是讲他的语法分析,也从来没有讲过什么诙谐幽默的话,而是讲这个词组、这个句子该怎样分析。那么他讲课吸引人的奥秘何在呢?就在于他对问题思考得十分深入,十分缜密,往往有一些深层次的探讨,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见解。而且,在课堂上,他从一些常见的语言现象入手,提出一些让人思考的问题,然后引导学生随着他的思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往深走,最终得出让人信服的答案。课堂上从没有哄堂大笑的那种气氛,但大家的思想都在跟着老师走,从问题到探索,到分析,到解决,最后获得的是一种“原来如此”的愉悦。一堂课五十分钟的时间,就这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吴:您是不是说,朱德熙先生的教学艺术十分高超?
蒋:朱先生在课堂上能把学生的思路引着跟自己走,这确实是很高明的教学艺术。有的老师一肚子学问,但在课堂上表达不出来,学生昕他讲课远不如看他的文章来得明白,这样的教学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朱先生讲课吸引人绝不仅仅是因为他口才好,首先是因为他有深入的研究。如果没有深入的研究,他怎么可能在人们习焉不察的语言现象中发现问题?怎么能对问题分析得那样深入?怎么能提出富有新意的答案?大学的教学,首先是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传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一个教员自己没有深入的研究,没有丰硕的科研成果,而仅仅是介绍一般的研究概况和转述别人的研究成果,这样的课不能说是高水平的,也不会吸引学生。所以,朱先生讲课的成功,不仅是由于有讲课的艺术,而
首先是有科研的艺术。一个好的大学教员,应当是科研水平高,教学效果好。朱德熙先生确实是我们的楷模。
吴:在您将近五十年的教学过程当中,您有哪些体会是最深的?
蒋:在评国家级“教学名师奖”的时候,上面要求写一份教学体会,其中要求写几句自己体会最深的话。我写了《论语》中“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两句话。我觉得,作为一个教师这两条是必须具备的。
第一要有“学而不厌”的精神。学术是不断发展的,作为一个教师,自己必须要有知识更新,任何时候都要努力站在这个学科的前沿。这就是“学而不厌”。只有这样,你讲出来的东西对学生才会有吸引力。如果没有“学而不厌”的精神,自己没有知识更新,教了几年书就觉得差不多了,可以吃老本了,于是五年前教的是这些东西,五年后教的还是这些东西,十年后教的也是这些东西,那学生肯定是厌烦透顶了。所以,“学而不厌”是搞好教学的重要前提。
同时要有“诲人不倦”的精神。一般来说,在北大这样的大学里,教师对科研都是比较重视的,但是作为教师来说,光是自己研究还不够,还要有“诲人不倦”的精神。有的教师对自己的科研抓得很紧,但对教学就不大愿意花力气,认为教学是一种“付出”,对自己没有好处,能应付过去就可以了。这就缺乏“诲人不倦”的精神。我觉得,“诲人不倦”不光是对学生负责的问题,还应该把它放到知识传承的高度来看。知识不是哪一代的人能够穷尽的,它总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持续不断的探求,才能够不断发展而愈来愈接近真理。既然如此,那么,作为一个献身于学术的人来说,自己努力在科研中取得成果固然重要,为学术发展培养下一代人也同样重要。特别是做老师的,要有这种使命感:我这一代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要让下一代来做。中国有句古话叫“薪火相传”,在一根木柴上点火,这根木柴总是要烧尽的:但是,如果火能再烧到下一根木柴上去,而且,一根一根地传下去,火就能永远不灭。要站在这样的高度上来看待自己的教育工作,就会觉得教学和科研同样重要,这样才会有“诲人不倦”的精神。从这个高度来看问题,我们就会把“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这两者结合起来。同时具备“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的精神,这是做好一个教师的基本条件。
吴:您指导的博士生论文,获得过全国的优秀博士论文奖。那么,您在指导博士生方面有什么心得体会?
蒋:博士阶段的学习,学位论文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不能说一个博士生进来以后,写出一篇博士论文,他的学习就算完成了。有的博士生把写博士论文作为自己学习的唯一目标,一入学老师就给他指定题目,指导他用全部时间来做这个题目,到毕业的时候,论文做得很漂亮,就交了差。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好的培养办法。因为,第一,三四年的时间只写一篇论文,这太窄了。第二,这完全是老师把着他的手在做。至于学生自己独创能力的培养,就挺欠缺的。我认为,整个博士生阶段有两点很重要:一是要打下比较宽厚的基础,二是要具备自己独立钻研的能力。因此,博士生第一年就是要鼓励他多方面地获取知识,基础要宽一点,像我们搞汉语史的,不光是要学汉语史,现代汉语也要学,一些国外的语言理论也要学。总之,要有很宽的基础。同时,平时也好,写论文也好,都要注重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博士论文的题目应该由博士生自己选,选题目的过程就是他独立研究的过程。他可以把题目选了以后来跟我讨论。如果我认为这个题不好做,我会建议他换一个,至于换什么,还是他自己去找。在他自己独立考虑以后,我可以给他提供参考意见。题目选定以后,还是需要他自己独立去研究,方向性的东西我可以给他指一指。比如,你做这个题目,有几个问题是必须要碰的,必须要解决的;或者在材料方面,你已经看到哪些材料,还有哪些关键的材料没有看到;哪些比较关键的观点你没有注意到,这些我会指给他。论文初稿出来后,我会仔细地看,给他提出详细的意见。但是整个过程都要他自己独立思考,不能由老师代替。
吴:在思考的过程中,建立自己做学问的方法。
蒋:对。即使有些知识观点跟我不一致,我也是充分尊重学生的创造能力的。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看法,只要你言之成理就可以,不一定跟老师意见一致。而且往往跟老师意见不一致的,倒可能是有新意。一句话,对博士生的培养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他独立研究的能力,培养他创新的能力。离开这一点,即使一篇博士文章写得很漂亮,得到了这个奖那个奖,但是他的创造能力如果不强的话,那他毕业以后也不会有多大发展。
吴:您主持过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的几个教育部的重大项目,您让博士生也参与这些课题吗?您认为参加这样的科研项目对培养博士生的科研能力有什么作用?
蒋:如果博士生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一致或比较接近,我会让他们参加。但不是把他们当成劳动力来使用。而是通过这个课题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让他们在做课题的过程当中,去独立思考,摸索做学问的方法。对于学生来说,这是多一个实践的机会。
吴:您觉得,老师的研究成果对教学有什么样的影响?怎样才能把科研成果转化到教学中去?
蒋: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个不做科研的老师绝对不会是个好的老师,因为他的知识永远停留在老水平上,他不可能有前沿性的东西。但是,这里还要强调一点:一个做科研的老师,在教学上。也要有创新意识。不能在科研上要求创新,而在教学上就图省事,每年都重复老一套。一个好的老师,应该有意识地把最新的科研成果(包括自己的和别人的)放到教学中去。我是努力朝这个方向做的。我从1986年开近代汉语研究这门课,到现在整整20年了。我还写了一本《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如果照本宣科的话,20年下来,我还用备什么课?直接上去讲就行了。但是一直到最近我讲这门课时,差不多每讲一次课,我还要花一天多时间备课。为什么呢?因为我要重新考虑教学内容,要把一些新的东西,包括别人的观点以及我自己最近的意见放进去。我每次都给学生发新讲义,每一届的讲义都会和上一届的讲义有较大的不同。所以,即使有学生原先已经听过了这门课,如果他再来昕一遍,他还是会有收获的。认真做科研和教学的人,就是要不断把自己的、同行的新研究成果带到课堂里面教给学生。
更重要的是,要把自己在科研中的具体思考过程教给学生。也就是说,学生在课堂上听到的不仅仅是研究的结论,而且是研究的方法。老师把自己的思考过程告诉学生,学生可以跟着老师的思路走,去掌握研究方法。当然,这不是要学生跟着老师亦步亦趋。老师在讲课时会说出自己对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见解,同时也引导学生对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这里所说的“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也包括老师的观点。我经常鼓励学生对我的观点提出补充、疑问甚至反驳,只要他说得有道理,我都会在课堂上加以肯定,并且说明放弃我自己的观点。这一方面是做研究的人应该唯真理是从,另
一方面也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有创新精神。独立思考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基本素质,当然,思考也要有正确的方向,正确的途径,这正是学生最需要学习的东西。我曾经在台湾大学讲了一次近代汉语课,那边有一个副教授,自己也做近代汉语研究,听了我一学期的课以后,这位副教授跟我说:“我听你这学期的课,最大的收获不是那些结论和观点,而是你的眼光,是你做学问的方法,这才是我最大的收获。”所以,我觉得搞科研的人,要教给学生的不是结论,而是得到结论的途径,得到结论的眼光。
吴:您先后去过国外的许多大学,像荷兰的莱顿大学、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等。在您去过的这些学校里,他们的教学方法是什么样的?和我们有什么不同?
蒋: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得很好。因为到国外去以后,我主要是讲自己的课,别的教师的课我几乎没去听过。所以说,别的教授是怎么教的,这个我还真说不上来。但是有一点,从跟学生的接触当中,我可以体会到一些国外跟国内的不同。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刚出去的时候,觉得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外国大学生在课堂上比较活跃,经常老师讲到一半就会提问,而且不满足一些结论性的东西,往往要问你多个“为什么”。而中国上课基本上就是一言堂,两个钟头的课,老师从头讲到尾,讲完了以后就下课了,学生很少提问。我觉得国外的这种课堂气氛非常好。也就是说,这种教育不光是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一种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学习中不满足于具体的结论,他总是要追问个“为什么”,知道了“为什么”以后,他就可以进一步去思考,可以解决类似的问题。回国以后,我也努力这么做,讲课的时候,不光是讲结论,而是讲一个思考的过程,着重于学生能力的培养。
另外,学生的个性也应该充分考虑。国外大学生的个性差别比较明显。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我1989年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古代汉语。当时学生不多,就五、六个人,有美国人、美籍华裔,还有日本人。一次,讲到《史记·项羽本纪》的时候,我用了一些别的材料来说明后代对项羽这个人有不同的评价。唐朝的杜牧写过一首诗,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宋朝的李清照也有一首诗。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我说,这两种看法你们觉得哪种对?几个美国学生说,各有各的道理,项羽回到江东卷土重来也对;不回江东,自杀也对。可见,他们看到了事情的多元性。而那个日本学生说了:“照我们日本人的看法,绝对是按李清照的诗,失败以后,就自杀,绝对不会再忍辱负重,卷土重来。”这件事我印象很深,过了那么多年了,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这说明,学生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事情的理解角度就大不一样。中国学生大的文化背景虽然一样,但是他们有各自的家庭,具体的社会生活环境并不相同,这在教学中也是应该充分考虑的。如果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就能够使教育收到更好的效果。启发性的教学,要培养学生能力,应该注意到学生不同的个性。虽然课堂里面只能根据多数学生的水平来讲,但是如果课下有辅导,有学生提问的话。就要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和多种需求,做一些有针对性的启发。
吴:北大的汉语语言学研究经过好几代老师的努力才达到现在这个程度。想要保持目前国内领先的地位,还要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您觉得在教学和学科建设方面,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蒋: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了。因为这也是一个关于世代传承的问题。
吴:对,就是刚才您说的“薪火相传”。
蒋:像王力等老一辈学者,现在我们是不敢望其项背的。不过,对下一代从总体上我是有信心的,因为他们受教育的环境比我们好。在80年代以前,我们基本上处于一种封闭的状况。现在这一代,从念大学、念硕士,到念博士,都是处在开放的环境中,他们跟国际学术界各方面的信息接触得更多一点,因此,从这一点上讲,他们肯定会比我们强。
吴:您对北大的年轻教师,在教学方面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建议?
蒋:对年轻教师的建议,还是刚才讲的两条。第一条,作为一个好的大学老师,你必须搞科研,你自己不站在学术前沿,这个课是上不好的,这个课是没水平的。第二条,就是你必须真正把教学当成一回事。我也很体谅现在的年轻人,负担很重,压力很大,要评职称,发表文章,承担课题,这些都跟他的个人利益息息相关。如果时间安排不过来,有些人往往就把教学排到最后一位,这样教学肯定做不好。我认为,教学是不可以敷衍的,不可以放松的。科研固然要做好,教学也要抓住不放,要做出出色的成绩。
吴:怎么样才能使某些青年教师不用敷衍的态度去对待教学呢?有没有什么机制来保证?
蒋: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自觉性,就是对学生有没有责任心。进一步讲,就是你对整个学术发展,对“薪火相传”有没有高度的认识。如果有这个认识,你教学就不会掉以轻心,就不会采取敷衍态度。如果你没有这个认识,成天想到的是提职称,写文章,发表什么东西,那么即使学校有再多的规定,恐怕也是见效不大。
责任编辑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