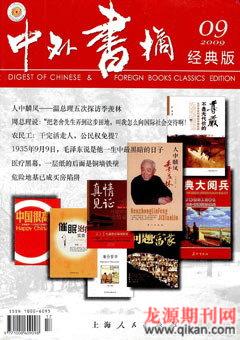中国空军奇袭武汉之谜
萨 苏
我在日本文献中看到对于1939年10月3日中国空军空袭武汉的战斗描述。根据其主要内容可以判断,此战至少击毁击伤日机160架,击毙日军鹿屋航空队副司令官小川弘大佐、木更津航空队副司令官石川淡大佐等多名高级军官。
特别是日方提到,当时在场的日军海军“第二航空队”司令官塚原四三将军在此战中负伤致残。由于他致残后无法继续担任海上任务,原来极有可能由他担任的日军海上机动部队司令官职务,改由他的同学,没有航空指挥经验的南云忠一担任。南云指挥的中途岛战役,是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转折点。如果是塬原而不是南云担任指挥。日军很可能避免失败的命运,中国空军的轰炸造成意料不到的效果云云。
日本的记载翻译(由西西河网友你克我服翻译)如下:
奇袭汉口基地
苏联送给中国的SB-2轰炸机神威大展,于1939年10月大举进袭了日本军占领下的汉口基地。中方趁机而入的背景是此时正值诺门坎事件爆发后日本的注意力集中在北方。当时日本海军的航母舰载机部队正以“第二联合航空队”的名义驻扎在汉口的空军基地。而且因为汉口机场拥有长达1500米级的跑道,停机坪也很宽敞,所以不仅仅海军,陆军的航空队也使用此机场。1939年9月末,汉口机场除了有140至160架日本海军战机外,还有日本陆军20架侦察机和联络机云集于此。可是,他们对中国空军的奇袭攻击完全没有任何察觉。
10月3日凌晨,以12架苏制图SB-2高速轰炸机为主力的轰炸机部队袭来。由于日本方面没有一架战斗机在空中执勤,防空炮火也没有准备,因此中方的SB-2驾驶员得以冷静实施轰炸。第一波轰炸是在6000米高空进行的。由于没有遭到反击,他们又降低到1400米高度实施了第二波轰炸。中方的12架战机虽然没有达到满载的10吨载弹,但全部炸弹都倾泻到了汉口机场。日本方面的飞机由于密集驻扎于此。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燃起了熊熊大火。据统计,日方飞机的损失中,全损至少为60架,另有接近100架左右受伤。汉口机场的大部分飞机都被认定无法起飞。人员伤亡更甚,死伤者多达240名,其中司令官塚原四三(海军少将)负了左手被切断的重伤。九死一生的环原在治疗中的11月15日晋升为海军中将。但由于失去左手,被认定不再适合舰队勤务,只好转任基地航空队的指挥官了事。塚原于1921年加入横须贺航空队,进入航空界打拼以后,历任“临时航空技术讲习部员”、“凤翔号副舰长”、“航空总部教育部员”、“航空厂总务部长”、“赤城号舰长”、“航空总部总务部长”、“第二航空战队司令”、“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等职,始终没离开航空教育与部队勤务。由于塚原丢了一只手(没法再继续在海上指挥舰队),因此无法胜任海军机动部队司令长官一职了。再也找不到塚原这样精通航空的人才,结果只好让虽然与塚原同届毕业(海军56期)、但却始终与航空无缘的南云忠一担任海军机动部队司令长官,可见中国此次轰炸在历史拐弯处产生了何等大的影响!看看丢了一只手的塚原,仍旧能继续在军中服役(虽然是被转到预备役去了),就可以了解环原对于航空界实乃不可或缺的人才。如果不是这次轰炸负重伤,未来担任机动部队指挥角色的,将有很大可能性是塚原。在太平洋战争开战之时,塚原担任了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初战就奇袭轰炸菲律宾,在马来海战中击沉英舰两艘,始终奋战在腊包尔航空队最前沿,这也算是对他多少有些补偿吧。
回头再看汉口机场的时候,1939年10月3日那天据说补给飞机将从木更津航空队飞过来,塚原司令及下属军官都集中在战斗指挥所前。正在此时炸弹落下,实在是不走运得很,以为是自己的飞机而毫无戒备之际……
这次的轰炸除了塚原以外,还直接造成了木更津航空队副队长石川淡、鹿屋航空队副队长小川弘的死亡。汉口机场原本是赛马场,经平整修建成机场。关于这次奇袭,坂井三郎在《天空的武士》一书中以《最倒霉的一天发生的事》为题有详细描述;而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2》里面只提到中国空军的SB-2等扔下五十余枚炸弹,大多数落入附近水田云云,并未涉及日军飞机所受损失。
——节选自《帝国制空战》,光人社2006年发行。
但在中方的记录中,我找不到1939年10月3日轰炸武汉机场的记录。记录中有苏联志愿航空队大队长库里申科曾经与中国空军一起空袭武汉,而且其殉难经过与日本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对自己亲历此战的记录十分吻合。然而,库里申科的死,很多文献记载是1939年10月14日。如果是那样,与这次空袭就对不上了。
补充两点:
1译文中“在太平洋战争开战之时,塚原担任了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初战就奇袭轰炸菲律宾,在马来海战中击沉英舰两艘”。
这击沉的两艘军舰可不是普通的玩意儿,一艘是31500吨的声望级战列巡洋舰反击号,另一艘是35000吨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激战过俾斯麦号的威尔士亲王号,《大西洋宪章》就是在它上面签署的!两艘军舰被击沉的消息传到伦敦,丘吉尔接报后哀叹:这是他“一生中最沉重和最痛苦的打击”。
2坂井三郎是日本海军在战后幸存下来的最著名王牌飞行员,曾著有《王牌空中武士的回忆》,曾在中国的期刊《航空知识》上连载。这里的文字就来自该书:
我清楚地记得1939年10月3日。这天,我读完信后就检查自己那架战斗机的机关炮。机场上,人们工作从容,情绪松懈。
机场的平静突然被控制塔传来的叫声打破了。接着,没有任何其它警报,四面八方就响起了轰隆隆的爆炸声,大地颠簸摇荡,响声震耳欲聋。“空袭”,不知谁喊了一声,但没有必要。这时,所有警报器都尖叫起来,当然也是为时过晚,毫无用处。
轰炸开始前没法到隐蔽所了。炸弹愈来愈强烈的爆炸声,犹如不断的雷鸣。地面,烟尘滚滚;空中,弹片横飞。有几个驾驶员与我一起,发疯似地从机修车间往隐蔽所跑。我把身子弯得低低的,以躲避嘶叫着飞来的钢片。我一头向两个水箱中间砸下去,要不是动作快,恐怕连人影子都找不着了。因为附近的弹药撒了一机场,震得耳朵发痛,地面飞沙走石。所以,若我有片刻迟疑,恐怕早就见阎王去了。附近的爆炸声突然停止,我抬起头来,看看发生了啥事。机场里,炸弹还在乒乓作响。透过爆炸声,传来人们痛苦的叫喊与呻吟,躺在我周围的人都负了重伤。我立刻向离我最近的那个驾驶员爬去。此刻我才感到大腿和屁股痛得像刀割,顺手一摸,血已把裤子浸湿了。伤口很痛,幸好不深。
我慌了,站起身来就跑,不过这次是向机场里跑。奔到跑道时,抬头向天上一望,头顶上有12架轰炸机在编队。它们飞得很高,
至少在20000英尺的高度上大转弯盘旋。它们是俄国的CB双引擎飞机,是中国空军的主要轰炸机。不可否认,敌机的突然袭击达到了惊人的效果,打得我们措手不及,狼狈不堪。可以说,在敌机尖叫着俯冲投弹时,我们实际上没有一人事先知道。
看到机场上情况,我吃了一惊。
一架挨一架的、停在那长长跑道上的两百架海军的轰炸机和陆军的战斗机,大部分在燃烧。一片片火焰从炸开的油箱中飘出,翻起滚滚浓烟。有些飞机的机身被弹片击穿后正在漏油,暂时还没烧着。火从一架飞机烧到另一架飞机,汽油淌到哪里就燃烧到哪里。整个长长的一排飞机全都变成了一团团暗红色的蘑菇云。轰炸机噼里啪啦像鞭炮爆炸;战斗机烧得呼呼啦啦,像一盒盒点着了的火柴。
我疯也似地围着燃烧的飞机跑,极想找一架没损坏的飞机。也巧,真还有几架隔开停着的“克劳德”没挨炸呢。我赶紧爬进座舱,发动引擎。甚至没等全部发热,就开着它向跑道冲去。
轰炸机正在渐渐升高。我径直追上去,把油门推到底,从这架不甘示弱的“三菱”飞机获取每一点速度。起飞20分钟后才赶上敌机。
我没注意自己飞的是空中唯一的一架战斗机。很明显,这架轻武装“克劳德”对那12架轰炸机根本不是个大威胁。飞机下面长江边上的宜昌市,它仍在中国防卫部队的控制之下。倘若我在这里被击落,即使当场不死,落到敌人手中也不会生还的。
我从后下方接近,敌人全然不知。当炮弹通通通地发射出去时。敌机炮手打不着“克劳德”了。我尽可能靠近最后那架飞机,集中火力打左引擎。开火后我迅速爬到它的上方,看见那台被击中的引擎冒出了长长的一条黑烟。它已掉离编队,开始下降高度,我掉过机头,想结果这“残废”,可是没能那么做。因为就在我向前推驾驶杆进入小角度俯冲时,我记起宜昌在汉口以西至少150英里,若继续追击轰炸机,就没有足够油料飞回基地,那就得迫降敌区。
有利的冒险与拿自己的生命和飞机开玩笑完全是两码事。继续攻击就是自杀,这种极端行为没有必要。我转弯回飞,那架俄国轰炸机是否成功地到达了自己的机场,不得而知。当然,最坏莫过坠毁在友军控制区内。
回到汉口机场一看,12架敌机所带来的重大破坏真难以相信。几乎我们所有的飞机不是被炸毁,就是被炸坏。基地司令的左臂被炸掉,他手下的几名上校以及一些驾驶员和维修人员,死的死,伤的伤。
猛烈的追击和战斗的激情。使我忘却了自己的伤痛,但从飞机上下来只走了几步,便晕倒在跑道上。
从我的推测来看,这架被坂井击伤的SB-2轰炸机,很可能就是库里申科大队长的座机。请看关于库里申科殉职一战的描述:
轰炸机大队大队长库里申科,率领机群奔袭日军汉口机场。在武汉上空与敌机相遇。在击落5架敌机后,库里申科的飞机左发动机被击中,他用单发坚持飞行。返航至四川万县上空时,飞机失去平衡。他尽力控制飞机超低空摇摆着避开居民区,迫降于长江水面。机组的领航员、报务员和轰炸员都爬出机舱。当地民众亲眼目睹了这一惊险过程,纷纷跳入江中营救。惟有库里申科大队长因筋疲力尽,未能爬出机舱。20天后,人们才在下游猫儿沱发现他的遗体。
在我国的资料中,后来也找到了相关材料,认为是10月3日、4日进行了两次空袭,使用的是DB3重型轰炸机,库里申科大队长在第二次空袭中阵亡。
但由于日期存在差异,而日本方面没有第二次空袭的记录,这种推测只能是一个谜了,是我军把一次空袭当作了两次,还是日军把两次空袭合成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