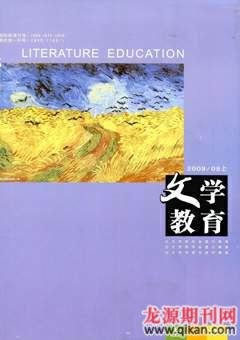宗璞《我是谁?》的人性深度
自创作了《红豆》之后,宗璞把手中的笔搁置在了一旁。文革时代的特殊环境让不少作家选择了沉默。一腔的爱国热情往往会被曲解,被赋予另外一层完全相反的意思。蒙受着不白之冤不说,还得忍受身体上的种种意想不到的摧残,不少知识分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该何去何从呢?
历史会证明对错,时间会带走不幸,可是它们常常是不同步的。文革一过,它就被定性了,然而它留下的伤痕却难以瞬间消除。整整一代人带着难以抚平的伤痕走进下一个时期。在政治社会的变革中,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的群体,仿佛注定要在夹缝中生存。他们的身份模糊不清、模棱两可,遭受着人们的恶意怀疑。
知识分子是宗璞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人物形象,宗璞在《我是谁?》中把主人公——韦弥放置于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新中国诞生了,韦弥——一个精于并专心于生物学的知识分子,怀着重建家园的信心,不远千里地赶了回来。简陋拥挤的居所、粗糙简单的饮食、繁重紧张的工作都没有让她感到遗憾后悔。她抓住每分每秒,生怕一时的消遣就使祖国的进步滞后。她希望在这个新的政治环境中,能一心一意地搞自己的研究。可是时代的政治风云变幻不定,而且突如其来,让人一时无所适从,不知所措。文革,一场波及甚广的政治运动,来临了,期间知识分子的身份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各种质疑。赤裸裸的斗争让人们撕下了温情的面纱,不顾一切的揭发批斗让人胆战心惊。人性这个永恒的主题又一次不得不被重新审视。在这场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人性成为了冷酷、无情、自私的代名词。人性何以变成了这样?人们困惑了。
往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被政治给颠覆了,人的本性究竟是什么呢?政治真的有那么强大的力量能改变人类的本性?韦弥在文革的无情斗争中受到了批判。一个人要被揪出来时,莫须有的罪名总是会被找到。在不经意间,韦弥变成了人们眼里的“牛鬼蛇神”和“毒虫”。之后,就有轰隆轰隆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韦弥寻找着可以藏身的缝隙,可是人们如针尖般的话语和眼光无处不在,连不懂世故人情的小女孩也像躲避魔鬼般躲避着她,而且在逃走的同时还不忘叫嚣一声“打倒韦弥!打倒孟文起!”怎么会这样呢?韦弥如堕五里雾中。在校园的小径上跌跌撞撞地行走着,昨日的希望、激情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没有理想,不容于人民的韦弥迷失了自己。
政治斗争改变着人们,人性一点点的丧失。韦弥不停地自问着“我是谁?”韦弥陷入了寻找自己独立人格的深渊。周围人们给予的种种“答案”是对的吗?韦弥不信任这群“疯狂”的人了,他们也同样迷失了自我,同样需要扪心自问一下“我是谁?”韦弥发疯似地奔跑向那个僻静的所在——一潭湖水。鸿雁在头顶哀鸣,她忆起自己和丈夫文起昔日沸腾的热情。但是现在呢?祖国母亲抛弃了他们,祖国的人民无情地对待他们,他们滚烫的热情冰冷了。他们埋怨这个祖国吗,怨恨这些人民吗?他们的心灵是那么纯洁,没有埋怨和怨恨,只是静静地哭泣,为祖国、为祖国的人民、亦为自己!在宏大的政治势力面前,一切都面目全非了。“众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让人害怕。
刚刚建立的信仰在顷刻之间瓦解了,刚刚高扬的信条在转眼之间崩溃了。历经不知多少苦难的中华民族,好不容易建立起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又陷入了混乱之中。这群知识分子,本想把自己的一技之长,毫无保留地贡献给日思夜想的祖国,可是在强大的政治斗争和无情的人性面前,不知何去何从,破灭了心中的希望。之前,他们舍弃一切富贵地位回到祖国的怀抱,不图祖国人民的任何回报,只想让祖国能早些强大起来。祖国,这两个字,在他们心中的份量是难以估量的。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回来了,两脚站在中国的土地上,他们长长地舒了口气,把数年压在心头的郁闷全部吐出。祖国的荣辱兴衰每时每刻都牵动着他们的心。对生养自己的故土的爱,与其他人相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心中的理想、祖国的恩情,本是可以融合的,但在文革岁月里这种融合却成了不可能。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连种族都难以保全,到处战火连绵,连一间安宁的居室都无法提供,何谈其它呢。这两者纠结在他们的心中,矛盾的心境困扰着他们,他们努力寻找可以两全的出路,然而,个人在时代历史的潮流中是无助且无力的,时代汹涌澎湃的浪潮湮没着单独渺小的个人。同样的,在强大的政治话语下,个人的舆论就是呓语,根本不能当真,因此也无需重视了。
不知是知识分子敏感,还是他们使人敏感,反正他们在时代政治的大潮中总是要触礁。韦弥和丈夫文起踌躇满志、兴高采烈地归来了,做好了为祖国倾尽全部心力的准备。祖国的温暖让他们心安,祖国经受的灾难让他们心碎,终于,苦难的日子就要过去了。她和丈夫文起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他们不期待祖国人民的热情欢迎,只想着在祖国的进步中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可是,毫无人情可讲的政治斗争却来了,他们无处可躲了。孟文起“在死亡里看见了希望”,生的自由成了奢望,趁还没有失去死的自由时,文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心痛啊!人活着,连死的自由也不能自主。文起离开了,留下了韦弥一个人。
在批斗中,韦弥,连同其他知识分子,变成了人们眼里的“毒虫”,只有在地上爬着。韦弥在“虫群”中爬行着,看着身边的虫子一个个消失,听着虫子发出的“咝咝”声,一个她久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又再次被提起——“我是谁?”6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悲惨的、低下的,如虫子一般卑微地生活在最底层。各种各样的声音掩盖了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声音,韦弥个人的声音更是如湖水的涟漪般无声了。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该拥有的自由都消失了。天空中失群的秋雁迷途了,声声哀鸣让人心惊。韦弥亦如失群的鸿雁般寻找同伴,寻找归宿。她拼命奔跑,天空中的飞雁合群了,可她还是孤身一人。“忽然中,黑色的天空上出现了一个明亮的‘人字”,这是雁群排列成的。凝聚了日月光辉的“人”字清晰地伫立在韦弥眼前,可是有不少的“骷髅、蛇蝎、虫豸”噬咬,践踏着这“人”字。雁群排出的“人”字飞向了远方。韦弥找到了“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人”的自由和尊严,却需要用生命来诠释,这样的结果只是太可悲了。迷途的大雁找到了自己的同伴,并组合出了“人”,真正的人呢?韦弥这个个体何时才能找到自己的同伴,能不能被自己的同伴接纳?韦弥推翻了那些加给自己的“称呼”——“牛鬼蛇神”、“大毒虫”,她声明了自己的“身份”。她是人,可是她不能得到“人”的自由和尊严,她生与死的自由都被人无情地剥夺了,在丧失了“人”该有的一切之后,她迷失了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在苦苦的追寻中,韦弥终于找到了满意的答案——“我是人”。“人”是多么让人自豪的词语。作为人的自觉、自由、自主重新回归了吗?韦弥还没真正享有作为“人”生的自由权利和尊严时,就用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韦弥活下来要得仅仅是这个答案。文起争取了自己死的自由,韦弥有死的自由而且也找到了自己。
“人”的意识在韦弥心中复活了。韦弥没有丝毫怨言,而是充满了“觉醒和信心”地喊出了自己的声音。湖水转瞬就拥抱了她的身躯,淹没了她的声音,她的声音仍然如“虫子的嗫嚅”般无力,没有人听到。韦弥也在死中得到了解脱,在死中找到“人”该有的。她的叫喊没有唤醒其他的人,周围依旧是“黑暗和沉寂”,单个人的声音太薄弱了。知识分子的叫嚣不会震动任何人的耳膜。韦弥死了,但她坚信“‘人会回到自己的土地”,而这回归的时候就在不远的“春天”。
宗璞的《我是谁?》也是抒写文革给人带来的不幸,但她选取的视角独特。在强大的政治运动中,“人”迷失了自我,不再称其为“人”。《我是谁?》就是对“人”的追寻。韦弥追问着自己的“身份”,苦苦寻找着自己丧失的“身份”。生在人群的漩涡中,她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人”的身份被政治话语、政治身份淹没了。作为知识分子的韦弥觉醒了,追寻着自己的“身份”,确立着自己作为“人”的身份,不惜用生命作为代价。
参考文献:
[1]郑新.命运沉浮中的觉醒.学苑漫录,2005,(11).
[2]赵晓芳.爱,是不能忘记的.当代文学,2007,(2).
[3]赵慧平.说宗璞小说的“本色”创作.当代作家评论,2007,(6).
郭瑞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