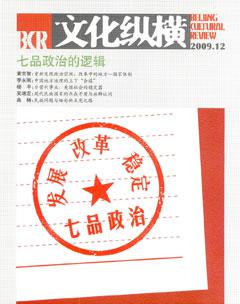国家政治与州政治
林国荣
詹姆斯·法卢斯在其2009年4月发表于《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中直陈中国政治的当下实情:“当人们抱怨的时候,人们所抱怨者通常是黑心的老板、记者、市政官员或者各级官僚,人们并没有抱怨体制本身或者领导人。针对体制及其压迫的日常抱怨确实存在……但这并不是常态……也许大部分中国人趋于短视,但就目前来说,人们行动中所透射出的期望是:国家的体制能够保护他们免受地方层面造成的冤屈。”
中国的司法和行政系统就当前的状态而言,日常的主要力量和机制几乎完全是在省级的、甚至是地方的政治领域内运作,地方政体往往展现出复杂的态势,行政和司法系统很难有机会或者意志超越寡头式的地方利益网络,相反,地方法官和官员从其所接受的教育和生活经验出发,比一般公众要深得多地浸染于地方性的激情和偏见当中,这一切都使得为公众伸冤的道路因为缺乏动力和同情式的理解,而难上加难。当前,中国的司法和行政系统在面对地方利益驱动之下的种种自利规划时,总是表现出无所作为,而在实际上,它们自身也正是地方寡头利益的操作者和捍卫者;在公众心目中,这只不过是进一步表明了国家领导权的暗弱。这样的公众感觉对当前的领导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威胁,它同时也正在摧毁领导人达成政治目标的日常能力,在这些目标中,有很多都是必要的和根本的。最终,这样的境况很可能会将人们置于在各种可能的选择中无力进行选择的灾难性处境当中。
利益政治的政治德性
自从1780年代费城会议首次进行大范围的宪法大辩论以来,美国也一直面临着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毁灭性影响,尽管联邦党人的主要政治观念在1780年代的辩论中取得上风,并且也能体现在甚至包括《独立宣言》在内的建国文件内,但自美国建国以来,地方政府,尤其是州政府,为了地方权力体制的利益仍能置联邦法律于不顾,这一趋势发展到1860年代达到顶峰。在1860年代初,南方各州在为奴隶制辩护时,甚至可以跳过种植园制度的经济和伦理意义这些实质性的问题,直接以“民意”形式诉诸州的立法主权,对联邦立法权的至上性构成面对面的宪法挑战,置国家于分裂的悬崖边缘;同时,北方,尤其是东北部的各州,也在金融寡头势力的钳制下,致使联邦立法机构无法形成独立的政治意志,有时候甚至连合格的立法成员都得不到。
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都已经内在于1780年代的宪法论战当中;在那场公开的政治对话中,联邦与州政府的关系问题已经作为宪法问题最核心的部分,得到详尽无遗的揭示和阐述。不幸的是,问题本身仍然存在,并在很严重的程度上存在于合众国的历史当中,甚至威胁到联邦自身的生存。但这并不能证明1780年代参与政治对话的新大陆政治精英的失败,因为联邦与州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覆盖了美国法律生活的所有方面,从而使问题本身的完善解决远远超出了仅仅一代人的理智能力。换句话说,这个问题已经作为一种恒久的张力内在于美国的政治生活当中了。
在1780年代的宪法论战中,联邦党人的反对者们针对联邦党人的强中央政府设想提出了一系列的反对看法以及反设想。问题首先涉及到:中央政府较之州政府更为远离地方人民,因此在与地方人民的利益和习俗产生亲和力方面,州政府要比联邦政府居于远为优越的位置上。对此,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给出了正面的回应:“各州人民对他们的地方政府往往比对联邦政府怀有更强烈的偏袒,除非这一原则的力量为后者的大为优越的管理所摧毁。”在此,汉密尔顿对地方性质的所谓“民意”的构成要素表现出深刻的不信任和警惕;对汉密尔顿来说,地方性质的“民意”并不一定就是州范围内的大多数人民的想法,事实往往相反,在新的选举制度下,地方的“民意”因为在一个很狭窄的地理范围运作,很难有机会摆脱地方寡头和等级体系的操控。换句话说,汉密尔顿并不否认联邦政府在某些必要的方面是专制的,实际上任何的权力形式都必然是专制的,相比之下,人们更应该担心的是地方寡头的肆无忌惮和邪恶放荡以及州政府的残暴行为,这样的行为如果不接受联邦的强制性约束,几乎是不可能从“民意”方面汲取任何教训的。
汉密尔顿在同一篇论辩中进一步指出,真正有效的政府是那种能给人们提供恰当利益的政府,而不是人们想象中虚构的地方性质的自然共同体。真正能够激发人民信任和依恋的政府是那种能够结合有效管理和恰当利益的政府,而不是以“父权之名”行寡头之实的政府。这要求联邦的权威和观点要在实质的程度上渗入、并在关键时刻主宰人民的日常生活;当时一位联邦党人的支持者击中了问题的要害:“先生,公民对政府和法律的依赖是建立在他们从政府所获利益的基础上的,其持久性不会超过权力所能赋予的那些利益的持久性。因此,当各州的人民发现他们的政府正变得麻木不仁,而且政府已经没有了提升人民福利和利益的手段时,先生们,人民才不会枉然地把影子当偶像,也不会在没有任何补偿可能的情况下,散发其艰苦挣得的财富。就给人民带来利益而言,各州的宪法既脆弱,又无用,而且还将会萎缩和腐烂。如果各州不会因为州长对抗衡联邦之无与伦比的绝对统治之成就没有耐心而灭亡,那么它们就会因为其自身的无足轻重而灭亡。”
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著名的第10篇中,着重论证了:在一个幅员辽阔、正在经历商业化、利益多元化的共和国内,联邦政治的基本要求就是建立在“利益”及其相互之间的折中和冲突的基础之上。联邦党人的这一“利益政治”诉求遭受了其反对者毫不妥协的攻击。反对者认为,将宪法建立在互相冲突的利益原则的基础之上,并以此来构建酝酿中的参议院,这无疑会成为宪法的重大缺陷;“利益政治”将从根本上瓦解传统的宗教和公民美德,而后者却是共和国政治稳定的根系所在。反对者希望宪法在主要的方面首先是公民性格的塑造者,而不是利益的控制和协调者;这就像1776年麻省议会所宣告的那样:“虔诚和美德是人民自由之保障,应当加以鼓励;邪恶和不道德应当加以压制;本最高议会认为,发布本宣告是恰当的,要求并恳请本殖民地的善良人民过一种明智、宗教而和平的生活,避免所有渎神行为、对神经和主日的蔑视、以及所有其他的犯罪和违法行为、所有的放荡、不敬神、腐败和堕落、所有的暴力和动荡行为以及诸如此类的不道德,要求并恳请本殖民地的人民严肃和虔诚地参与对神的崇拜。”
联邦党人的反对者从这一传统立场出发,不断地向参与宪法辩论的同辈和殖民地听众释放如下的警告信息:联邦党人的政治活动一旦获得成功,将使共和国付出丧失传统美德的代价。
对此,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就必须向反对者和人民证明传统秩序是不可能的,单单宗教和公民美德也不可能造就任何形式的政治稳定。在一个商业化的、拥有广阔前景的共和国中,宪法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应当基于利益理论。正如韦伯斯特指出的:“除非人性改变,否则,美德、爱国主义,从来都不是,将来也不会是固定的、永久的原则和对政府的支持。”联邦党人的利益政治暗示了利益平衡的政治德性,而不是同意的道德。无论是麦迪逊还是汉密尔顿都没有着重提到那个时期的新大陆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尽管这一趋势最终将证成利益政治的必要性。这是因为对麦迪逊来说,“利益政治”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新型的政治美德,这种美德的基础并非传统或者宗教戒律,而是政治清醒。一旦人们接受利益政治的教育,并生活在此种宪法之下,就没必要担心流行的信念、偏见和激情。麦迪逊对人性的善良及其训诫手段不抱幻想,他所接受的是马基雅维利曾经深刻解释过的那种永恒循环的人世间的利益冲突。不过与马基雅维利不同,麦迪逊指出,人也许是坏的,但共和国一旦摆脱自然共同体的束缚,就有可能是稳定而完善的,而且在一个多元而辽阔的国家里,人们有足够的机会和能力去满足自身的私人欲望。在第10篇论辩中,麦迪逊指出,导致共和国崩溃的根本原因不可能是美德的衰落,而是利益分配方面所产生的剧烈变化。因此,宪法的核心问题应当是“执行能力”的问题,应当是效能和能力上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隐藏在权力制衡框架的背后;在美国,人民现在掌握了平衡的力量,美国人剩下的是要面对这一事实,建立与这种新的利益格局相一致的政治制度。
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民主政治的断裂性和特殊性时,直觉到了双方所争论问题的性质所在,并就此评论说:“不要从一种已经逝去的社会状态中得出的观念来判断正在形成的社会状态;因为对社会的这些状态而言,它们的结构差异非常之大,它们不可能得到一种公正或公平的比较。要求我们当代人具有源自其祖先的社会环境中特有的美德,这也难说更有道理,因为这样的社会环境本身已经沦落,并且已经成为包含了它本身所具有的所有的善与恶的废墟。”
与此相对,在联邦党人的反对者们所提倡的公民美德背后,实际上隐藏的是一幅父权制下的州权图景,这是一种传统的欧洲模式,尤其是查理一世时期的英格兰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意识就是:政治统治者实际掌握全部统治权,个人掌握所有权。
州政治是政治腐败的主要温床
美国随后的州权历史都不幸被联邦党人言中。在“政治统治者实际掌握全部统治权,个人掌握所有权”的地方政治模式下,政治完全变成一个纯粹物质利益相互妥协和交易的市场;州权为之提供了强大的诱惑和广阔的空间,州的政治统治者通过操纵庇护制度和小费制度,进一步把持并稳固自己的权力,最终让一切必要的来自中央的行政监督和司法介入都变成幻想;在州议会里真正掌管权力的不是议会的政治领袖,而是商人、地产主以及地方上的银行家们。在此种局面之下,美国政治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丧失了“国家政治”的方向。
假如人们承认地狱不能由教徒来统治,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对联邦党人的反对者持同情立场的斯托林所作的总结也就称得上是一针见血了:“联邦党人的回答是,实际上小民主国和大民主国一样都不可能由教徒来统治。人的行为不是出于激情就是出于利益。审慎而恰当地设计出来的宪法,其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或者改变上述动机——改由信徒们来统治它们——而是要把它们引向公共利益。”(这一点也构成了新大陆共和主义者和传统的欧洲共和主义者之间的转折性差别;反联邦党人并不是单纯地为欧洲旧制度的某些残余作丧钟式的辩护,他们是在为在一个新世界中的生存地位而进行正面的斗争。)
联邦党人的反对者们极力拒绝将宪法的基础锚定在“我们人民”之上,为此,他们对《独立宣言》的用词表示了极端的不满,很多人甚至拒绝参与制宪会议的工作;他们转而探索一部以州权为基础的宪法,这主要并不是出于对传统的宗教虔诚以及公民美德的考虑;换句话说,反联邦党人之所以注重公民美德和传统宗教,是因为他们注重州权;他们之所以注重州权,是因为他们注重个人自由。与《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管理意识和相对并不强烈的个人自由意识相比,反联邦党人是自由的更为强烈的提倡者;如果说反联邦党人是洛克主义者,那么联邦党人便是边沁主义者。在反联邦党人纯朴的政治想象中,个人自由的自然家园是州,而不是联邦。
在反联邦党人看来,个人自由所要担心的最大威胁并不是联邦官员和参议院的“阴谋”,而是他们的才干。他们对《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精英意识充满警惕和反感,并且言辞尖刻,“联邦自耕农”和《加图来信》的作者都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和情感:“并不存在像一些人虽然没有却假装有的那样一些为政府所必需的伟大天才。诚实的情感以及共同的限制就足够了……伟大的才能,如果没有总是用来误导那些诚实但无防备之心的大众,它也是引导民众离开公共美德和公共善好之平坦道路的力量。” 在此,反联邦党人实际上指出了全国范围内的代议制的一个缺陷,即它不能从实质意义上代表人民的利益,联邦立法机构的代表构成及其运作方式与全国人民的利益构成之间总是存在差异和断层,除非联邦立法机构能够急剧扩大代表人数,而这样大幅度增加的代表人数将使联邦立法机构无法进行日常的有效运行和决策。这样的差异和断层将为联邦的政治精英提供发挥才干的空间,而这样的才干是宪法本身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加以约束的;这很可能为联邦政治精英成为“民主煽动家”提供空间和出路,最终将美国政治引向帝国和荣耀的方向,从而摧毁自由。“联邦自耕农”不无讽刺地说:“相对于大人物来说,这个国家的大量自耕农将更为温和,道德更加善良,野心更小。”
对此,联邦党人指出,地方性质的自然共同体是政治小人物的天然故乡,这些政治小人物无不是庸俗的低级政客,地方政治的同质性和缺乏流动,使得这些人最有可能成为败坏的政治煽动家;与之相对,联邦政治或者“国家政治”避免了上述根本性的缺陷,在“国家政治”的澄明之地,诞生民主政治领导人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腐败或者低级的政治煽动家。汉密尔顿则更为直率地提醒人们注意:民主政治煽动家也许是危险人物,但他们往往并非小人。联邦党人进一步强调:“……政治推理中,有关人性邪恶的普遍假设和有关人性正直的假设一样是个错误。代议制意味着人性中还有部分德行和荣耀的存在,而它们恰恰是信任的理性基础。”显然,反联邦党人所倡言的以传统宗教精神和公民美德为基础的政治形态,将最终使得美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缺乏任何浪漫主义式的跳跃或者上升,更不可能允许出现历史主角在对抗时局之必然性方面表现出英雄主义和苦难意识,而这一切却是日后的美国内战所要求于政治领袖的根本素质。
后来的美国历史证成了联邦党人的申述。州政治无论是在镀金时代、重建时代,还是在进步主义时代,都没有成为保护个人自由的主要地带,反而成为政治腐败的主要温床。联邦代议制确实无法从实质上代表“我们人民”的全部利益,但这是因为任何的代议制形式都做不到这一点。代议制的精髓不在于实质上代表人民,因为代议制并不是人民;相反,代议制的精髓在于引导人民,引导国家的种种重大利益,使之在“国家政治”的轨道上运行。宪法本身做不到这一点,但联邦宪法所培育出的政治领袖人物能做到这一点。
联邦党人的遗产时至今日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这笔遗产促使国会和总统逐渐地加强全国性的法律建制,以约束对联邦法律的侵犯并加速联邦法律的执行。他们加强了联邦法官和检察官的职能,联邦检察官由总统亲自任命并派往各州,同时,他们也用他们自己的法官和预算扩充了联邦法院。这一切都为“国家政治”的成功运行提供了成功的手段。从法律上讲,州检察官和州法院必须优先实施并运用联邦法律,但是如果地方政府忽略了这一要求,那么这些建制、举措就能够迫使他们臣服于联邦法律。若没有这些建制及其力量,反联邦党人极为看重的《权利法案》一开始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地方法律的软弱及其与地方利益的趋同,使得地方政治领导人没有能力、更没有动力去干预现状,他们绝对不情愿看到地方经济发展缓慢。正如最近的伊利诺斯州案例再次表明的那样,在这样的局面下,只有联邦机构能够不间断地追捕腐败的地方官员,而且只要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不采取行动,这些联邦机构就有权力截断地方产业的发展道路。这些“独立”的联邦机构非但根本没有侵蚀宪法的权力,恰恰相反,它们巩固了国家在观念层面上的权威、实际操作层面上的控制力和“国家政治”的主导地位。
在有关中央和地方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以及在权力制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追随马布里诉麦迪逊案、美国诉尼克松案以及五角大楼文件案所提供的所谓“美国模式”,因为在美国历史上,这一系列的案件只不过是为了伸张联邦最高法院针对总统或者国会越权行为的控制权罢了,这些极端的案例并不是美国宪法的主流和精髓所在。换句话说,并不存在“以自由和权力分立对抗国家权威”意义上的“美国模式”。况且,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联邦最高法院本身恰恰也正是联邦权威和美国“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在实践中也是联邦权威最强有力的捍卫者以及联邦权威之合法性的提供者。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