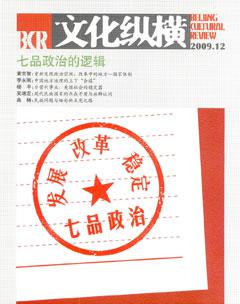气候变化的政治后果
保罗·赫尔曼 格雷戈里·特雷弗顿


对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的传统解读通常以资源战争、弱国倾覆、移民激增等为标志。但是从媒体的视角出发,气候变化并不仅仅包含这样简单的因果关系,或者说一种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对于那些已经被严重问题困扰的国家,像阿富汗、朝鲜和津巴布韦,尽管不易感知,但是气候因素可能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气候影响在长期干旱的国家像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尚且可以承受,因为适应恶劣气候的努力贯穿着这些国家的整个历史。
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气候变化是在监控之中的,并且夹杂着也加剧着现存的困境,比如经济薄弱、基础设施差、族群冲突、治理不力和政治合法性的质疑,这些困境往往通过外溢效应造成跨国影响。气候影响是多方面的,广泛分布的,并且积聚起来会产生系统性的后果。治理良好的国家可能比发展中国家更能适应气候的变迁,但是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不良影响。[1]
人们日益意识到了气候变化的直接表现形式,比如地表平均温度、降水形式以及对地球自然系统的次级影响等。但是无形的第三层次的社会政治和制度影响还并没有被充分地重视。[2]只有把这些损害安全的直接影响考虑进来,才能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恰当的应对做一个全面的评估。
物理变化与社会反应
气温升高和水体异常(比如干旱和洪水)影响着像牧场、农作物以及饮用水等自然资源的可用性。相对稀缺会使受影响的群体要么合作、要么竞争,但正是竞争使其社会影响备受关注。这种发生在城市居民和涌入城市的农村居民之间的竞争是极具分裂性的,在世界许多地方,比如南亚,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当城市没有足够的资源容纳新的居民迁入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会向更为繁荣的国家迁徙。这将造成移民拥挤在各种警戒线和围栏外的人间悲剧,引发对移民来源国未能守卫边界的指责以及移民目的国本土主义激烈而可怕的反应。
国内群体间竞争的另一条断层线牵涉到不同地区的政治实体,比如北非国家内部的撒哈拉-马格里布分界线。同时,竞争也发生在家族和种族之间。财政收入的减少、新福利需求的出现、传统政治的不平衡使原本脆弱的中央政府面临更多压力。官方对竞争地区的对策很容易被认为是不充分的,有的时候甚至会激起已有的被边缘化和被歧视的情绪。中央政府的无能和地方上的不满情绪可能激发贫瘠的内陆地区的叛乱,比如在近东的部分地区。相反,自治运动则有可能在被山地环绕国家的富裕地区开展,像正在安第斯山区国家发生着的那样。遭受气候影响打击的穷国则无力维持国内秩序。
人们安于──如果不是轻视──这种相对缓慢的气候变化,比如用厘米为单位来衡量未来几十年间海平面的上升。但是,微小的变化会带来巨大的差异。通过计算机建模显示,海平面上升18厘米将会侵吞佛罗里达大沼泽国家公园10%甚至更多的淡水湿地。[3]淡水资源遭到盐水入侵绝不仅仅是因为海平面覆盖海滩、灌满水井,它也是人们目光短浅的排水举措以及在近海地区高浓度、高水位咸水区的抽水行为带来的结果。海平面上升造成的海水入侵已经污染了以色列、泰国以及太平洋、印度洋和加勒比海岛国,甚至是世界上水量最大的河流的三角洲地区,像长江和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地下水资源。[4]而且,即使是海平面的微小上升也会使咸水和淡水在河口附近的交界线向内陆延伸。[5]可能这一过程中最具破坏性效果的是淡水植物的消失,这些植物的存在可以帮助清洁并给河流补充氧气,也能够缓冲风暴和洪水。
对即将来临的洪水的预知比海平面上升更能引起人类与之相应的行动。在一个全球化的、通讯便捷的时代,科学成果的报告,尽管常常被断章取义,也能够迅速激起个人和群体的反应。人们可能在没有退路前行动起来,并将大风暴看作更恶劣灾害的前兆。比如说,在世界上全国1/10的人口居住在海平面1米以内的38个国家中,有9个在加勒比地区,在海平面上升到一米线之前,美国政府的应急预案是必须的。[6]极端恶劣天气变化也是可与气候变化相比拟的对各国社会的严峻挑战。[7]2008年,美国和中国都经历了罕见的严重气象灾害。[8]时至5月,美国就要迎来一年中最致命的飓风活跃期,中西部的很多地区都将被水淹没。[9]中国则经历了严重的冻害,毁灭性的地震以及洪水的打击。当然有一些气象灾害不能归因于全球变暖,比如2005年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和2008年缅甸的纳尔吉斯风暴,这一判断是与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相吻合的。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持续的气象压力也许提醒了人们,一个气象灾害更频繁、更剧烈,且国家基础设施不断被毁坏的地球的未来将是怎样的。
极端气象灾害常常被认为是对平民的灾难而非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些灾害很少在实质上毁掉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也很少引发意在颠覆政权的动乱。[10]但是极端气象灾害确实使原本就是多方面的、分布广泛的、具有集合系统属性的气候影响扩大了。比如,2008年美国春夏两季的洪水并不是世界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但是它们代表并加剧了这个问题。到6月中旬,谷物和牲畜的价格已经达到或接近历史最高纪录,上涨的密西西比河部分航道也不再对食品运输船开放。食品通货膨胀不仅影响着美国的消费者,而且影响着进口美国谷物的很多国家。[11]需要动员军队控制的大规模火灾,像前几年发生在希腊和澳大利亚的火灾,会对国家安全造成更为直接的影响。
政治影响与制度建设
气候变化的影响,特别是水的可用性,会影响地区、国家和机构之间的关系。比如中国有一个从南方主要河流向北方干旱地区调水的宏大计划。这一计划以及中国在湄公河上的水坝,加之雪线增高和冰川融化都会减少流入湄公河的水量,流经越南的水量大幅减少了,给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倚赖捕鱼和务农的居民带来严重的经济困难。很难想象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和东盟的未来将会如何。而且下游国家间的冲突似乎在所难免。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未来东亚的制度架构和地区冲突解决机制中有所体现。
另外一个例子,尽管发生的概率较低,就是在远东地区中俄再起纷争。在中国,气候变化使得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的人口面临水资源短缺的现状,而俄罗斯最有可能摆脱这种稀缺的影响。[12]而且,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拥有一个日益庞大的、有需求的中产阶级,因此其对原材料和商品的需求是巨大的。这种情况有可能促使中国控制黑龙江及其附近地区,还有黑龙江以北曾经被中国控制的富饶土地。
中国的劳动力和商人轮流或者一同进入日益有序的、环境适宜的和商业化的俄罗斯远东地区。[13]人口统计显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人口在减少,这使得俄罗斯政府感到自身的领土控制力减弱,以及这种情况对富有进取心或不满足的中国人的巨大吸引力。与此同时,气候也是移民从南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涌入俄罗斯的原因,致使俄罗斯政治右倾化,具有排外倾向。政府的公开要求以及漫无目的的移民潮这两种进程都导致了边界地区的紧张对峙。这种紧张,反过来会削弱中俄在广泛领域的合作关系,包括中亚极具战略意义的上海合作组织共享领导权的问题。
气候变化也会影响现有国家以及机构的能力和活动范围。在未来的几十年,西欧国家为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不仅投在国内,还有东边新近加入欧盟的成员国、环地中海低地国家,以及通过金融机制在全球各地的投入。除了西欧,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像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也都是如此。这项新花费可能以减少传统的系统维护的项目花费为代价,比如扩大中的发展援助、生化武器和核武器的反扩散、反洗钱以及打击非法贸易等。如果是这样的话,发达国家自身将面临更多危机。核武器重新兴起可以部分归结为气候变化的原因,而且会重启关于核扩散问题的辩论。
气候变化也可能在一些国家引起规范的破坏。气温的上升和水源的缺乏会引起关乎生计的农业衰退,结果则有可能是该地区更为依赖不需要大量水和耕种技术的毒品种植。而且,因为农业受损,开发能源以及其他原材料就显得尤为重要。类似的资源开采,取代了原有的基础广泛的经济发展模式,催生了腐败和争夺资源流通控制权的国内冲突。
早在最近海地、埃及和其他地区发生的食品危机之前,气候变暖、水源稀缺、化肥和能源的高价以及农业转向生产生物能源等都加剧了食品安全问题。对市场力量的传统解读认为,一旦世界上的农民获得了正确的价格信号,食品供给问题将自动解决,证据显示这种说法已经站不住脚了,尽管最近商品价格有所回落。正如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指出的:“呈现出来的危机是世界食品供给和农业生产的一个根本性的结构变化,很明显与能源价格上涨、气候变迁以及亚洲兴起的中产阶级密切相关。除非将食品危机置于这一层面进行考虑,饥饿和营养不良将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激发不稳定和焦躁情绪。” [14]
在越来越多的地区,食品安全问题激发了国内冲突,比如苏丹、阿富汗、加沙地区以及索马里。对于徘徊于饥饿和死亡边缘的人民来说,食品作为国内武器的作用上升。救济食品会被袭击、抢劫甚至毁坏。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及其下设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在为充足的资源发愁,不得不在危险情况下削减救济量,令人不禁质疑类似的多边合作组织的效力何在。长期看来,人民饥饿、营养不良、体弱多病的国家不能够为摆脱长期贫困建立获取足够的人力资源。
气候变化激起的另一个国家间问题是海洋边界问题。海平面的上升使低地岛国面临海岸被淹没的危险,而海岸线恰恰是现今测量海洋国土的基准。[15]比如,目前有超过200个小岛,主要是岩石和暗礁散布在南中国海的浅滩上。尽管目前在高潮位时,这些所谓的小岛只有很少部分露出海面甚至完全被海水淹没,恰是它们划定了国家的专属经济区(EEZ),因此无论在合法性上、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战略上都是重要的。在极地附近,尤其是北极地区,融化的海冰和逐渐裸露出的地标可能会引发新的领土和拓展专属经济区的诉求。当近海资源因海岸侵蚀、人口压力以及陆地资源过度使用而显得更为宝贵之时,模糊的海洋边界和竞争性的诉求会更富争议。并且,当海洋温度变化时,捕鱼业也会发生变化,新的问题又会在渔业领域内爆发。
气候谈判与全球秩序
最后,气候变化也推动了新的国际制度的创建,因为它清楚地表明其他一些制度是脆弱的、僵化的。最为明显的是,未来关于减少碳排放的多边安排可以建立一个国际能源署式的组织,监督国家履行承诺,或许还可以谴责那些不遵守的国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已经有一个位于波恩的秘书处提供支持,可以进行一些监督。此外,一些观察家认为温室气体减排最终将牵涉全球范围的“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比如在大气层中植入反光材料。[16]国家不可能让渡给其他国家改变大气层的单方面权利,如果缓解的努力走到这样一种极端,就必须有值得信赖的多边机制。
在较近期,一项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多边协议有望在今年年底达成,尤其是在欧洲,以取代将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一些观察家认为,在以西欧许多国家为代表的气候纯粹派与担心约束性承诺会成为用环境掩盖经济竞争的幌子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美国占据了有利的实用派或中间派的位置。如果美国在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调解,这种中间派立场将是一个支点。
然而,美国的立场可能是进退两难。最发达的国家希望美国大幅削减各国排放水平,这也正是发展中国家想要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所希望的开放的财政援助和技术转让,最发达的国家也希望能够提供。风险在于,如果美国没有执行严格减排目标,或者提供慷慨的财政援助和技术转让,其威望或软实力会加倍受损。这将使美国很难让其他国家的政府在一些突出问题上提供支持,比如“反恐战争”和反扩散。
主要国家如何对气候变化作出反应、应对或适应会影响全球化进程本身。牢固的多边合作新习惯和新机制有助于加强全球互动。另一方面,尽管气候变化并非罪魁祸首,其总体影响可能足以阻碍全球化进程。部分由于气候原因出现的难民数量增加有可能引起对新的人口流动控制。疾病模式的转变会增加对公共健康的忧虑,激起对外国人的偏见。北极圈的国家可能试图宣称它们在北极地区拥有新的航海和资源优势(引起地理上处于劣势的国家的不满)。
发达国家关于公共品(比如水资源)私有化的主流经济学说会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尤其是在脆弱的传统社会。如果有巨大的温室气体削减义务的国家针对没有这种义务的国家征收碳税,将引起经济报复的恶性循环。国家在全球经济不断扩展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尊重国际现状,而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会追求狭隘的修正主义目标。
评估气候变化与未来出路
对于安全分析家以及科学家而言,气候变化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气候“赢家”(如俄罗斯)可能转变为政治输家;俄罗斯与中国的相互作用表明了这一点。更糟糕的是,气候变化既是极不确定的,也是非常长期的。在当前逐渐显现的国际经济危机中所面临的协调利益的政治挑战令人畏惧。这场危机使得我们更加难以令人信服地展示和沟通前瞻性的绿色技术和设施有助于创造就业,并且是一项双赢战略。不过,现在无所作为只会令最终影响更加恶劣。事实上,如果把气候科学家们聚集在一间密室里,问他们需要做些什么,他们会说“一切,而且一直做下去”。
然而,补救行动的规模和范围需要与问题相匹配——对于这一点,科学尚未给出令人信服的标准。多年以前,在人们关注气候变化之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战略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曾观察道,他往返于波士顿与华盛顿之间所感受到的气候变化比美国几十年来的感受更深。从分析上和政治上看,摆脱到底是缓解还是适应这个让人困惑的辩论应该是一个起点。目前为止,多数讨论关注的是缓解:世界如何减缓并进而扭转温室气体的累积。然而,即便缓解战略远胜于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其他战略,仍然会让世界在未来几十年内继续变暖。因此,思考全球变暖的安全影响意味着思考组织、国家和制度如何适应无论如何都是事实的气候变化。由此,即使谢林是对的,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的累积性、系统性后果至关重要。气候变化影响着维持人类一切努力的生物圈。一种单一的、简单的政策路线——比如把一个组织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或者承认一个分离主义省份的独立——是不够的。相反,从对外援助、国家建设、边境控制到食品与能源安全、技术转让与贸易政策、国际法与多边外交,气候维度需要统筹所有这些政策考虑。如果意识不到一系列关键的安全政策问题背后隐藏的气候维度,未来的政策行动将会遭遇失败的危险。
1.最近两年一些有思想的分析家们似乎一致将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进行讨论。2007年4月,CNA 公司发布了一份关于《国家安全与气候变化的威胁》的研究。2007年11月美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中心和新美国安全中心联合发布了《后果的时代》报告,而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了《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报告。公开的资料显示,美国情报界也探讨了环境与安全之间的关联性,最近开展了一项关于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影响的大规模评估。 ‘National Security Analyst Appraises Risks of Climate Chang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Daily, 16 May 2008; ‘New Intelligence Assessment Sizes Up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Climate Change, Inside Defense Newsstand, 18 June 2008; Hous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Select Committee on Energy Independence and Global Warming, Open Joint Hearing, 25 June 2008.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权威性三卷本评估报告则强化了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努力:Climate Change 200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对政治和社会影响卓有见地的分析,见Nils Gilman, Peter Schwartz and Doug Randall,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 System Vulnerability Approach to Consider the Potential Impacts to 2050 of a Mid-Uppe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Scenario (San Francisco, CA: Global Business Network, March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 gbn.com/ArticleDisplayServlet. srv?aid=39932..
3.Testimony, Dan Kimball, 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 Washington DC, 26 April 2007.
4.IPCC, Climate Change 2007: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p. 331.
5.作者之一的家乡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圣约翰河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
6.Assessment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Select U.S. Security Interests, Module 2: Country-Level Exposure to Potential Sea-Level Rise, Report Prepared b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arth Science Information Network (CIESIN), Columbia University for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19 October 2007. Data available at http://sedac.ciesin. columbia.edu/gpw/lecz.jsp.
7.Thomas R. Karl et al., eds, Weather and Climate Extremes in a Changing Climate. Regions of Focus: North America, Hawaii, Caribbean, and U.S. Pacific Islands, U.S. Climate Change Science Program and Subcommittee on Global Change Research, Synthesis and Assessment Product 3.3, June 2008.
8.在这里没有讨论到的是气候变暖带来的地表干燥和火季延长的影响,这个问题加利福利亚人和澳大利亚人可以作证。
9.‘U.S. 2008 Tornado Death Toll 58% Above Average, Daily Green, 5 May 2008.
10.对气候变化作为安全问题的出色描绘,见Joshua Busby, ‘Who Cares about the Weather? Climate Change and National Security,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3, July 2008, pp. 468-504.
11.‘U.S. Midwest Farmland Flooding Boosts Food Prices, Reuters, 18 June 2008.
12.CIESIN, Assessment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s on Select U.S. Security Interests, Module 3: Water Scarcity, 20 November 2007, www.ciesin.columbia.edu/ documents/Climate_Security_CIESIN_ July_2008_v1_0.ed70208.pdf.
13.比如可参见,Aleksandr Khramchikhin, ‘The Chinese Bicycle, Novy Mir, 15 March 2008.
14.Laurie Garrett, ‘Food Failures and Future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5 May 2008.
15.Idea conveyed by Michael Malley, Depart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16.Fred Iklé and Lowell Wood, ‘Climatic Engineering, National Interest, no. 93, January-February 2008, pp. 18-24.
本文原刊于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SURVIVAL杂志4~5月刊,感谢作者惠赐版权。作者保罗·赫尔曼 (Paul F. Herman Jr)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远景分析处项目主任;格雷戈里·特雷弗顿( Gregory F. Treverton) 是兰德公司全球风险与安全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