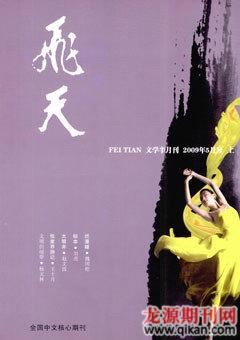敦煌莫高窟半月记
高 平
敦煌的莫高窟,我去过许多回了,最难忘的还是第一次去时的经历。
1979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当时我在甘肃省歌剧团任编剧;1980年,被选为甘肃省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甘肃省分会常务理事;心情不一样了,想出去长点儿见识,做点儿学问,当年10月,我向作协分会提出想到久已向往的敦煌莫高窟去一趟。他们很快同意了,文联给我开了三封介绍信,还发给了120元出差费(这可是个不小的数目!那时的物价和人们的工资一样低,收费的地方也少,记得同事结婚凑份子送礼只需交1至2元)。
29日上午八点从兰州乘火车西行,进入河西走廊以后感慨颇多,因为那是22年前我被西藏军区送来“监督劳动”的地方。一路上竟然写了短诗七首,只有《不悔》一首成型留了下来。这正应了鲁迅先生的告诫: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作诗,容易将诗美杀掉。
第二天早上到达柳园车站,那时车速慢,1000公里路程跑了近25个小时。从柳园到敦煌还要坐100公里的汽车。由于到下午两点才有班车去敦煌县城(不像现在不长时间就有一趟,至于出租车则连名儿都没听过),那个小站也没有可去可看的地方,我就坐在车站写信,告诉家里已经到了柳园(如果是现在,只需打手机,“言而无信”了)。写完了信到邮局去寄,在街上又得到了灵感,写了一首《我看见几个青年》,后来发表在云南的《边疆文艺》上。
当时去敦煌的人不多,难得遇到了几位同行者,那时还不兴印名片,他们写在我的笔记本上的名字是:上海画院的张充仁、王大进、王志强、张一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姜伯勤、黄崇岳、毛佩琦、陈汉玉。当晚,我们一起住在敦煌县招待所,大家神聊了很久,知识分子一遇到思想解放话就特别多。
第二天(10月31日)起床以后才知道,从县城到莫高窟虽然只有25公里,但要前去并不方便,要等到明天才有班车,大家都很着急,经过联系,由县机关派车送我们八人去莫高窟,每人付了一点汽油费。
到了莫高窟,我被安排住进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招待所(人民大学和上海画院的七位在莫高窟待了三天就回去了),这是一个坐落在大门外右侧的古建筑三进小院。我的几位早已熟悉的男女朋友也住在里面,他们是编导、舞蹈演员赵之洵、高金荣、田生瑜和种莉莉,还有摄影家陈之涛。当天,我拜访了副所长段文杰(所长常书鸿不在)和被誉为敦煌学“活字典”的史苇湘,史先生也是刚被“改正”的右派,在负责资料室的工作。
白天,我们逐日地参观洞窟,有时由潘玉善解说,有时自己看。记得有一天竟然一口气看了60多个洞子。有的洞子虽然有编号,其实没有多少东西可看;有些洞子大同小异,走马观花就可以了;关键是要细看重点洞和特级洞。也有的洞窟(如465窟)因为通路崩塌还没有修缮,我们就扛着梯子,一层一层地爬上去看。可以说我们把所有的洞窟差不多都看过了(我相信,除了那里的工作人员,任何外来的参观者再也不会享受这样的“优待”了)。在参观中,敦煌壁画和雕塑的艺术构思、表现手法、历史内容以及它的沧桑故事,它的丰富与伟大,使我一次次受到强烈的震撼。莫高窟像一块巨型的磁铁,紧紧地吸引着我的追忆、我的想像、我的思考,催生着我的创作欲望。其中除了编号3、9、112、159、220、285、322的特级洞中的珍品以外,12窟的法华经变,331窟的涅槃变,21 7窟的净土变,285窟的五百强盗成佛,445窟的嫁娶图、耕获图,323窟的张骞出使西域图,156窟的宋国夫人出行图,257窟的鹿王(九色鹿)本生,428窟的裸体飞天。96窟的大弥勒佛,296窟的商旅图,420窟的胡商遇盗图,146窟的云中乐队,144窟的乐舞图,158窟的卧佛,215窟的现代供养人……也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方面专家的著作很多,我就不班门弄斧了。有趣的是,大家发现在编号Z248(C152、P101)的北魏时期的洞中,有一尊苦行的雕塑非常像我。
晚上,我们一是聆听史苇湘、段文杰介绍、讲解有关敦煌艺术的种种知识和情况,二是整理资料和看书。史苇湘先生热心而又慷慨地为我提供了很多种参考书。我在莫高窟的15天里,阅读了《敦煌拾零》、《敦煌变文集》、《敦煌歌辞集》、《王梵志诗一卷》、《敦煌曲子词集》、《敦煌掇琐》、《敦煌图录》、《敦煌劫余录》、《敦煌杂录》、《敦煌曲初探》等等。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终于读到了已经失传千年的韦庄的著名叙事长诗《秦妇吟》(它作于唐僖宗中和三年,即公元883年。1900年首次在藏经洞挖出了手抄本,原件现在巴黎)。一年之后,我发表了《<秦妇吟>的现实主义成就》一文。20年后,我又根据它编创了戏曲剧本《秦妇吟》。
高金荣、田生瑜、种莉莉三位的目的和我完全不同,他们只是寻找、描绘壁画上的各种手和手臂的造型和姿势,为创作敦煌舞收集素材(后来编演了《千手观音》)。我也想附带为他们做点贡献,在阅读敦煌古典文献的过程中,特别留意摘录、翻译了有关手的记载1 700多字,交他们参考。
在此期间,也听到了一些有关壁画的趣闻。有一则这样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一群白俄士官逃生到了新疆,新疆方面以邻为壑,把他们送到了敦煌,住进了莫高窟。美国人知道以后就同他们联系,告诉他们说在某个洞子的壁画上有中国的全国地图,把它剥下来送到上海,可以给他们10万美金。敦煌人民知道那是第61窟,画的是山西五台山图,上面标有地名。群众把他们赶出洞去,并把这个洞子戏称“十万金洞”。关于这件事,1936年《申报》记者陈庸雅在《西北观察记》中曾有报道。
我不止一次地看过白俄们居住的洞子,他们在里面生火做饭,把壁画熏黑了不少。那段无可奈何的历史既然发生了,除了惋惜和叹息,又能怎样!
敦煌研究所的专家们和所有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依然十分艰苦。他们住的是低矮的小土房,里面的炕和“桌子”都是土坯垒的,顶棚和窗户糊的纸一遇到戈壁起风就哗哗作响,钻沙进土。一年四季喝的是苦成的水,什么茶叶泡出来都没有茶味。子女上学得去50里外的县城。附近几十里没有任何商店,生活的不便可想而知。他们都是无怨无悔的纯粹事业型的人,数十年如一日地献身于敦煌艺术的保护、整理、发掘、发现、研究、发扬;从家乡到西部,从青年到白头,与世无争,于国有功。
整个莫高窟恰如沙海孤岛,可谓地广人稀;古木荒草无语,悬壁幽洞有眼;壁画雕塑,栩栩如生;各种神怪传说,使人将信将疑。我去时正值秋末,我住的小院在大树的包围之中,每到夜深人静,秋声不绝于耳,披衣入厕需穿过庭院小径,纵然快步往返,但不能闭目塞听,更难以抑制想像,我虽然不信鬼神,却总是毛骨悚然。
我和赵之洵发现小院的后面有个一公尺见方的水泥池子,里面的水是用汽车从城
里拉来的甜水,是专门留着供前来参观的贵宾和外国人喝的,其他任何人不得饮用。我们是在研究所的食堂吃饭的,那里用的自然也是成水。为了泡茶,我俩常在夜间去小池里“偷”灌上一铁壶,搭在火炉上烧开,以解白天老喝咸水之苦。后来被入发现了,池盖上了锁,我们也不好吭声。
我和赵之洵之间还有个“花絮”。11月12日早晨,我们走进九层楼,见他突然跪倒在大佛脚下磕起头来。我问他:“你是好玩,还是真信?”他说:“真信。”我说:“你怎么也迷信了,一个泥胎有什么可信的?”我还将这件事说给那几位女士听。到了晚上,我胃疼得要命,上吐下泻,得了急性胃炎,因为没有医生,只好自己找了些中成药。大家说:你骂了佛,佛惩罚你了吧?我辩驳说:“佛不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吗?如果如此小气,动辄报复别人,那就不配为佛,更不值得人信了。”经我采取了“饥饿疗法”,第三天肠胃就好了。
12日晚间,招待所所长吴小弟来房间看望,闲聊中问起了我的经历,当他听到我曾是第一野战军战斗剧社的一员时惊喜地说:“我们这里也有个战斗剧社的!”我问叫什么名字?他说叫李其琼。没错,我记得她。那是1950年的初春,在刚刚解放的成都,我们战斗剧社文学和美术队同住在玉带桥的一家公馆里。就是美术队的。她是一位文雅、清秀、寡言的四川姑娘,印象较深的是她梳着两条大辫子。赵之洵也为这里竟然有我的一位一别30年的战友而欣喜。
13日中午,当我们从林间小路走向食堂的时候,赵之洵忽然对我说:“后面一个女同志好像在追我们,你看看是不是你说的那位老战友?”我回头一望,是一位老太婆嘛,哪里有一点点样子?立即转过头来肯定地回答说:“不是!”我们只管继续往前走。后面的“老太婆”急忙赶上来,操着地道的四川口音向大家发问:“你们哪位是高平同志?”啊,她果然就是当年的李其琼,她显然也认不出我了。我马上应卯:“我就是!”我去她家拜访,才知道她和丈夫孙儒侗1952年就自愿来这里工作了,历尽了艰苦;后来竟然被双双打成了“右派”,受尽了折磨。当晚,他们夫妇又到招待所来回访,并送我一篮自己种的梨。之后,我再去莫高窟时请她比较详细地讲述他们的经历,于1989年3月用古乐府体写了一首长诗《敦煌女画家》,同年,发表在《飞天》7月号上。1997年收入《高平诗选》。也许是由于“同右相怜”我才为她“树碑立传”吧。
期间,我们抽空游览了西千佛洞、阳关旧址、南湖(寿昌海)、鸣沙山和月牙泉等名胜古迹。
在敦煌的15天里,我一共写了14首诗(其中的《莫高窟秋风》、《敦煌情歌》、《登阳关》、《告别敦煌》我比较满意),加上歌词《欢迎你来敦煌》,正好是一天一首。
我这一生,写作比较勤奋;每到一地,很少空手而归。“至于成败利钝”,那就一看社会的环境,二看自己的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