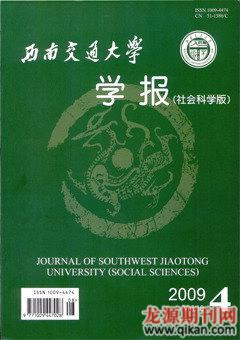“伤心人之伤心语”
苏利海
关键词:晚清词坛;张惠言;浙派;项鸿祚;《忆云词》;没落贵族;伤心语
摘要:项鸿祚是晚清词坛名家,学界对其词赞誉甚多,但论述多停留在“情真”、“感人”的层面上,对其词风的生成、特征及在词史上的地位认识不足。实际上,项氏出身于“簪缨之族”,但家世已然败落。正是“没落贵族”的身世直接造就了他多感抑郁的情性,而生活的封闭性、审美情趣的精致淡雅、情感的细腻幽怨则决定了其词“苦艳郁深”、凄婉幽邃的风格。项鸿祚在创作上表现出对浙派末流空疏靡丽词风的厌弃,而他有意识地借写苦涩缠绵的艳情抒发身世之感的艺术追求却与后来晚清盛行的比兴寄托之风相一致,从而昭示了晚清词坛的新气象,开了晚清词坛以比兴入词之先河。
中图分类号:I22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4-0020-05
晚清词坛可谓家家言“比兴”,户户谈“寄托”。对这种风尚的形成,前人多归因于张惠言的尊体之功。但本文认为张氏理论之所以能在晚清盛行,恰恰是因其顺应了当时词坛已然兴起的比兴寄托创作潮流的结果,这也意味着并非先有了张氏理论这个“因”,才有词坛实践这个“果”,而是倒置过来,先有了词坛上已然存在的比兴寄托的创作事实,然后才有张氏理论的兴盛。这位当年名不播词林的学者在逝后之所以被后人捧上词坛祭酒的高位,正在于他的理论顺应了时代潮流的发展。这也凸显了晚清词坛的复杂性,虽然众多词人倡言“比兴寄托”,但对这个传统术语的接受,每个人的接受视域各异,在观念上、实践中皆表现出不同的趣味。故阅晚清词人集子,不能仅以其词中出现了“比兴寄托”诸语,就笼而统之地纳入所谓的“常州词派”,从而忽略了词人特殊的生存背景和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创作个性。本文研究的项鸿祚词即可提供这样一种反思。
一、“伤心人”之“意内言外”的词学理念
清道光年间,张惠言的寄托理论尚局限在常州一地,并未能风靡全国,但其时大江南北已有不少词人自觉地在创作中实践着比兴的理念,其中有意识地在词中寻求比兴寄托并能昭示晚清词坛新气象的当首数项鸿祚。项氏在《忆云词自序》中屡屡畅言“比兴寄托”,但他所谓的“比兴寄托”,并非像有学者所言是对张惠言理论的完全接受,而是他个体生存处境和时代变迁相撞击的结果,具有特定的内涵和指向,这一点项氏在《忆云词自序》中已有清楚表明。如其中的《甲稿序》云:
夫词者,意内而言外也,意生言,言成声,声分调,亦犹春庚秋蟀,气至则鸣。
《丙稿序》云: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生涯之生?时异境迁,结习不改,……茫茫谁复知者,倪仰生平,百端交集,正不独此事而已。
《丁稿序》云:
当沈郁无惨之极,仅托之绮罗芗泽以浅其思,盖辞婉而情伤矣。不知我者,即谓之醉眠梦呓也可。
项氏所在地——杭州,在道光年间仍为浙派所缚,词风所尚多以南宋为宗,正如时人谭献所云:“杭州填词,为姜张所缚,偶谈五代北宋,辄以空套抹杀”。与项氏交往的词人如郭唐、叶午生、吴子律、李西斋等多属浙派,如郭唐为浙派后期领军人物,叶午生则被浙派大家姚燮称为“甚野云石帚,残月屯田,格韵能超”(《忆旧游,题叶午生海蒳轩词》)。
项氏多言“比兴寄托”,但这里的“寄托”显然并非源于常州词学,而是出自他的“身世之感”,这就与张惠言等常州词派诸人所言的“君国之忧”类的“寄托”拉开了距离。如项氏所说:“山鬼晨吟,琼妃暮泣,风鬟雨鬓,相对支离,不无累德之音,抑亦伤心之极致矣”(《忆云词甲稿序》)、“托之绮罗芗泽以波其思”等,无不说明他上承楚骚的香草美人传统,而在艳情之中渗透了乱世之感和身世之悲。其云“茫茫谁复知者,侥仰生平,百端交集”,也正提醒后人:“绮罗芗泽”尚是外在表象,“沈郁无憀”才是词人心魂所系。
在论及项氏词风时,学界多以哀婉动人、情感真挚来概括,如有学者云:“项氏的词有着充分的感情投入,这也就是《忆云词》的价值所在”。“情真”的概括尚缺乏一定力度,更不能揭示出项词个性所在。唯有从项氏自称的“寄托”入手,方能更准确地解读其词,进而对他在词史上的地位有准确把握。
二、“没落贵族”的身世之感
项鸿祚(1798~1835),浙江钱塘(杭州)人,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项鸿祚曾在《玉漏迟,题(饮水词)后》中以纳兰容若为异代知己,并云:“君自孤吟山鬼,谁念我、啼鹃怀抱,消瘦了。恨血又添多少。”言辞凄厉,似有难言之痛。
对项氏凄楚词风的溯源自然不可仅停留在其所言的“幼有愁癖”这一先天抑郁型气质上,本文把这种“愁癖”概括为“没落贵族的伤世悼己之悲”。之所以称项氏为“没落贵族”,源于其家世曾经既富且贵。他的祖辈们辛苦从商,积累下丰厚的家底,后又由商转儒,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据此也可称项氏出身于“簪缨之族”。不过到了项鸿祚这一代,家世已然败落,谭献说其“世业盐筴,至君渐落”。项氏在《忆云词丙稿序》中也云:“是叠遭家难,索居鲜欢,追忆前尘,十遗八九”。一个“至君渐落”,一个“叠遭家难”,可见他的生活实是山河日下,不可与先辈同日而语。
导致他家庭衰败的原因虽待详考,但从作品中还是可探得一二,这其中主要有:家居火灾之厄、人事纠纷(多指外人的谤毁,如《壶中天》中云:“众女谣诼蛾眉,元南无北,到处机蓬矢”)以及功名不就,先后两入春闱皆告负等。
作为没落贵族的代表,项氏拥有一种独特的生存境遇,并对其凄婉词风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这种生存境遇表现为:
(1)生活的封闭性。项氏性情静默,常喜独处,如谭献所云:“性湛然耆古,尝避喧南山读书僧院就泉看山,无复尘念”。由于经常“闭门骚屑特甚”(《徵招》序),他的生活圈子异常狭窄,与他相伴的仅是几个诗词文友和妻妾歌妓。他除两次上京应试和在周边的江苏、江西做过短暂的游历外,一生时光多消磨在内闱里,或作词听曲,或品茗赏月,抒发的情感也多集中在相思惆怅、日月如梭、功名不就之类主题上。
(2)审美情趣的精致淡雅。项氏词多写闺中精美饰物和周围小巧的水榭、亭院,属于王国维先生归纳的“优美”的小境界。如《临江仙·秋闺即事》所云:
一架牵牛花褪了,日长亭院秋清。云罗低抹远山青。疏疏小雨,凉透木犀屏。薄睡起来添半臂,夕阳又照西櫺。更无人会此时情。自钞宫谱,闲品玉靴笙。
词中之景应是他日常生活的缩影,“更无人会此时情”中的“情”也是一种富贵人家的闲情逸致,其中景物如褪色的牵牛花、白云、青山、木犀屏、宫谱、玉靴笙等皆带有闲暇、精致、慵懒的气息,体现出他的审美格调中闲适、清雅的一面。
(3)情感的细腻、幽怨。由于经常“闭门”,与外界处于隔绝状态,项氏的情感也趋于内敛,体现
出窄而幽、细而密的特点,对人世的悲欢离合、自然万物的春荣秋谢的感受尤较常人敏锐。可以看出,正是“没落贵族”的身世直接造就了项氏多感抑郁的情性,并进而决定了他凄婉幽邃词风的形成,而一部《忆云词》也可谓一曲“没落贵族”的挽歌。
三、“伤心人”之苦艳郁深的词风
关于项氏词,谭献《箧中词》曾论道:“荡气回肠,一波三折,有白石之幽涩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无其率,有梦窗之深细而化其滞,殆欲前元古人”。此论有意把项氏划入浙派。实际上项氏对浙派并不认同,他在《甲稿自序》中云:“一二知者,强附我于名胜之后,虽复悄然自疑,而学之愈笃”。读此可知当时已有人把项鸿祚划人浙派宗社中,但一个“强”与“疑”充分表现了项氏对浙派的不满,原因在于“近日江南诸子,竞尚填词,辨韵辨律。翕然同声,几使姜张頫首,及观其著述,往往不逮所言。而弁首之辞,以多为贵,心窃病之,余性疏慢,不能过自刻绳,但取文从字顺而止”(《忆云词乙稿序》)。项氏作词强调“文从字顺”,“不能过自刻绳”,反对在韵律词藻上过度雕琢,因此对浙派“辨韵辨律”的风尚颇为不满,称他们的创作是“往往不速所言”,所以自己“雅不欲与诸子抗衡”(《忆云词乙稿序》)。他在《祝英台近·自题填词图》中又云:“自吟苦。任教采壁旗亭,争唱玉田句”,表示出一‘种不傍他人,自辟新境的骨气。
项氏作品趋于南唐词风,与清初的纳兰容若更为相似,如他所说:“生幼有愁癖,故其情艳而苦,其感于物也郁而深”(《忆云词甲稿序》)。本文即据此把项氏风格概括为“苦艳郁深”,其中“苦艳”是指其作品在题材上多以表现苦涩缠绵的艳情为主,而“郁深”则指他借艳词来抒发身世之感。正如项氏所言,“苦艳”尚是外在的,背后的“寄托遥深”方是其中的真味,也是他刻意追寻的境界。
项氏甲稿成于癸未(1823)年,是他二十五岁前所作。从词序中所说“束发学填词”来看,此集应收有少时之作。虽然项氏称自己的词是“山鬼晨吟,琼妃暮泣,不无累德之音,抑亦伤心之极致矣”,但此时的“伤心”多指情爱之苦,正可以“为赋新词强说愁”(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来概括,所以大多写得旖旎秀丽。如《醉太平·有忆》:
诗魔酒魔,愁过病过。撩人一段横波。唤卿卿奈何。池喧绿荷。墙围碧萝。骤凉亭院风多。近黄昏睡那。
词中所“忆”的显然是一位女郎,其思念之情,也有明确所指。“撩人一段横波。唤卿卿奈何”虽显直白,但也生动刻画出一个为情爱所困,无法自拔的多情少年的精神状态。下片以“绿荷”、“碧萝”、“亭院”等美景愈加衬托出少年的无聊、无奈、苦闷,整首词可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一境的翻新。
甲稿中的“伤心”除了情爱之苦外,还包括科举失利的隐痛。项氏是道光十二年(1832)才中举人,在此之前一直科场失意,这无形中为其敏感的心平添了许多愁闷。如其在《采桑子·吴子律索看近词赋此答之》中所言:“浮名只为填词误,诗酒流连。花月因缘。写入乌丝尽可怜。”由于科场上屡屡受挫,他只能日日借填词来排遣苦闷,故后人每每称誉项氏所作是“词人之词”,这实在是他从未想要的荣誉。在项氏屡言的“寄托”中,由于科举失利而导致的失意无聊乃至愤闷孤傲无疑是其中一个主要方面,这点在下一首词中有充分体现。《满江红·九月十四日晚,乘月过虎跑,憩小池上,见寺门未阖,闲步近客室,有皂衣高冠者呵禁甚厉,问老僧知当轴诸贵人宴两试官于此,始忆城中放榜又三日矣,一笑纪此》:
独有常娥,不笑我、青衫依旧。正相伴、寺门乞茗,野桥沽酒。小隐竞成丁令鹤,学仙羞逐淮王狗。趁夜凉、来叩远公房,惊而走。莲座倨,蛮狮吼。松径僻,骄骢骤。只维摩病瘠,见人摇首。身贱自遭奴隶薄,心闲好与溪山友。怪秋坟、鬼听忽揶揄,颜之厚。
功名不就给词人带来的巨大刺激从此阕词中不难感受到,项氏内心极度波动不安,用语激切、直白,不再含蓄、委婉,为其集中少有的变调,盖因外事所激,愤然而作,不著粉饰的结果。此类词在数量上虽不占优势,却提供了其心魄交战的最有力线索。词人表面上说是“一笑纪此”,但内在的情感却纷繁复杂:自卑、白惭、自怨、自慰、自怒等皆包含其中,深刻揭示了他落第后无限的辛酸与苦涩。“独有常娥,不笑我、青衫依旧”正反衬出当时为众人讪笑的窘境。“惊而走”既可见权贵之威势,更见出作者的愤懑、羞惭之情。“身贱自遭奴隶薄”足可证明科举失利对他的心态乃至一生的重大影响。此后项氏虽中了举人,但在随后的春闱一试中又遭重创,不久郁郁而亡,其中原因也可由此想见。
乙稿成于戊子(1828)年,为其羁旅漂泊期。在度过了多愁善感的青春期后,项氏在此集中多抒发异地漂泊之苦。项氏此次出行显然不是休闲度假,联系其“世业盐筴”的家世,以及作品中凄苦怨抑的语调,可测这当是一次远游经商活动。从其词中提到的浙江吴越一带的吴山、越中、吴江、吴门、山阴、兰溪,江苏扬州、镇江一带的广陵、红桥、金焦、维扬以及江西南昌的豫章、百花洲、灌婴城、梅仙祠、铁柱宫、滕王阁等地名可知,这次远游路线是由杭州出发经苏州、扬州、镇江,最后到达江西南昌。此集中展现羁旅之情的作品如《霜天晓角·玉山晓行》:
征铎郎当。点轻衫露凉。卖酒人家未起。残月在、柳梢黄。行装。诗半囊。梦回思故乡。秋到屏风关外,吹一路、野华香。
词中所言玉山今为江西省玉山县,其中屏风关“在县(按:指玉山县)东二十五里,距常山曹会关十五里,关屹然东西相望,关皆横跨两山间,诚江浙要冲也”,项氏去往南昌的路上经过此地。该词境可与温庭筠的《商山早行》相媲美,“卖酒人家未起。残月在、柳梢黄”描绘出了拂晓之时,旅人辞别店家匆匆上路的特定剪影。“秋到屏风关外,吹一路、野华香”,写景自然明丽,秋郊野外的芬芳仿佛扑面而来。
丙稿成于甲午(1834)年,这一时期,项氏屡遭变故:家宅不幸失火;送母北上途中,母遇水而亡;爱姬和友人相继逝去。过多的悼逝之词凝缩了其心境的悲凉衰飒,所以此期词作大多苍凉悲咽。从《烛影摇红·庚寅秋感》中可知,其爱姬约逝于戊子(1828)与庚寅(1830)年间,集中《水龙吟·魂》、《浣溪纱》(“风蹴飞花上绣茵”)、《西江月》(“翠被香添夜夜”)、《忆旧游·湖楼闲望,偶成此解,不知词之所以然》、《霓裳中序第一·检故箧见亡姬遗扇》等悼词皆为亡姬所作,无一不写得凄婉动人。集中又有若干首痛悼友人的,如《徵招·年来江湖词客子律、西斋、频伽,相继下世,余以多难闭门骚屑特甚,倚声及此盖不独牙琴之悲,黄垆之痛也》:
冷鹃啼落西湖月。词人可怜俱老。玉笥总埋云,剩秋风残照。薄游欢意少,忍重展、乌丝遗稿。竹屋羹洲,酒边花外,黯然怀抱。愁草掩闲门,知音绝、谁听怨琴凄调。暗苇泣孤蛩,耿窗灯寒峭。角巾归去好,定还共、夜台歌啸。醉魂远,剪纸难招,
悔相逢不早。
从“忍重展、乌丝遗稿”可看出项氏与吴子律、郭麐等人曾有唱和之作,但在项氏词集中却只有甲稿录有《采桑子·吴子律索看近词赋此答之》一首,可见交往并不深厚。而“悔相逢不早”也显示出项氏与郭唐等人更是相识很迟,或仅为闻名而已,故此词名日“悼友”,实为自伤。如其所言“盖不独牙琴之悲,黄垆之痛也”(黄垆“谓地下也。犹言黄泉”,这里的“痛”显然不仅是痛悼友人,更是“痛”自己的“多难”身世,所以项氏羡慕他们能“角巾归去好,定还共、夜台歌啸”,言外之意是说自己现实的悲凉处境实远甚于他们。
表达类似主题的词还有《壶中天·叶午生比部同年殁于京邸,以词哭之》,词人从挚友病逝他乡的悲惨遭遇中发出了“如此江山,不容词客,寂寞人间世”的悲怆之吟,简炼、形象地勾勒出当时文人才子科场失意,落魄他乡甚至魂归故土的悲惨一生。
此集中值得关注的还有两首词,它们对于考索项氏的中年心境最有价值。如《长亭怨慢·经年雁旅,岁晚言归。概念平生,短歌当哭,不独为三径之荒也》中“此身如叶。尽零落何须说”、“恨夕阳、有限黄昏便卷尽、一林残雪”诸语直接反映了他中年时的萧条景况和惨淡心境。此外如《壶中天》直指人世的险恶,以神游天宫来反衬人间的凶暴,而“众女谣诼蛾眉,无南无北,到处机蓬矢”则说明外在的打击已然把他逼迫到无容于人间的境地。
丁稿成于乙未(1835)年,这年项氏上京应试,再次失利,心境益见颓唐。如其《丁稿序》所言:
今年正月,再上春宫,此事遂废。留京师五十日而去,还我睡乡,始检旧稿,次为一卷。嗟乎!当沈郁无憀之极,仅托之绮罗芗泽以浅其思,盖辞婉而情伤矣。不知我者,即谓之醉眠梦呓也可。
丁稿作品大部分拟《花间集》,专写男女情思。但这些艳词多是“伤心人”“托之绮罗芗泽以没其思”的“伤心语”,也是项氏临终前对自己一生遭际的反思。如《采桑子·读(金荃词),题后》:
艳词空冠《花间集》,不上云台,却上阳台,一读《南华》事事乖。谢郎折齿狂犹昔,红粉成灰,蜡炬成灰,剩得闲情赋锦鞋。
云台本为汉宫中高台名,汉明帝追念前世功臣,图画邓禹等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后用以泛指纪念功臣名将之所。阳台则是宋玉《高唐赋》中所描述的楚王与神女欢会之所,为男女情爱的代称。“艳词空冠《花间集》,不上云台,却上阳台”,正概括了项氏一生科场失意,只能在儿女情场中空耗生命的悲凉结局。下片所云“谢郎折齿狂犹昔”更是感叹一生碌碌无为,回首往昔,只落得“剩得闲情赋锦鞋”的可悲结局。作者检点过去,不知是耶、非耶?似有无限的遗憾在心中回荡,“一读《南华》事事乖”句则大有人生如梦如烟之感。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项氏作品苦艳郁深,内涵丰厚,词笔清切凄婉,不用学问语,不堆垛典故,不做字谜,在清词逐渐诗化的风潮中能坚守词体特有的抒情功能和含蓄蕴藉的审美维度,故被后人誉为“词人之词”。严迪昌先生则在《近代词钞》中称项鸿祚是“清中晚期过渡人物,为近代词史之先兆巨擘”,所谓“过渡”指他自觉地在创作中实践着“比兴寄托”的理念,其创作手法更是直接上承李煜、秦观,以艳词来写身世之感,这与后来张惠言等人强调的君国之忧、伤时之痛的“寄托”内涵颇有不同,故谭献曾不无遗憾地称项氏是“知二五而未知十”,意其境界过狭,当不得正宗。但项鸿祚在词中刻意寻求寄托,表现出对浙派末流空疏靡丽词风的厌弃,并与后来晚清盛行的比兴寄托之风不谋而合,故称其为开晚清词坛以比兴人词之先河的“近代词史之先兆巨擘”,可谓允洽。
注释:
①如郭磨在《梅边笛谱序》中批判当时浙派成员创作是:“性灵不存,寄托无有”,他在创作中亦体现出追求寄托的倾向。可参看严迪昌《清词史》441—451页的论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
②可参看李跃忠刊发在《江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的《忆云“愁癖”浅论》一文。
③见钱仲联编《清八大名家词集》749页,岳麓书社1992年出版。下文所录项鸿祚词及词序均选自该书,仅标题目,不再说明。
④见清代黄寿祺《玉山县志》卷12,同治刊本。
参考文献:
[1]周济,等,介存斋论词杂著复堂词话蒿庵论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8。
(2]姚燮,疏影楼词[c]∥陈乃乾,辑,清名家词(卷八),上海:上海书店,1982:4。
[3]夏承焘,张璋,金元明清词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89。
[4]张佳平,清词人项廷纪家世、生平、著述考[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5(1):80—83。
[5]谭献,清代碑传全集·项君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547,1547。
[6]谭献,箧中词(卷四)(c]∥续修四库全书(173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70。
[7]丁福保,佛学大词典(下册)[K],上海:上海书店,1991:2061。
[8]严迪昌,编,近代词钞(第一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423。
[9]谭献,复堂词自序[c]∥陈乃乾,辑,清名家词(卷十),上海:上海书店,1982:1。